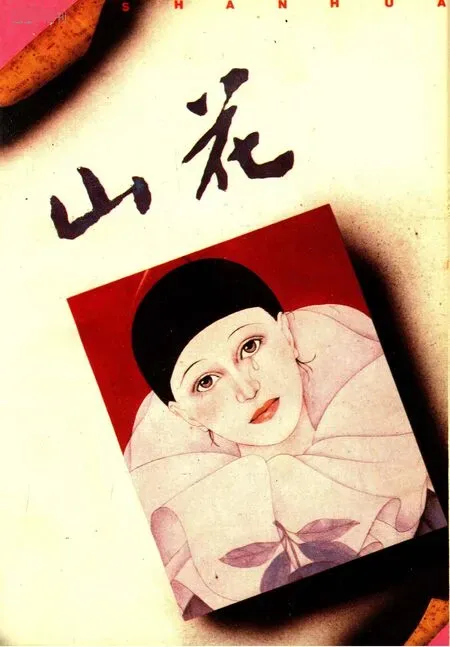馬丁·艾米斯《懷孕的寡婦》中的女性解放觀
左燕茹
當代英國著名后現代作家馬丁艾米斯以其大膽的小說形式和敘事于法以及對暴力、大屠殺、核戰爭等時代大主題的反映而備受讀者和評論界關注。“到90年代為止,他己成為英國所有小說家中最受人尊敬、最為人所模仿和最讓人質疑的一位。”2010年,艾米斯醞釀數年的長篇小說《懷孕的寡婦》出版,該小說再次回歸曾為其帶來聲譽的性、喜劇和英國社會主題,評論界普遍認為這是馬丁的回歸之作。
《懷孕的寡婦》的小說背景設定在20世紀70年代,“其時性解放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它已經進行了很長時間,每個人都沉溺其中”。吸毒、濫交和嬉皮士似乎已經成了這一代年輕人的生活時尚。二十歲的基思和一幫年輕人在意大利的一個城堡里度假。作為文學專業的學生,基思閱讀了大量的文學經典作品,他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詩人。然而,在時代變革洪流的影響下,基思的純真和書生氣逐漸被消磨掉了。在和女友莉莉同居的同時,他被山魯佐德的美貌所吸引,為了與其約會,他從小說中獲取靈感,用藥物麻醉女友莉莉。然而,在這個女性奮力追求性自由的瘋狂年代里,基思陰差陽錯地和性欲狂格羅利亞走到了一起。這次經歷所導致的慢性性障礙使他在隨后的二十五年中備受折磨,并經歷了三次毫無幸福感的婚姻。小說中每個人物的感情、婚姻和命運都烙印上了時代悲劇的色彩。
年過六旬的艾米斯在《懷孕的寡婦》中,對“已逝青春”的回憶平添了一絲反思和睿智的基調。馬丁版的“致青春”將對青春的回顧和反思置于性解放運動的時代大背景下,輕快而發人深省地刻畫了迷失在性解放運動中的一代年輕人的人生軌跡,反思了性解放運動帶給人們身體和精神的永久性傷害,是對后現代女權主義的批判和戲劇性解構。通過檢視以作者為代表的一代人的青春記憶,作者指出性解放運動并未帶給女性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它遺留下的身體和精神的雙重創傷最終使性解放運動變成了一個“懷孕的寡婦”。
性解放運動的狂歡
在六七十年代的歐美國家,“男人和女人的世界里正在發生著某種事情,一場革命或者巨大變革”,這場巨大變革就是性解放運動。在性解放運動的狂歡中,女孩子們都想“像男孩那樣舉止行為”,這可是當時的流行元素。女人們身體的時尚感在升級,女性著裝趨于多樣化,更隨意更松散,軀體的外露越來越明顯。小說中的女主人公們身著超短裙、透明襯衫、比基尼等外露明顯的服裝,甚至在一些公共娛樂場所袒胸露背并以此為美。“裙邊上來了,道德下去了”正是對當時這種社會風氣十分貼切的寫照。小說中曾經穿著平底鞋、帶著眼鏡、做過社區服務并熱衷于慈善事業的山魯佐德,在性解放運動的洪流中蛻變成人人側目的金發美女, “在露天泳池邊毫無顧忌地往胸部涂抹橄欖油”。
除了發型和著裝的變化,年輕人的道德行為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女性思想變得自由和開放起來。19世紀以前,清教徒的道德觀念制約著大多數女性的行為,而今的“新女性”挑戰傳統的性觀念和性道德,像男子一樣公開談論性自由,隨意更換性伴侶。小說中的主人公們都有著不止一位性伴侶,同性戀者也公開招搖過市。媒體的大力宣傳和“全美婦女協會”等組織的推波助瀾,讓女人們熱血澎湃地投入到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中來。然而由于對女權主義的本質缺乏正確的理解和引導,在性解放運動的洪流中,女子們膚淺地以為模仿男性、酗酒和以自我為中心的兩性關系就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高。女人的虛榮心讓她們覺得美貌能取悅于人,智慧則一無是處。男子們則趁機勸誘女人們要“順應時代的潮流”,借此滿足自己的欲望。而對他們來說,臨死前盤點自己一生中有過多少女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推翻男權、追求女性自由的幾號成了人們道德頹廢和墮落的遮羞布。
作為70年代性解放運動的見證人和親歷者,艾米斯目睹了那些純真的少男少女如何迷失在反對性別歧視、平等和自由等頗具鼓動力的宣傳中,這些標語口號的神力使他們近乎盲目地投入其中,使性解放運動成了一股放任泛濫的洪水。女人們盲目地以為像男子那樣擁有婚前性行為和多個性伴侶就意味著女權的提高,對自己作為女性主體的身份缺乏認知,在譴責男權禁錮的同時卻以男性視角界定自身的女子身份,這種身份的迷失導致女性迷失了自己的本真,將自身流于欲望支配的次等生物。
性解放運動的后果
小說伊始,作者便提到這是一部關于性創傷的小說,一個假期“斷送了基思二十五年的大好時光”。2003年,53歲的基思突然發現,性解放運動這場“天鵝絨革命”并非沒有流血和犧牲,而是男女雙方都深受其害。時至今口,人們普遍認為性解放運動以“隨心所欲”為旗幟,過度追求欲望的滿足不僅給人們的身體和精神帶來了雙重創傷,還導致了倫理道德的淪喪和精神生態的頹廢。
基思飽受身體創傷的折磨,肯瑞克和以作者的妹妹薩莉為原型創作的維奧利特等都是這場革命的犧牲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身體畸形綜合征等疾病折磨著他們的身心,無法實現的生育夢想困擾著小說中的女性。麗塔曾經幻想著要生十個孩子,結果卻悲哀地發現自己從未實現為人母的愿望,“我好像忘了這回事。我已經錯過了。”而基思的妹妹維奧利特則因酗酒和縱欲過早地離開了人世,成為這場運動中最驚人的犧牲品。維奧利特的影子在小說中若隱若現,提醒著讀者女性在這場運動中付出的慘重代價。
性道德的巨大變革導致了倫理道德觀的日漸淪喪和人們精神生態的頹廢。在這場革命的洪流中,女子開始像男子那樣不在意婚前性行為,“感情與思想己然分離。感情與性業已脫節”,混亂的感情生活導致了婚姻的極端不穩定,“離婚很容易,結婚卻是非常困難、痛苦、昂貴和令人厭煩”。愛與不愛也不再重要,1970年的愛情己被“歇斯底里的性所取代,人們當然不必再為不負責任的性行為道歉”。人們愛的只有自己。“在這個新的世界里,莉莉愛不愛基思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莉莉愛不愛她自己”。小說中的大部分人物都有過不止一次婚姻,這表明婚姻關系不再穩固,人們沒有勇氣去承擔愛和家庭的責任。艾米斯在接受美國知名網絡雜志Slate采訪時曾說,色情將改變人性,無處不在的色情己令性遠離愛。在《懷孕的寡婦》中,無處不在的性讓愛退居其次,讓婚姻和家庭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性解放運動喧囂過后,大量的負而影響隨之而來。兩性交往越來越頻繁并呈低齡化趨勢,婚前性行為、未婚先孕、離婚率居高不下等現象非常普遍,單親家庭子女心理缺陷問題增多,青少年犯罪率大幅上升等,這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性解放運動深刻地改變了愛與性的本質,它所導致的倫理道德淪喪的后果難以估量。
“懷孕的寡婦”的啟示意義
《懷孕的寡婦》是艾米斯對性解放運動所做的記錄和深沉的反思,是作者對“生命中最劇烈的社會變革”的深度思考和再認識。“懷孕的寡婦”這一書名來自俄國思想家赫爾岑的論文集《彼岸來信》,它表達了赫爾岑對歐洲革命命運的深切擔憂。“令人恐懼的是舊秩序的滅亡留下來的并非是一個新生兒,而足一個懷孕的寡婦。在新舊秩序的更替之中,暗流涌動,還要經歷混亂和荒涼的漫漫長夜。”艾米斯以“懷孕的寡婦”來喻指性解放運動,實際上是他對性解放運動和女性解放的質疑和反思,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通讀小說,我們發現小說人物幾乎全是年輕人,成人的缺席使性解放運動缺乏正確引導和有力監管。小說中作者不止一次地追問“警察在哪里?”“你們的父親在哪里?”回應他的只有沉默。女人們懷著熾熱的心情和滿腔熱血投入到為女性解放而激進的奮斗中來,但失去理智的她們由于缺乏正確的引導而陷入迷茫。作為一個人道主義者,艾米斯認為女性要取得真正的解放必須要有社會和家庭的關愛和引導,要讓女性意識到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這樣她們才能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獨立的意識,才能在思想上獲得真正的解放。《懷孕的寡婦》中成人和家人的不在場無疑表明社會和家庭在青少年性教育中的缺席。反觀當今社會,少男少女同居、未婚先孕、棄嬰乃至殺嬰等現象,我們不禁要反思社會、學校和家長是否盡到了他們應盡的責任呢?
其次,小說所呈現出的性別失范現象也引起了評論界的廣泛關注。女性從著裝到道德行為都向男性特質看齊,她們希望走出男性為她們界定的身份,但由于缺乏對自身主體性的認知,結果造成了嚴重性別越界和女性性別失范。“現代的大謬誤是一切以男子為標準,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為解放之現象。”。這種性別失范表明女性并不具有一種主體性的生存樣態,并未保有身體的獨立和人格的獨立。這顯然不利于實現女性的真正解放,只能帶給女性更多的迷茫和困惑。
“懷孕的寡婦”這一書名表達了艾米斯對女權主義前途的擔憂,“因為女權革命帶給我們的只是一個懷孕的寡婦而非新生兒。在新生兒到來之前,我們還要經歷幾次更大的震撼”。因此,作者認為,“思想意識并不是用一個于指頭捏著就能發生革命變化的。性解放運動,我認為我們仍然在途中,并且它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結語
在小說的敘述聲音中,我們發現有一個超然物外的“我”在審視著一切,“我”曾經和基思“非常密切,可是后來卻因為一個女人而鬧崩了”。在這個改變基思一生的夏天里,“我”始終對這些少男少女們的行為持迷茫和質疑的態度,“我”在小說結尾又重新和基思合為一體。這里的“我”其實足基思意識的一部分,“我”的看法正是作者對性解放運動那段歷史的思索和審視,這種理性的思考象征著未來的兩性關系將會走上一個新的征程。在當今社會,女性解放運動在每個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據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調查,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一場前所未有的“性革命”,它給整個社會帶來了行為與觀念上的巨大變化,隨之而來的未婚先孕、棄嬰和犯罪事件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目前我國正在全力構建和諧社會,而婦女解放也是構建和諧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作為一個有著深厚文化積淀的國家,如何避免西方低級庸俗文化對女性的精神污染與腐蝕,培養具有主體意識、獨立人格和健康精神生態的新女性,已經成為構建社會主義美麗中國的重要一環。《懷孕的寡婦》對女權主義的形而上的解構告訴我們,在兩性關系中,男女雙方只有自尊、自愛和勇于承擔責任,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女性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才能構建一個兩性和諧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