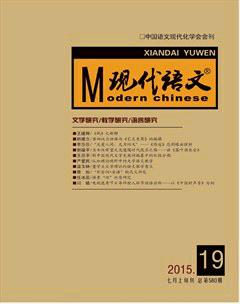唐初權力話語與《藝文類聚》的編撰
摘 ?要:《藝文類聚》的編撰與唐初權力話語有諸多關聯。編撰《藝文類聚》,是唐高祖羅致人才,牢牢控制權力話語,并對前朝官員進行柔性統治的策略。編撰《藝文類聚》,表面是話語爭奪,實質上是權力的爭奪。與興學校、復科舉相配合,編撰類書蘊涵教化功能。編撰《藝文類聚》,是為了弘揚儒學,重新確立儒家經學中心主義話語權力。同時從中也折射出當時歷史的一個側面:唐高祖不是傳統史著所說的庸才,而是一個有著雄才大略的開國之主。
關鍵詞:唐代 ?權力話語 ?李淵 ?類書 ?《藝文類聚》
本文擬將《藝文類聚》置于唐初權力話語之下,對其編撰情況做多方面的考察。
唐武德七年(624年)九月,歐陽詢上書高祖李淵,奏報《藝文類聚》編撰完成。[1]這是中國學術史上值得關注的重大事件。據《舊唐書·趙弘智傳》記載,同修者十數人。至今可知姓名的有六人:歐陽詢、令狐德棻、陳叔達、裴矩、趙弘智、袁朗。《藝文類聚》始撰于武德五年(622年),[2]歷時近三年遂成。唐朝初年,由于隋末戰亂,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生產凋敝,民不堪命。據《通典》稱,隋煬帝大業二年,戶數為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人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而到了唐貞觀年間,戶數不滿三百萬,驟減三分之二。[3]《貞觀政要》記載,“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這些原本富庶之地,卻“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4]這是貞觀六年(632年)的情形,武德年間的狀況可想而知。戰亂初平,百廢待興,唐高祖李淵聚集朝中精英人物,編撰《藝文類聚》這樣一部百萬字的大型類書,絕非僅僅是為了滿足一般士人的平時閱讀。
李淵本是有著雄才大略的開國之主,但是,由于受到兩《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書的歪曲與丑化,其形象被大大貶低。如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對李淵的評價是“昏庸無能”,“并無創業的才干,連做個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5]傅璇琮認為:“唐高祖李淵是一個平庸之主,軍事上主要依靠其子李世民,政治上沒有什么作為,文化上除了編撰《藝文類聚》外,其他也沒有什么可提。”[6]撥開歷史迷霧,綜合有關史料分析,李淵原本不是庸碌之輩,在唐開國之初,政治、經濟均有開創性的實績;大型類書《藝文類聚》的編撰也不是憑空而來,而是與當時特定的政治、文化密切相連,受一定權力話語的支配。
一、羅致人才,在大亂初平之時,牢牢控制權力話語
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七月,時任太原留守的李淵,從太原率甲士三萬起兵,十一月,攻克長安,已達二十萬之眾。次年五月受禪,改元武德,唐朝建立。李淵在短時間內橫掃千軍,勢如破竹,與他能夠廣納人才密不可分。早在準備起兵時,李淵便“懷濟世之略”“經綸天下之心”,廣交各方人士,“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且篤重情義,“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同時,“命皇太子于河東潛結英俊,秦王于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圣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7]太原起兵的要員,多是李淵各方網羅的人才。在攻克隋都長安和后來的統一戰爭中,只要有可能,對在實際活動中能發揮作用的文官武將,以及皇家隸人,都盡力收羅。在武德年間的統治集團中,既有前朝的顯貴,也有起義軍的將領,還有作戰英勇、脫穎而出的下層人士等;才俊云集,各盡其力,各顯其能。
編撰類書,并非僅是收集與編排資料,更需要“慧眼”與“卓識”。參與編撰《藝文類聚》的人員,就已知姓名的六位,均兼擅文史,為朝廷的“一時之選”。這六位編撰者均在前朝擔任過官職,他們在編撰《藝文類聚》時所擔任的官職、品級與當時的年齡分別為:歐陽詢,給事中,正五品上,六十五歲;令狐德棻,秘書丞,從五品上,三十九歲;陳叔達,侍中,正三品,約四十八歲;裴矩,太子詹事,正三品,約七十四歲;趙弘智,詹事府主簿,從七品上,轉太子舍人,正六品上,五十歲;袁朗,齊王文學,從六品上,應在六十歲以上。其中三位為前朝遺老,三位正值壯年。
如何避免前朝遺老在新朝中“水土不服”,如何充分調動和發揮前朝大臣的積極作用,是李淵必須解決和處理好的問題。邀請這些人來編撰類書,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文史之才,讓他們感受到新朝廷的重用。因此,李淵詔令編撰《藝文類聚》,不僅是一項文化建設任務,還是帝王的統治策略,是其加強柔性統治的重要組成部分。《藝文類聚》編撰完成之后,六位主要編撰者依然為新朝發揮著“余熱”:歐陽詢在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令狐德棻負責《周書》及參與《晉書》等史書的編寫,累遷禮部侍郎、太常卿、崇賢館學士等職。陳叔達擔任禮部尚書等職。裴矩官至民部尚書。趙弘智累遷黃門侍郎、國子祭酒等職。袁朗任祠部郎中、給事中等職。正是李淵的柔性統治,使六位主要編撰人員成為唐王朝的中堅力量。
對典籍的不斷編輯與闡釋,可以起到強化王權的作用。《藝文類聚》這部大型官修類書,匯集了各種典籍中的精華,其本身也是帝王實行有效統治的思想源泉。這部具有官方文化色彩的類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帝王對文化傳承的一種壟斷——有利于統治的思想與言論被保留下來,反之,則被剔除。例如,為了配合唐初追求俳縵、駢偶,堆砌雕琢的文風,選文也多于此相合,而一些具有社會意義、歷史意義的作品,如范縝為反對玄學、提倡唯物觀而作的《神滅論》等,反棄置不選。[8]這種由官方壟斷,滲透著官方意識的編撰活動所產生的文本,是經過刻意挑選與遮蔽的,以極其標準的意識形態話語方式呈現出來,權力話語的傾向性十分明顯,最大限度釋放了話語內在的權力。
李淵通過編撰《藝文類聚》的舉措,籠絡了社會精英,使其俯首帖耳地聽從自己的擺布,避免了這些前朝官員產生離心離德的叛逆之舉,牢牢控制了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在唐初政權尚不穩固之時,通過編撰類書,控制了擁有話語權力的士人,有效避免了各種社會思潮的“旁逸斜出”,起到維護穩定、鞏固新生政權的作用。同時,編撰類書及其它圖書,也是戰亂初平之后,文化精英能夠安身立命、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還可以從中找到上升的機會;幾位主要編撰人員在完成《藝文類聚》之后均得到升遷,即為明證。
二、編撰《藝文類聚》,表面上是話語爭奪,實質上是權力的爭奪
在編撰《藝文類聚》這一看似平常的學術活動中,因為有了皇帝的參與,其中便潛隱著權力運作。話語的擁有,意味著對權力的掌控。編撰類書,表面上看是話語的爭奪,實質上是權力的爭奪——唐初的太子之爭。
李淵稱帝之前,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尚能同心協力。天下平定以后,在爭奪和反爭奪太子地位的斗爭中,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的矛盾漸漸明朗化,雙方競相發展勢力,逐漸形成以李建成為首的太子集團和以李世民為首的秦王集團,標志著太子李建成與秦王李世民雙方矛盾進一步激化。在李建成與李世民明爭暗斗的時候,李元吉站在了李建成一邊。
對唐高祖李淵來說,處理皇子們的儲位之爭,是件棘手的事情,所以在太子廢立問題上躊躇不定。武德元年(618年)六月,長子李建成被立為皇太子,但是,在此前后,李淵有三次欲立次子李世民為太子。前兩次是:“上(高祖)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9]李淵進封唐王,是在617年,可見這前兩次欲立李世民為太子,均在建唐之前。第三次是在武德七年(624年)。慶州都督楊文干舉兵反叛,李淵命李世民率軍前往平叛,說:“(楊)文干事連建成,恐應之者眾。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10]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敘述不可信,因為《資治通鑒》是根據被篡改的唐代的《實錄》編寫的。但是在沒有發現其它史料之前,也沒有理由否定《資治通鑒》的記載。有一點可以肯定,即使李淵有過立李世民為太子的想法,其決心也是不堅定的,否則,就不會出現后來的玄武門之變。在《資治通鑒》中還有李淵無意立李世民為太子的記載:“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后,妾母子必不為秦王所容,無孑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11]高祖在立太子的問題上前后態度不一,李世民在即位之后也有所披露:“武德六年以后,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12]李世民的“我不為兄弟所容”的說法,并不一定符合歷史實際,但高祖廢立之心未定之說,卻有史料可以證明。
其實,歷代皇帝在廢立太子問題上猶豫不決,屢見不鮮。不過,李淵在太子廢立問題上的矛盾心理,以及忽左忽右的做法,客觀上也促使雙方的明爭暗斗逐步明朗化。《藝文類聚》的編撰班子是在高祖有意授權給太子李建成時組建的。在現在已知的六位編撰人員中,從《新唐書·袁朗傳》的記載看,屬于太子集團的有三人:領修人歐陽詢,以及裴矩、袁朗;再加上任太子舍人的趙弘智,一共是四人。很顯然,從這個編撰班子的組成人員看,明顯是效力于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并且是為日后太子李建成當朝儲備人才的。雖然隨著玄武門之變,李建成、李元吉被殺,這一切準備也就付諸東流。但是,這種利用編撰類書來網羅人才、組織自己政治班子的做法,還是顯而易見的,是李淵在皇子之爭中所持傾向性的昭顯。
編撰人員的選用,彰顯著兩大權力集團權勢的分布態勢。編撰團隊的一邊倒,是在利益糾葛尖銳對立的狀況下,李淵借以推揚、壯大李世民集團,打擊太子集團的刻意安排。
三、與興學校、復科舉相配合,編撰類書蘊涵教化功能
與興辦學校和恢復科舉相配合,編撰類書《藝文類聚》同樣蘊涵著教化百姓的功能。
據《舊唐書·儒學》和《資治通鑒》記載,李淵即位后,立刻采取興學舉措,恢復國子學、太學、郡縣學等,招收學生。各級各類學校的教學內容,主要是講授儒家經書:“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谷梁傳》各為一經;《孝經》《論語》《老子》,學者兼習之。”[13]據《舊唐書·禮儀制》記載,高祖李淵還駕幸國子監,親自觀看行釋奠禮,讓有學問的道士、僧人與博士互相辯論、問對,表明朝廷對學校教育的重視。
為了改變唐初官員缺乏、選官混亂的情況,李淵在武德四年(621年)四月下詔,參照隋代成法開科取士,明確規定“諸州學士及白丁”“為鄉曲所稱者”,經過縣、州兩級考試,合格者于每年十月再到朝廷應試,[14]解決了生徒和鄉貢的來源問題。武德五年(622年)三月,李淵再次頒布詔書,明確了國家設科公開招考,士人可以“自進”“自舉”的報考辦法,[15]宣告以考試為中心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正式得到恢復。李淵在位時間不長,卻重開科舉,并形成以后每年開科的慣例,實為英明之舉。
關于唐朝初年科舉考試的科目,《封氏聞見記》載:“國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按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試方略策三道;進士試時務策五道。”[16]
興辦學校,重開科舉,與《藝文類聚》的編撰,可謂相輔相成。
從《藝文類聚》的編撰體例上看,它糾正了以往類書偏重類事的缺點,創立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獨特體例,就是為了適應科舉和學校教育的需要。“事”可以供選材、取事之用,是作文資料庫;“文”可供閱讀、揣摩,是范文選本;“事”與“文”兩者有機結合,尋檢起來十分方便,說明《藝文類聚》是為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編寫的參考書。王昌齡《詩格》云:“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17]從中可以看出唐代詩人對類書的依賴,他們大都隨身攜帶類書,以備查用。作詩時,若無靈感,就把類書拿出來翻檢,幫助構思。
從《藝文類聚》“事”的選錄上看,學校教育以儒家經書為主,參加科舉考試,應舉者要熟讀并背誦儒家經典,與之相應,《藝文類聚》“事”的部分,輯錄了大量儒家典籍。
從《藝文類聚》的選文上看,唐初文風沿襲南朝余續,正如《新唐書·文藝列傳·杜甫傳贊》所言:“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18]文士作文時所追慕的對象,是南朝那些重事典與對偶的綺麗文章。科舉取士,特別是進士科,時務策優劣的標準主要看文章辭藻是否華麗。用典繁密、字雕句琢、文辭華美的,就容易被錄取。與之相應,《藝文類聚》輯錄的作品尤以南朝為最多,約2470篇,相當于《藝文類聚》全部選文的二分之一稍多,而其中又以南朝梁的作品被輯錄的最多。南朝文學素以華麗綺靡著稱,《藝文類聚》這樣的選錄標準,是與唐初文學發展的實際相適應的。
編撰類書,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說它是手段,是說類書與學校、科舉一樣,承載著教化的功能。在傳統的閱讀方式下,由于閱讀對象——類書文本的限制,加之當時典籍的匱乏,人們的閱讀視野受到很大限制。閱讀《藝文類聚》這樣的類書,是人們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通過編撰類書,作為文化精英的編者,壟斷、控制了文化的傳承。從類書的文本看,輯錄的材料具有選擇性,因此,人們的閱讀范圍是被事先規定的,也是比較狹窄的。傳統意義上的閱讀活動,是被動的、可控制的,是有固定程式的文化傳承行為,是一種定向的操作程序。在固定的、被動的文本框架內的閱讀,沒有選擇的自由,沒有比較參照,沒有對立思辨,只能在文本所劃定的范圍內馳騁想象,這樣就會不知不覺受到文本的影響,只能就范——以官方的社會意識形態為統一規范,只能臨摹——對前代經典的亦步亦趨地接受。這樣,類書的教化功能,通過編撰和閱讀的雙邊活動,共同完成了。
四、弘揚儒學,重新確立儒家經學中心主義話語權力
編撰《藝文類聚》是奉詔進行的,是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化活動。《藝文類聚》的編撰因此要體現官方意識,顯現權力對話語的必然控制,即要重新回歸自漢武帝以來所確立的儒家經學中心主義話語權力。
“自隋氏道消,海內版蕩,彝倫攸斁,戎馬生郊,先代之舊章,往圣之遺訓,掃地盡矣。”[19]隋末唐初,戰亂之后,儒學衰微,急需重新振興。儒學具有“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政化之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20]的重要作用。
在武力征討天下取得勝利后,人們認識到文治的必要:“武為救世之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圣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舉天下一之于仁義,莫若儒。”[21]這就是說,在用武力取得政權之后,必須用儒家思想來加以治理,才是“百世不易之道”。
作為開國君主,唐高祖親臨國子學釋奠,倡導文教,崇尚儒宗,明確表示他“敦本息末”的意思就是尊崇儒學,以儒家思想治理國家。經過隋朝末年的戰亂,唐初統治者深刻認識到儒學對于維護國家社會秩序的重要意義,積極致力于儒學的復興。《藝文類聚》雖為類書,但它不是機械地照抄、照錄有關資料,而是在材料取舍、體例設置等方面,均能體現出編者一定的思想傾向。在崇儒這樣的大背景下編撰的《藝文類聚》,自然是以弘揚儒學為要義的。
《藝文類聚》以弘揚儒學為要義,首先表現為全書對儒家典籍的大量輯錄。它輯錄的儒家經典,幾乎遍布所有子目。《隋書·經籍志》是唐初編撰的一部國家書目,分經史子集四部排列,著錄的都是當時存世的著作,與《藝文類聚》的編者所見書籍應該大體相同。《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儒家典籍,主要集中在經部和子部儒家類。其經部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圖緯、小學等十類,主要是六經及解經著作;對于六經,《藝文類聚》多有收錄,如收錄《易》54條、《尚書》70條、《詩》194條等。《隋書·經籍志》子部共著錄儒家著作39部(同一書的不同箋疏本未重復計算,亡書未計),《藝文類聚》輯錄其中的22部,占整個儒家著作的56﹪;輯錄的總條目為315條。
《藝文類聚》以弘揚儒學為要義,其次表現在具體類目對材料的選取上偏重儒家典籍。以《藝文類聚》“天部”子目“天”為例,其“事”的部分共輯錄25部著作的片段。分別是:五經及其它儒家著作12部:《周易》《尚書》《禮記》《論語》《春秋繁露》《爾雅》《春秋元命苞》《太玄》《禮統》《廣雅》《說苑》《白虎通》。道家著作4部:《老子》《莊子》《文子》《列子》。雜家著作1部:《呂氏春秋》。法家著作1部:《申子》。醫學著作1部:《黃帝素問》。天文學著作2部:《渾天儀》《靈憲》。史學著作2部:《三五歷紀》《蜀志》。類書1部:《皇覽記》。(筆者按,應作《皇覽·冢墓記》,為《皇覽》中的一個子目或一篇。)楚辭著作1部:《楚辭·天問》。“文”的部分輯錄的詩有晉傅玄《兩儀詩》《天行篇》《歌》,賦體有晉成公綏《天地賦》,贊體有晉郭璞《釋天地圖贊》,表體有宋顏延之《請立渾天儀表》。《藝文類聚》“天部”子目“天”下收錄的著作相當廣泛,但以儒家著作為主,其次是道家著作。
歷代帝王重視儒學,不是對其內容感興趣,也不是真正關心其學術論爭。他們重視儒學,實際上是將其看作整個國家思想文化建設的一部分。唐高祖李淵也是如此。通過類書的編撰,使編撰者成為自覺維護正統思想的中堅力量,構建統治階層的人才梯隊,以便實現長治久安之夢。
經過隋末戰爭,社會的權力布署暫時處于無中心的混亂局面。權力中心的真空以及權力秩序的癱瘓,同時意味著社會對話語權力的失控。唐朝建立之初,即開始編撰大型類書《藝文類聚》,是新興政權針對話語權力散落民間的彌散狀態,所采取的話語權力回收策略,顯示了權力對話語的控制。儒學之所以成為傳統文化中的權力話語,在于儒家話語本身就是王權的產物,與王權有著內在的同謀關系。
五、結語
編撰《藝文類聚》,自然有普及教育、增加社會人群文化知識的目的,但是根本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為了推行王政,進行教化,是權力話語在《藝文類聚》編撰中的反映。《藝文類聚》編撰于改朝換代的唐朝初年,其政治目的就是鞏固統治,標榜文治,以博得偃武右文的美譽;以其內容材料、分類體系、類目設置,來宣揚高祖的正統意識,表明高祖登上皇位是符合天意的,繼承的是正宗的儒學衣缽。
通過以上考察,也折射出當時歷史的一個側面。李淵在建立唐朝前后,不僅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措施,而且興辦學校,尊崇儒學,設置文館,延攬學者,恢復和發展科舉,搜求、整理前代書籍,編撰大型類書;這些諸多舉措足以說明,李淵是一個比較英明的開國君主。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藝文類聚》編撰研究”[項目編號:12YJA87000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王溥:《唐會要·修撰》,中華書局,1955年版,第651頁。
[2]劉昫:《舊唐書·令狐德棻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596頁。
[3]杜佑:《通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3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73頁。
[4]吳兢撰,裴汝誠等譯注:《貞觀政要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頁。
[5]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第三編第一冊),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2頁。
[6]傅璇琮:《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流程》,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第35頁。
[7]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頁。
[8]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頁。
[9][10][11][12]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5957頁,第5987頁,第5959頁,第6117頁。
[13]李林甫等:《唐六典》,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558頁。
[14]王定保撰,姜漢椿校注:《唐摭言校注》,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頁。
[15][唐]李淵著,韓理洲輯校編年:《唐高祖文集輯校編年》,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5頁。
[16]封演撰,趙貞信校注:《封氏聞見記校注》,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15頁。
[17]王昌齡:《詩格》,《全唐五代詩格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18]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文藝列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738頁。
[19]劉昫:《舊唐書·儒學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939-4940頁。
[20]魏征,令狐德棻:《隋書·儒林傳序》,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1705頁。
[2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儒林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637頁。
(韓建立 ?吉林長春 ?吉林大學文學院 ?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