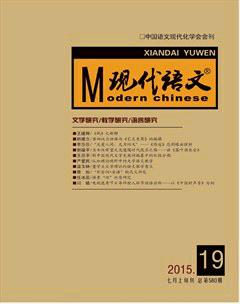萬化歸一是平淡
摘 ?要:蘇軾一生性格堅韌,詩文多種多樣,而且藝術水平極高,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巨人。本文以蘇軾的性格為支點,以蘇軾入黃州作為其人生的分水嶺,略論其詩歌創作思想以及理論的實踐。
關鍵詞:蘇軾 ?詩歌 ?文藝
一、氣岸遙凌豪士前
回顧中國歷史上的文人,蘇軾在詩歌領域,或許并非無人可及,但就文化史來論,蘇軾堪稱第一人,他才學廣博,是中國文化史中一座高峰。
當然,天賦足備的他,還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響,比如說有個好的家庭,父親蘇洵,雖然少不知學,但蘇軾出生后以為必須以身作則,于是學成文章大手筆。母親是“寧為范滂之母”的巾幗,其氣質自然巾幗不讓須眉。《穎濱遺老傳》稱其:“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豐裕家庭或許不是很必要的條件,但確實是成就巨人的有利因素,蘇軾沒有辜負這一家境。
蘇軾少年所學,不在詩詞,只在文章,因而蘇軾詩論離不開文論,古人既稱“詩文”,其創作方式其實有一體化傾向,他自己也說“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答李端叔書》)。他的第一批詩應該收在《南行集》里。北宋考試不考作詩,而考策論,應了這個文化背景,蘇軾文采才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因為身處文化世家,父親的見識又不差,充分發揮了其天賦。蘇軾少年時仰慕“韓,范,歐,富”這些有志氣節操前輩的為人。《上梅直講書》中自述:“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 當然這與母親的啟蒙有莫大關系。另外,父親蘇洵從小教導其學文章,自然有耳提面命的教誨。總之童蒙時代培養出來的氣質,是蘇軾一生無法擺脫的創作思維。蘇軾有志節,且有志于天下。
這種博觀應試培養讓蘇軾的文藝理論形成一個整體,即:一種理論,可用于詩文,同時適用藝術,如:書畫。反之亦然。同時也種下此后一生作詩文為藝術的大的原則:“自然而發”。《南行前集敘》中提到“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闡述了不得已而發,緣情言志的正確詩文寫作方式,就如另一篇《詩論》中所言:“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跡,而下及于飲食、床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又說“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堅決反對為文而文。初入文壇,就有這種造詣,怎么能不成為一代文宗呢?這是歐陽修也認可的,是不易之論。
蘇軾的思想,簡言之“雜且不俗”,性格更是堅韌不拔。
從小接受儒家治世思想,秉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崇尚志節,而且在實踐中很能夠身體力行,自登科后,每次出外任地方官,都政績出色。如在惠州時整頓西湖。知密州時收拾蝗災,知徐州時防水同渠等。貶黃州時改變當地“溺死嬰兒”的惡習。貶海南時,興教育,指導出第一個海南進士。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謀其政,不但謀當時的政,而且力求為人民發展千秋事業,現在西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沒有蘇軾的治理,西湖絕不會有現在的魅力。
蘇軾年輕時讀《莊子》,自言“感覺以前讀過”。說明其人對莊周以及道家思想的認可。這對他從政后起起落落、坎坎坷坷的人生用處極大。
宋初儒釋道三家合流,蘇軾都有截取,豁達的胸襟讓他有了無所不包的思想,蘇軾思想很大程度上秉持“實用主義”,什么時候該秉持什么思想,他似乎很能任意啟用。蘇軾政治生涯也曾有過輝煌,但他一生如意的時候很多么?基本沒有,作為舊黨領袖,他反對王安石新法。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等人要立即廢除新法,他同樣反對。司馬光死后如何,同樣被排擠。后新黨又得勢,他被貶到更遠的海南,而且還是昔日好友的“杰作”(按:當年章惇與蘇軾關系不差,但黨派不在一列,司馬光在朝時,章惇被貶,后心懷記恨,對蘇軾一貶再貶),如王朝云言:“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但無論如何,心懷天下的蘇軾似乎只在行“道”,道,是道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矣!
廣泛地汲取儒釋道三家思想的蘇軾,隱約還有一股倔強在內中生長,沒有這份倔強,為人為文都不夠靈動。在《答張嘉父書》中,蘇軾認為有創新的文,都應給予肯定,“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仆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就是這份倔強,支撐著他詩文的創新,堅決不茍同前人,支撐著他的政治良心,堅決為百姓著想。
二、一入黃州分歲月
蘇軾一生創作的分水嶺應該在黃州一役,生死大難——“烏臺詩案”。這事禍福參半,也是文人一生該經歷的起伏,沒有這一經歷,也就沒有斐然文采。
人生之境遇最是詩材,如曹子健之喪父,“徐庾”之囚北,王子安之刀下被釋,李后主之江南國亡,天地之變的舛難,造就文杰。如果以上這些文人的人生經歷沒有低谷生涯,誰敢保證中國文學中一定會有《洛神賦》《哀江南賦序》《與楊遵彥書》《滕王閣序》《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這些名篇?
蘇軾一生的創作在人生低谷時期頗多,質量也最高。貶黃州時作前后《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寒食帖》《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記承天寺夜游》。
經歷生死大難的蘇軾,登上黃岡赤壁,慨然傷心,“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后赤壁賦》)。若非一群人搭救,蘇軾很難渡過烏臺詩案這一關,但命運就是這么神奇,在獄中的他,連絕命詩都寫好了:“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縱觀蘇軾一生,難得有這樣的傷情句子,早年與弟弟子由“對床許約”定好早早退休歸隱的夢想,現在馬上身首異處,是人都痛心,東坡豈不一樣?出獄后傷心迷茫,頗有自暴自棄之感,《答李端叔書》中說:“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心灰意冷如此。書完最后結尾再說:“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完全驚弓之鳥之態。但他有退縮么?沒有!“塞上縱歸他日馬,城東不斗少年雞”(《出獄次前韻二首》),還得再寫。但從此以后,作文風格立轉,也是無法避免的事。
蘇軾這種性格堅韌的人,在大難不死后,看得更透更開,而非像秦觀一般,一貶就“死”。黃州以前,法“文貴不得為而為”的有為而作,第一是要文意自然噴涌,第二是世道有需,必為世路開道的“有為而作”。黃州后完善整體,尚自然,有“心隱”意味。
三、萬里平沙馳逸力
蘇軾大器早成,平生文采風流。早先繼承歐陽修“詩窮而后工”的創作思想,甚至說得更多。歐陽修《梅圣俞詩集序》:“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內有憂思感憤之郁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蘇軾《邵茂成詩集敘》:“至于文人,其窮也固宜。”文中集中表達了“文人固窮”的思想。
蘇軾少時學文多于學詩,或者可以說只學文,一般認為其作詩在《南行集》,作詞始于熙寧五年(通判杭州),后知密州,詞風為之一振。蘇軾取得功名后開始作詩,所以其對作文的理解,很容易用于作詩,所以蘇軾的詩、文、藝三方思想理論互取互用。如《折枝二首》中有句:“詩畫本一律,天工與自然”就把其結合起來。有宋一代,觀蘇軾可以窺整朝,不能不把這一功勞歸為文論法入詩。黃州被貶前最主要理論莫過于“有為而作”,《鳧繹先生詩集敘》中說:“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谷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儼然接過韓愈、歐陽修的旗幟,繼續吶喊,以儒家入世的精神作文作詩,一肩擔下文章救世的責任。在文章上階段性地戰勝了駢儷文體,詩作中也體現了個中性情,很容易以文為詩。但不同之處在于,其寫詩恰似小孩玩泥巴,輕松異常,隨手取來,雅俗共賞,這一點,是他一生的寫詩追求,也是他性格決定的。正是“涉其流,探其源,采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于文詞,見于行事”(《李氏山房藏書記》)。
同時應該注意,此時理論漸趨成熟,對靈感的捕捉也相當重視,蘇軾說“故畫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對作畫技術的的片刻捕捉,意在學會抓住藝術創作的靈感,對詩文也是一樣。
關于蘇軾作詞,宋人婉約詞風風靡之前,李后主站在朝代之交,有過無意識的創新,在詞中寫國殤。可惜沒有形成風尚。個中原因,暫且不表。
李煜與蘇軾是豪放派詞宗開山創派的人,前者無意為之,在內容上,首次在不登大雅之堂的詞曲中攝入故國憂憤,愛國這種高尚情操開始進入當時的“艷詞”,成婉約旗幟之“愁宗”,于是詞的格調驟然直上。蘇軾則有意為之,在《與鮮于子駿書》中,蘇軾說:“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也曾批李后主說:“后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于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后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東坡志林》),稍看不起其行為。蘇軾做事倔強,作文作詩孤標塵外。在詩文詞中表現出來即是創新,想要跳出婉約風格的籠子,無論最后成功與否。不可否認,這種有意識的創新尤其可貴。最重要的是在遣詞用句上做了探索。但豪放詞作品實在不多,大概全部詞作的十分之一,而且有些詞還豪放婉約風格參半,如著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
另外,蘇軾做婉約詞不輸宋朝諸公。如《水龍吟(楊花詞)》《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等。其實詩詞文學必須是抒情,如果不是非常雄健豪邁,很容易走上婉約風格。更何況,從蘇軾所處年代和其經歷及歷史背景等因素來看,并不完全具備豪放詞寫作的條件。有宋一代,基本都在外族入侵的噩夢中度過,蘇軾又非武將,不可能有盛唐氣象那種產生“邊塞詩”的環境。盛唐邊塞詩尚且有“悔教夫婿覓封侯”的閨怨,何況宋代?
李煜的開拓是不著痕跡的,無可奈何地加入國家情操,毅然為詞作“神品”。蘇軾則全然實踐理論,所以辛棄疾出,豪放詞大放異彩,蘇軾功勞在前。
四、人生到處是從容
經歷烏臺詩案的蘇軾,對人生政治理想看得更透,可敬的是看得更透以后,無論為人、為文仍然初心不改,始終如一。而后被貶海南瓊州,他的人生或許又生波瀾,但總能認清自己,豁達開朗地接受命運的安排。一個人的可敬之處在于,他是人不是神,卻被神化,但是當你把他請下神壇的時候,他依然如神一樣可愛。
烏臺詩案后蘇軾在《答李端叔書》表達自己對待功名如何貪得不已,從政如何不諳世事等一些自暴自棄的話,宛如驚弓之鳥,頗有心灰意冷的感覺,但也只是口頭講講,沒什么具體的自暴自棄行為,反而更加堅定,不易初心。后面無論拜相還是被貶更遠的海南,都如同旅游一般,我們說蘇軾是人,不是神,他也會迷惘傷心,發出“寂寞沙洲冷”“人生如夢”的慨嘆,但從小堅韌的性格支撐起了他人格的魅力。
自貶黃州以后,蘇軾的人生換用道家那種豪邁應付,文藝上也漸趨自然平淡,并且更加注重這方面的修養,在《書吳道子畫后》中說:“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游刃余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對自然之法的贊嘆,評價為古今第一人。更在《答毛澤明書》中表示,不但自己寫文章要自然為之,評述文章品目高下也應該“付之眾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自然之道,大浪淘沙,眾人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為文如此,為人也一樣。新黨再次得勢后,蘇軾被一貶再貶,最后到海南渾然像去旅游,不過其生活艱苦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但如論如何,心情是最重要的。這些日子的詩作如《食荔枝》《縱筆》,盡顯悠游人生。
在《謝民師推官書》中說:“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大力贊揚自然。如這時《汲將煎茶》都是這樣。另一個很重要的舉動是在海南期間的《和陶詩》,蘇軾晚年為詩尚自然,對陶詩非常喜愛。他說“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東坡題跋》卷二)。早年說“為文固窮”,在晚年時候找到這樣五六百年前的文章知交,心里怎么能不愉悅,所以把陶詩一首一首和了一遍。可見陶詩對蘇軾的心靈慰藉非常之大。
在蘇軾迎來人生又一個幸運階段,被釋回京的時候,他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東坡集(卷四十三)》:《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又是人生的一場旅游,沒什么好抱怨的,旅游完了就該振作起來做正事去了。在總結自己一生經歷與文章經驗的時候,他說“凡文字,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彩色絢麗,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平淡,絢麗之極也!”(蘇軾軼文匯編》卷四 :《與二郎侄書》)。蘇軾少年老成,文章才華頂尖,少小時自然掩飾不住崢嶸之氣,而這個詞,用來形容蘇軾早年,再恰當不過。但人生的歷練總歸是由張揚到平淡,諸葛亮說“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正是道家一種“不爭之爭”的大爭體現。再如陶淵明所講“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蘇軾當年如沒有這樣情操也,不可能成就他自己的偉大。處世從容,萬化歸一,平淡是人生真諦。
參考文獻:
[1]曾棗莊,曾濤選注.三蘇選集[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2]孔凡禮.蘇軾年譜[M].北京:中華書局,2005.
(陳玲玲 ?浙江寧波 ?寧波大學 ?31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