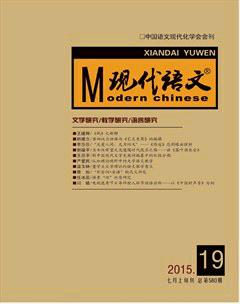《穆斯林的葬禮》中的愛情悲劇及其原因分析
摘 ?要:《穆斯林的葬禮》描寫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不同的愛情故事,經歷的不同的命運變幻。文章講述了梁家第二和第三代人的愛情悲劇,展示了他們愛情悲劇的延續與變化,并揭示了造成這些悲劇的原因,深刻地展現出文本蘊含的悲劇力量。
關鍵詞:愛情故事 ?悲劇延續 ?原因分析
《穆斯林的葬禮》描寫了一個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間的興衰,三代人的命運沉浮,兩個發生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形態卻又交錯紐結的愛情悲劇。小說以獨特的視角、真摯的情感、豐厚的容量、深刻的內涵、冷峻的文筆,深情回望中國穆斯林漫長而艱難的足跡,揭示了他們在華夏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撞擊和融合中的心路歷程,以及在特定的時代氛圍中對人生真諦的困惑和追求[1]。
一、韓子奇的愛情悲劇
梁家第二代的愛情故事是關于韓子奇與梁君璧、梁冰玉倆姐妹之間的情感糾葛。師傅梁亦清的突然離去,使這個家失去了支柱,也使韓子奇與梁君璧的結合成為理所當然。他們的婚姻有愛,但更多的是責任。韓子奇作為梁亦清唯一的徒弟,并且在這個家生活了那么長時間,他們之間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這份養育之情他應當報答。當梁君璧讓他娶她時,他沒有反對,并且他們的婚姻遵循了伊斯蘭教規。雖然沒有應有的聘禮和隆重的婚禮,但他們心里是感到幸福的。這一方面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愛是兄妹之間的情感,具有報恩性。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他們的愛情是得到承認的,并且在之后的生活中這種感情一直都在。所以,韓子奇對梁君璧的愛無可否認。然而他們的愛情本身就存在著矛盾,這也推動文本情節的進一步展開。
抗日戰爭爆發,韓子奇到英國去避難,在此期間與他相伴的人是梁冰玉。無情的戰爭,陌生的異國生活,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冰玉曾經所經受的情感創傷,使她需要一個值得信賴的人。而韓子奇內心沉寂的愛也被喚醒,玉兒的獨立、開放、知性,讓他體會到了真正的愛情,他們的結合看似偶然卻又順理成章。他們的愛情雖然在道德面前碰了壁,但讓心靈綻放了光芒。可是,人生不是一場夢,夢醒之后可以忘記,而人生不可以;人生也不是一部書,書成之后還可以刪改,而人生不可以,人生從來沒有藍圖。度過了人生,才完成了人生。歷史從來都是即興之作,你不能改變它的曾經存在,也無法重寫。一切都過去了,一切都留下了[2]。十年過后,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軌道,舊日的兄妹之情仍以夫妻的形式存在,如今的男女之愛則要以兄妹的面目出現——愛被命運排錯了位置[3]。如果說韓子奇離家十年的過程是他理想愛情實現的過程,那么當他回到以前生活的現實中時,這種理想也就破滅了。雖然在伊斯蘭教教義中允許一夫多妻,但禁止娶兩姐妹,當韓子奇和冰玉回到他們朝思暮想的家時,還沒來得及享受重逢的喜悅,就將面對這艱難的抉擇。璧兒不會選擇離婚,也不會選擇接納玉兒,她的信仰不允許她這么做。她的那一巴掌不是為了自己打的,而是為穆斯林打的,為她所堅持的崇高的信仰打的。韓子奇在事業與愛情的面前,選擇了自己癡迷的玉器事業,選擇了留在這個家而沒有跟隨玉兒遠走他鄉。他的懦弱和沉默,迫使玉兒離開,也讓他和璧兒的婚姻名存實亡。玉兒堅持著自己的人格和尊嚴,堅持著自己對于真愛的追求。她的放棄不意味著失敗,即使傷痕累累,她寧愿保留理想中愛情的完美,也不愿讓殘缺的愛在現實中茍延殘喘。在這場三個人的“戰爭”中沒有勝者,留給我們的是滿目瘡痍的愛情。
二、韓新月的愛情悲劇
梁家第三代人的情感經歷主要是韓新月和楚雁潮的愛情悲劇,他們的愛情既受到上一代人愛情糾葛的影響。又有著自身的悲痛。新月是梁冰玉的女兒,卻生活在梁君璧家,她所得到的母愛沒有溫暖,但她依舊對生活充滿了熱愛。當她如愿踏進北大的校園時,卻意外收獲了自己的愛情。她和楚雁潮老師最初只是師生之間的關心與交流,隨著不斷接觸,他們共同分享對文學和音樂的喜愛,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拉近了他們的距離。之后新月被查出患有心臟病,他們之間的交往增多,感情也漸漸顯現出來。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但韓太太卻棒打鴛鴦,將他們強行拆開。這種傳統的“棒打鴛鴦”的悲劇模式中,愛情的反對者一般是實有其人,如《白蛇傳》中的法海、《牛郎織女》中的王母娘娘、《梁山伯與祝英臺》中的祝父,而在《穆斯林的葬禮》中它虛化為一種宗教力量——回族不能與“卡斐兒”結婚的伊斯蘭教規[4]。其實,對新月來說更可怕的是這種教規已內化為自己“母親”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處事原則。在新月生命垂危之際,韓太太依然堅決反對她與楚雁潮的愛情,她寧可讓新月死也不愿丟人現眼。面對阻礙,楚老師沒有退縮,他愿意信奉伊斯蘭教,但還是沒能打動韓太太。沒有了生活的期盼,愛情的希望就要破滅,生命的花朵就要凋零。這讓人想起《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她們的處境都可謂“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環境的壓迫使得她們一步步向現實退讓,最終都抱恨而終。黛玉臨終前所說的:“寶玉,寶玉,你好—……”和新月用生命最后的力氣,等待天亮,等待她所愛的人,但只留給我們一個字“楚……”有異曲同工之妙,都向我們傳達了那還未來得及言說的愛。新月走了,帶著遺憾、傷痛。穆斯林的葬禮,神圣、純潔、莊嚴。它不僅是新月的葬禮,也是整個家族的葬禮,整個故事的葬禮。韓新月和楚雁潮,是為了真愛而活著,他們的愛情可悲,可嘆,但又可敬!就像作者所說的“我覺得人生在世應該做那樣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劇,悲劇,也是幸運的。因為他畢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經歷的對自己心靈的冶煉過程,他畢竟經歷了并非人人都能經歷的高潔、純凈的意境。人應該是這樣的大寫的人[5]。”
三、悲劇原因
小說中的悲劇,是美的價值被毀滅的悲劇,是兩種文化碰撞的悲劇,是固步自封的民族文化的悲劇。造成上述愛情悲劇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宗教信仰
韓子奇與梁冰玉愛情悲劇的產生是因為宗教信仰的束縛,而新月與楚雁潮則是因為宗教信仰的不同,被民族分歧拆散。可以說他們愛情理想的破滅,都與宗教信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們都曾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愛情理想,都體會到真愛的滋味,但最終卻沒有實現“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愿望。《荊棘鳥》中也寫到了宗教束縛下的愛情。主人公梅吉與拉爾夫教士的愛情之路布滿了荊棘,充滿了疼痛。梅吉堅強而美麗,拉爾夫高大而優雅,他們真心相愛但卻因為教士不能結婚而無法在一起。梅吉對抗的是上帝,她想從上帝的手里搶奪拉爾夫,結果注定失敗,雖然她從來不曾放棄[6]。楚雁潮堅定執著,為了這份愛情愿意信奉伊斯蘭教,拼盡全力卻終抵不住生命的脆弱,也無法改變新月從出生起就是穆斯林的事實。梁冰玉,經受了新思想、現代文化的洗禮,在與韓子奇的愛情中表現出果斷與愛憎分明,充滿女性自覺意識[7]。她為真愛也進行了抗爭,她不介意韓子奇是她的姐夫,卻觸犯了伊斯蘭教義,被迫離家出走,遠離自己心愛的男人和女兒。在小說中,楚雁潮對愛情進行抗爭的這份勇氣,讓我們看到上一代人未能堅持到最后的愛情,在下一代人身上卻進行到底,他們的愛情敢于掙脫宗教的束縛,將心靈之愛演繹得淋漓盡致。讓我們在悲傷的同時也感到欣慰,雖未開花結果,但那種抗爭的精神卻可歌可泣!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文化的融合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要求,對于各民族宗教文化的束縛我們要敢于去抗爭,打破各種文化之間的狹隘偏見,以求得各個民族之間的融合。
(二)封建家長制
這部小說向我們展現了梁君璧這一封建家長的典型。對于新月,雖不是親生的但她也養育了這么多年,作為母親,女兒的情感生活她有權利干涉。新月與楚雁潮的愛情,一方面是老師和學生之間的交往,另一方面是卡斐兒和穆斯林的碰撞。無論哪一方面,都是梁君璧所不能夠接受的。她企圖用自己的傳統的封建權威來塑造新月,拒絕她的獨立與自由。新月受到過新思想的影響,她想沖破束縛找到真正的自我,這就造成了她們之間的沖突。最終,新月與楚雁潮的愛情還是被封建家長制壓垮。梁君璧身上帶有很強的控制欲,打著母愛的旗號,醉心于權力的享受之中,即使這樣也無法抵制她生命的空虛,無法阻擋她人格的異化。最終,他們成了封建禮教的殉葬者。在其他的文學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封建家長制對于社會發展、人類精神文明進步的阻礙作用。比如,《金鎖記》中的曹七巧對兒女情感生活的破壞。她不想和別人共同分享兒子的愛,對兒子的婚姻進行破壞,導致兒媳婦的死去。她害怕女兒擁有自己渴望得到卻從未得到的愛情,便親手斷送了女兒長安的幸福未來。她病態的發泄與報復,也使自己走向了毀滅。
(三)個人性格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由此可見性格因素對小說中人物命運有著巨大的影響。在小說中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特征,我們無法去責備他們性格的好與壞,要知道人無完人,或許正因為這樣,才更增添了小說的悲劇色彩。作品中刻畫的性格最為鮮明復雜的人物形象是梁君壁。她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少年時代,她敢于沖破世俗觀念,勇敢地以身相許,并發誓幫韓子奇重振奇珍齋。可是當她成為女主人之后,便逐漸成為一個恪守教規、乖戾封閉、保守冷酷的女性。在發生丟寶事件后,她狠心地辭退了為奇珍齋立下汗馬功勞的老侯,令其全家生活無著;在博雅齋時代,她出于世俗的功利目的,一手包辦了兒子天星的婚事,使兒子痛苦莫名;出于狹隘的宗教觀念,她硬是拆散了女兒新月與楚雁潮這對有情人;出于情仇和嫉妒,她不能容忍妹妹與丈夫的關系,終于使他們心力交瘁,各奔東西。與此同時,小說也展示了這個人物性格的另一面。她盡心撫養新月,收留海大嫂,對兒子傾注愛心,就是對丈夫韓子奇,她也盡到了為婦之道。通過對這個人物復雜性格的描寫,體現了作者對人性的深層揭示。不僅如此,作者還進一步剖析了堅持穆斯林宗教信仰和傳統道德觀念的梁君璧這個形象的文化內涵。在不斷變化的時代文化的撞擊下,她徹底失敗了。不但兒子沒有得到幸福,女兒新月早夭折,丈夫孤寂地死去,而且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與她共同生活幾十年的丈夫并非一個純粹的穆斯林,而他們的兒子自然也不再是純粹的回族了[8]。
朱光潛先生說:“悲劇比別的戲劇更容易喚起道德感和感情,因為它是最嚴肅的藝術。”[9]《穆斯林的葬禮》向我們展示的是一個包含了兩代人的群體性的愛情悲劇。通過對這些愛情悲劇的描寫及原因的揭示,我們深刻體會到文本中的悲劇力量——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注釋:
[1]霍達:《穆斯林的葬禮·內容簡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2]霍達:《穆斯林的葬禮》,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3]周顯峰:《愛的毀滅與延續——淺析<穆斯林的葬禮>主要人物的命運》,文學自由談,2011年,第11期。
[4]夏金蘭:《在夾縫中生存的愛情——淺談<穆斯林的葬禮>中的愛情悲劇》,安徽文學(下半月),2013年,第11期。
[5]霍達:《穆斯林的葬禮·后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
[6]宋潔,張虹,劉麗敏:《宗教與愛情——<荊棘鳥>與<穆斯林的葬禮>之比較》,學苑擷英,2010年,第7期。
[7]胡進:《悲劇人生中的命運和情感捉弄——讀<穆斯林的葬禮>》,北方文學,2010年,第5期。
[8]王慶生:《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9]朱光潛:《悲劇心理學》,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趙軍榮 ?河南開封 ?河南大學文學院 ?475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