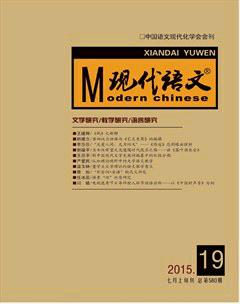董學文文學理論的語文教學意義
摘 ?要:董學文文學理論研究對于語文教學有以下幾方面的意義:第一,對語文教學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關系能有較好的認識;第二,課堂教學結構能力的培養,是閱讀教學、作文教學的教學結構設計的基礎;第三,在語文教學知識的新舊轉換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董學文文學原理為語文教學中語言和文學關系的處理開辟了新的視野。
關鍵詞:董學文文學理論 ?課堂教學結構 ?新舊轉換
當今語文教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學界對語文教學的認識、語文教學的方法都存在爭議。如何看待這些爭議,新舊語文知識、語文教學方法之間如何過渡,尤其是該怎樣認識語文教學中的工具性與人文性?研究董學文先生的文學原理有助于順應語文教學的發展,深化對語文教學的認識。
一
語文教育中語言教育和人文教育之間關系是怎樣的,該怎樣認識語文教學中語言教育和人文教育?這是語文教育百年來的難題。從目前的一些語文教學法來看,有兩種傾向,一種傾向于語言,一種則傾向于人文。傾向于語言的學者認為后者只教中心思想,沒有顧及語言知識的教學要求;傾向于人文的學者認為前者把語文肢解了,沒有顧及語文的審美體驗。
這兩種觀點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完全可以辯證地思考。馬克思說過:“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1](P533)因此語言既是交流的工具,具有知識性;也是對社會的反映,因為反映中帶有社會的特點和反映者自身的特點,因而具備了人文性。這二者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無法分開。例如文革的語言,如今基本已經成為一種古董語言了,失去了工具性,也失去了對人感化的力量——人文性了。
一般來說,語文中閱讀教學總是按照字、詞、句、段、章、篇、語法、修辭、邏輯的方式進行教學,因此也有學者認為這樣的教學很破碎。把完整的文章割裂成破碎的語言知識,這就需要對教學流程的設計重新思考。而推動這個文章分析方式轉變并進而建構新的語文課堂的,正是當代文學理論的變化。從閱讀教學的情況來看,與閱讀教學課堂結構關系最為密切的文學理論教學內容是文本理論。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文本理論,就有什么樣的課文分析模式,相應也就有怎樣的課堂結構。所謂課堂教學結構就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相對穩定的諸教學要素的組合方式及教學活動系列”[2](P142)。這是語文教學設計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直接關系到語文教學的質量,一直都是以文本理論作為基礎的。
我國傳統的文本分析模式是“內容”與“形式”兩分的文本分析方式。文學作品的“內容”“是指通過塑造形象、生動地反映作品中的現實生活及其所包含和體現的作家的思想感情”[3](P86)。其要素主要是題材、主題、情節等。在傳統的語文教學中,對主題的分析是不可缺少的,這個過程就是歸納中心思想的過程。一般來說,中心思想的講解需要到小學五年級以后才開始,但低年級的學生也會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主要表現為人文思想的熏陶,借助課文教學生怎樣做人。文學作品的“形式”是“指作品的內部結構、表現手段和外部形態的有機組合”[3](P88)。主要由語言、結構、表現手法等要素構成。這種文本分析方法作用于語文教學,就形成了我國目前比較成熟的語文教學方法——講讀型教學方法。在小學階段其具體的教學過程是:“揭示課題-閱讀全文-劃分段落-概括段意-提煉中心-復述練習-進行小結-布置作業。”[4](P139)在初中階段則減少了字詞學習的時間,增加了課文藝術表現手段學習的環節。這種教學流程的設計是從語言到文學的學習過程,是從字、詞、句到段、章、篇的學習過程。其優點是有利于學生對語文知識的系統掌握,缺點是把課文分析得太零碎,缺乏整體感。而且對于文章“中心”的學習有“知識化”的缺陷,在學生思想品行的塑造上往往起不到作用。
“內容”和“形式”兩分的文本劃分方式對于文學文本有些難以說清楚的現象。有學者認為:“這種觀點直接把哲學范疇變成文藝學范疇,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說明文本的某些問題,但往往有忽視文學特殊性的一面,始終難以準確地描述文學文本的存在方式和構成方式。”[5](P95)在西方現象學文學理論的刺激下,出現了“言、象、意”三個層次的文本分析方法。“言”就是文學語言,是“用生動的感性外觀和豐富的理性內蘊體現文學審美意味的意象語言”[6](P35)。“象”是文學形象,指“作家以語言為物質媒介,依據自己的體驗和理解,對生活形象加以藝術概括,創造出來的具有情感因素和審美感染力的生活圖畫和具體情景。”[6](P39)這種界定對“形象”的范圍進行了擴展,在原來的“人物形象”的基礎上擴展為包括意境、意象在內的文學形象。“意”則為意蘊。相應地出現了新的語文課文文本分析方法,如整體式的語文教學方法。其具體的教學側重點有以下幾個方面:1.感受閱讀樂趣;2.豐富閱讀活動;3.注重閱讀體驗;4.學會多種讀法;5.提倡多角度有創意的讀。[7](P114-118)這種教學方法承認文學文本的意蘊的無限豐富性,發掘文學形象的美,并利用文學文本的這些特點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讓學生感受美、體會美、領悟善。
這就從教學結構角度避免了語文教學過于零碎的現象,為語文教學從美的角度入手進行教學提供了可能。
二
當然,要更為科學地解決語文教學中語言知識和人文教育之間的關系,我們得對這兩種關系做更為細致的探討。董學文先生的文學原理卻提供了這樣一個解決問題的理論知識。要解決這個問題先要搞清楚語言和文學的關系。一般說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但語言在什么情況下成為了藝術,這是一個難題。從董學文的《文學原理》來看,“文學符號首先作為語言符號存在,意味著在感受這種符號的同時,必須注意其藝術涵義的達成過程。”[7](P206)其藝術涵義達成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是語音,文學語言通常都有韻律,這種韻律既來自于作者的情思通過比較有效的語言組織顯得高低錯落;其次是語義文學語言往往強調情感,信息性不強;再次是形象,文學形象和科學形象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直觀、傳遞作者當時的審美狀態,而后者則是客觀的狀態。由此,我們可以深入一步思考語文教學中的這個難題。我們可以以抒情文學為例。
從抒情文學來看,其語音、語義、文學形象都有語言和文學之間的辯證關系。
從我國古詩的情況來看,詩歌中生字、新詞是語言知識,但詩歌語言的組合形成的文學節奏卻是文學知識,詩歌中單個詞語解釋是語義知識,但作為語象在詩歌中整體的作用卻是文學知識。詩歌的形象和科學的現象有區別,但詩歌卻需要對生活中真實的現象進行還原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形象。例如《送孟浩然之廣陵》,全詩沒有一個字寫情,但卻讓人無比感動,原因就是這首詩是景中藏情。“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一句,明寫長江,實際是寫詩人目送著友人的船遠去。他依依不舍,直到看不見了還不忍離去,只看到長江之水滔滔滾滾,而他自己內心的一腔離情也如這滾滾長江,起伏不定。
從作文教學的情況來看,這兩者之間的關系也是很微妙的。從作文的根本目的來看,作文教學也是教育的一種方式,是培養人的。因此作文教學的首要目的是讓學生學會生存。在這基礎上對學生的人格等方面進行建構。因此作文最根本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的信息發布能力,使其具備生存能力。但是從教學對象、教學方法的角度來看,學生更傾向于情感的表達,更喜歡作文的美。這也就是語文的知識性和人文性之間的矛盾。
我們現行的語文課程標準,看似降低了作文寫作的難度,在時間的限制上,在表達的長度上降低了作文教學的要求,但對學生真情實感的要求卻增加了。也就是說現行的語文課程標準降低了作文知識的難度,提高了作文人文培養的難度。但其實,要寫出真情實感是不容易的。自古人們對這個問題就有闡述。劉勰在《文心雕龍》就神思的情況談道:“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言不達意,是學生作文中的普遍現象。雖然學生作文大多是寫實性的,但是要寫出真情實感其實是需要考慮語言與人文之間的關系的。這里涉及到許多問題。
首先涉及的是內在的“意”怎樣轉化成外在表達的“文”。首先是習作構思,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習作構思的過程可以從以下幾個角度思考:“第一,表象操作……第二,抽象邏輯思維……第三,情操和想象對思維制約的加工……第四,內部語言的形成”。[7](P147-150)內部語言形成的過程從文學理論的角度來看,涉及到素材轉化成題材的努力,這是一個把零散的素材轉化成有聯系、有條理、有社會意義的材料的過程。這個過程在學生作文中困難很大,需要老師的點撥和指導。從最近一些名師的作文教學情況來看,他們的成功其實就是這步工作做得好,降低了作文的難度。例如,上海特級老師賈志敏是通過小品使素材轉化為題材;浙江特級教師張化萬是通過有邏輯聯系的生活展示來達到這一效果。往深一步說,這個過程是一個用普通話理解生活的過程,既涉及到語言知識的學習,也涉及到人文精神的培養。
內部語言外化也涉及到語言知識和人文精神之間的問題。這個過程有“體裁對內容的征服”[5](P281),語言對內容的征服”[5](P283)。前者是文體知識對語言的組織,散文、議論文、說明文對語言的組織是不同的。后者是語言把人文精神固化的過程,使作文有一個完整的中心。此外,作文修改的時候要考慮內部語境向公共語境轉化的問題,這就可以避免學生作文思路不連貫等問題。
三
董學文文學理論在語文教學新舊轉換中意義也很重大。
新舊語文教學方法,以及新舊語文教學的要求對文學理論等造成的困惑是明顯的。高教出版社出了一本《文學概論》專科教材,把這兩種文本的存在方式放在一起(既講內容和形式,又講作品層次論),其中重復、矛盾的地方,不可勝數,顯得不倫不類。據說是為了“‘前瞻性與‘穩妥性相結合。”[8](P5)從“教”的角度來看無可厚非,但是作為體系化的理論就顯得編者無能力消化不同理論。深層原因是新舊兩種理論需要調和在一起必須有新的文學理論的架構,而恰恰在這里,這本文學概論的編者缺乏開拓能力,于是也只好新舊雜陳,將就著用吧。
從這個角度來講,董學文先生的文學原理研究無疑對前沿的文學原理和新潮的文學原理融通、交匯有很大的貢獻。他主編的《文學原理》把以前的文學理論教材中屬于“內容”的題材、主題等放在“對象的構成”這一節,而將其新潮的關于文本的結構層次放在第四章“文本的結構”這一節。這樣就各得其所。當然這也有困難之處,什么是文學客體?首先,“客體”這個詞來源于哲學,從哲學到文學理論要經過怎樣的處理?在這里,董學文給出了廣義和狹義兩個定義:“就廣義而言,可以理解為給人(即意識形態與思維的主體)提供意識與思維的前提與材料的整個客觀世界,它在整體上制約著人類的思維與意識,而文學就是作家思維意識活動的產物,所以它對文學的影響自不待言。就狹義而言,由于文學是以人為中心的社會生活為主要書寫對象,所以,嚴格地說,文學的客體主要是指豐富多彩的人類生活。”[6](P80)把文學看成是生活的反映,這是認識論體系一貫的觀點,對此做出引申,生活是寫作的客體也水到渠成,關鍵是對“生活”和“寫作主體”之間的關系進行科學地闡釋。畢竟文學來源于生活,但不同于生活。生活真實要經過藝術概括而變成文學真實。而“寫作主體”與“生活客體”之間的關系,也不是簡單的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或者能動反映的關系,而是“制約與超越”的關系。這不是簡單的標新立異,而是有哲學和心理學依據的,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文學是一種意識,是對生活客體的反映,它受制于生活客體,但是“人的意識不僅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造客觀世界。”[6](P228)這也是面對相同的客體會有不同的文學的原因。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可以從皮亞杰那里得到印證,主體感知客體時總是習慣性地將其納入自己的認識模式,加以整合,這是“同化”,但是人們認識的心理模式也會不斷變化,主體在整合同化客體時,又受到客體的影響,那就是“順化”。
文學對象區別于文學客體,那就是它是文學表現的對象,因此它不像生活客體外在于文本,它實際上已經進入了文本,因此文學對象既和內容相關,又和內容不同。按董學文的研究,傳統中常見的內容的三要素中,“題材”和“主題”屬于對象,“情節”則不屬于文學的對象。而文學史經常出現的“主題”則成為“母題”。“母題”的提出似乎是對原型理論的超越。
他的《西方文學理論史》也可以對語文教學法做開發性的研究。這個我們在《文學鑒賞與語文教學專業能力的培養》一文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翟啟明:《新課標語文教學論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3]曹廷華:《文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吳忠豪:《小學語文課程與教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顧祖釗:《文學原理新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董學文,張永剛:《文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7]倪文錦:《小學語文新課程教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8]劉甫田,徐景熙:《文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溫玉林 ?廣東羅定 ?羅定職業技術學院教育系52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