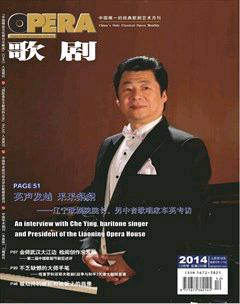被劫持的郵輪和地板上的肖像
司馬勤



上個月,我特別調整繁忙的國際行程,刻意騰出時間,確保自己可以觀賞紐約演出的《克林格霍芬之死》(The Death ofKlinghoffer)。很多人想說服我別去看演出,他們的作為反而激發我必須去看個究竟。
幾個月前,我在這個專欄里曾經提到大都會歌劇院決定取消原定的《克林格霍芬之死》高清現場直播(Live in HD)——這個妥協構想拙劣,目的是為了平息一些猶太組織批評歌劇有“反猶太”意味的指控。大都會歌劇院總經理彼得·蓋爾伯(PeterGelb,請不要忘記他也是猶太裔)當時聲稱,他作出這個決定,是為了避免給歐洲的反猶太運動火上加油。可是,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更顯得像蓋爾伯當時希望倉促了事。不讓任何事情令他分心——他那時的當務之急,是大都會工會威脅罷工的危機。要是真的罷工的話,大都會歌劇院的整個演出季,不只是《克林格霍芬之死》就全都變成泡影。
最終,工會沒有罷工。事實上,工會成功地爭取到他們大部分的要求;蓋爾伯到頭來更像一個被迫退讓的弱敵。這些事實,都可能導致后來反對《克林格霍芬之死》運動的連環炮轟。
讓我們重溫一下——也讓我舊事重提——這部歌劇當年在紐約首演(那是23年前的事了,當時我也在場)沒有引起什么爭議。是的,某些人感到不滿,因為故事描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阿基萊·勞倫號(AchilleLauro)郵輪,以及因病坐在輪椅的里昂-克林格霍芬(Leon Klinghoffer)被殺的情節,這些都是史實。當時,克林格霍芬的遺孀與女兒聲稱,她們不希望自己的家族悲劇,每天每晚都重演在買票觀眾們的面前。可是事實上,除了幾個激進作者撰文批評歌劇故事取材,沒有很多的反對聲音。
一直以來,這部歌劇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演出,都沒有引起什么麻煩。搬演在大都會歌劇院的制作由湯姆·莫里斯(TomMorris)執導,年前在倫敦英國國家歌劇院早已演過。大家恐怕低估了美國如何看待變幻無常的中東政局,尤其是2001年“9·11”恐怖事件直至本年在加沙地帶(Gaza)發生的領土沖突。
如果蓋爾伯以為取消《克林格霍芬之死》高清直播可平息抗議人士,他的想法大錯特錯。抗議團體在大都會演出季開幕那天開始,在場內外就擾攘了無數遍,盡管開幕選演的劇目——詹姆斯·萊文指揮莫扎特《費加羅的婚姻》——與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或者美籍猶太裔被害者都拉不上一丁點關系。直至《克林格霍芬之死》首演當晚,輿論越見激烈。某些參與演出的藝術家說,他們甚至接到威脅的訊息。蓋爾伯更被指控,說他接受恐怖分子在金錢上的資助。喜歡在媒體曝光的政客也乘虛而入——他們包括紐約前市長魯多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前紐約州州長大衛·帕德遜(David Paterson)、現任皇后區區長美琳達·卡茲(Melinda Katz)。可是,這些發言人沒有一個真正知曉這部歌劇(其中卡茲的言論最為荒誕:她“個人對這部話劇感到被冒犯”。她難道不知道這是一部歌劇?)。
所以,自問在眾人喧囂之中,我怎能錯過《克林格霍芬之死》呢?抗議行列之中,沒有幾個人看過這部歌劇!正如香港近期的街頭集會受到多方面譴責,我只愿意相信那些身體力行、親身經歷過這場運動的人所說的話。正如香港的那些群眾集會,我等待首演后幾天,自發性地到實地看個究竟。
大部分《克林格霍芬之死》的樂評。都仔細地論述了大都會首演的情景。當晚,有不少人在場外聲討抗議,他們試圖打斷演出的過程。這些評論差不多全都正面,大部分人贊嘆歌劇院堅持并成功地把作品搬到紐約的舞臺上。
我踏進大都會歌劇院看演出的那天,反對《克林格霍芬之死》這個運動已經被削弱了,抗議團體那種只圖私利的虛偽已經原形畢露。因此,來看歌劇的觀眾終于可以平心靜氣地、不折不扣地觀賞演出。只可惜,整體的演出令我感到失望。尋根問底,失望源自演員陣容,因為在我的腦海里,23年前的原班人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大都會請來了艾倫·奧佩(Alan Opie)這位男中音擔任男主角,他也算勝任;但是,多年前參與首演的桑福爾德·西爾樊(Sanford Sylvan)的精湛演繹,簡直就是克林格霍芬的化身,顯露出這個復雜人物的多重矛盾。20多年前的記憶可能退化,但西爾樊也是英國導演潘妮·烏爾科克(Penny Woolcock)專門為英國第四(Channel 4)電視臺執導的歌劇電影版本的主角,所以他的演出也算名揚四海。大都會的其他演員同樣都遜色于那些第一代演員。
真正的問題所在,是樂隊與合唱團。大衛·羅伯特遜(DavidRobertson)指揮中規中矩,每一個音符都是正確的,合唱團更令人刮目相看(合唱團在歌劇中擔綱重要部分,在歌劇的結構之中同樣舉足輕重,令人聯想到巴赫的受難曲)。可是,他們的演繹缺少了音樂中應有的緊迫感。
亞當斯的音樂一點都不浮華。詠嘆調沒有什么抑揚頓挫的旋律,配器方面沒有依賴任何交響效果。或者更確切地說,音樂的脈動好像有著內在的強度,而這強度一直以來都應有威脅性,好像要突圍一樣。當然,音樂到了最后一場,的確沖破了障礙;那正是主角被殺的場景。只可惜,大都會的演出中找不到音樂應有的緊迫感。我猜,參與演出的每一個人都好像被一連串的抗議運動嚇趴了。他們可以從頭到尾演出完整的歌劇(就像早前首演的評論一樣),已經覺得很滿足一樣。
離開歌劇院的時候,我有兩個特別清晰的印象,它們令我更了解這部歌劇與大都會歌劇院。盡管制作并非十全十美,演出卻帶來了新的音樂發現——這些都是從未聽過歌劇音樂、只看過劇本字面的人無法明白的。打從一開幕的合唱段落,巴勒斯坦群眾都站在道德上的高處。歌劇進展的過程中,當我們近距離觀察恐怖分子暴徒般的舉止,這個形象慢慢地瓦解了。以色列人一開始就像一群被寵壞了的小資產階級,但是當他們集體受苦的時候,卻保持了最崇高的尊嚴。
在大都會歌劇院里找不到的,就是尊嚴。盡管我們還得敬佩蓋爾伯——他讓克林格霍芬的女兒們在節目單上刊登聲明(她們還是痛恨這部歌劇)——歌劇院還是要罰扣一分。為什么?歌劇院對于整個事件的處理,真的不夠細心。這部歌劇描述的,是豪華郵輪中發生的殺人事件。節目單里有一則廣告,竟然推銷豪華郵輪假期!
蓋爾伯與工會在夏季展開大戰之際,他曾短暫地離開了自己的“散兵坑”,接受英國《衛報》訪問。訪談中,他聲稱“作為一個藝術模式,歌劇現在面臨危機。”報道出版后,有幾位歌劇樂評家——他們之中最顯赫的是擔任《洛杉磯時報》首席樂評的馬克·思維德(Mark Swed)——撰文批評蓋爾伯。他們大致的論調是:硬要在歌劇這門藝術扣上“面臨危機”的帽子,歸根究底的罪魁禍首就是蓋爾伯。一些心地比較寬宏的評論家提議觀眾應該把眼光放得更遠,不要只看蓋爾伯在大都會搬演那些浪費金錢的狂蕩制作。“這門藝術絕對沒有原地踏步,”思維德寫道,“歌劇發展的進度甚至可以說蓬勃得無法控制,簡直就是飛躍增長。”
雖然我從來都沒有在一個雜貨店、銀行或者蠟像館看過歌劇演出(思維德在文章里興致勃勃地提出這些曾辦過歌劇演出的特殊場地),但是我的確在其他場地看過另類的歌劇演出(也曾在不同刊物中發表過評論文章)。我可以列出的場地包括:歌廳、給大眾開放的戶外公園。說真的,在今天主流歌劇院看演出往往令我心灰意冷,于是我盡量尋找僻路上的另類制作。看罷大都會搬演的《克林格霍芬之死》后,我飛奔到規模樸素的切爾西歌劇團(Chelsea Opera)那里。
切爾西歌劇團本年度演出季的首個制作,有兩部一幕劇:《酒吧地板上的面孔》(The Face on the Barroom Floor)與《諾頓皇帝》(Emperor Norton)。歌劇團選擇美國作曲家亨利·莫利科內(HenryMollicone)這兩部作品,凸顯了這個藝術機構的兩個強項:首先,《諾頓皇帝》屬于紐約首演:第二,劇團挑選兩部特別為年輕演員創作的歌劇,讓多位年輕歌唱家有機會在舞臺上一展身手。我曾經有機會到訪中央城歌劇院,熟知《酒吧地板上的面孔》是特別為這個城鎮而創的作品[委約的靈感源自中央城泰勒屋酒吧(Teller HouseBar)地板上的美女肖像]。這部作品在過去30多年,每一年都有在中央城演出。《諾頓皇帝》真有其人,他行為古怪、生活于19世紀的舊金山。當年,他宣布自己是美國皇帝兼墨西哥的保護者。這部歌劇是舊金山歌劇院梅羅拉歌劇計劃(Merola Opera Program)的委約。這個青年歌劇演員訓練計劃,也是我多年關注的一個項目。
要是說切爾西歌劇團與大都會選擇的方向剛好相反,那真是恰當之極。看起來,導演琳內·海頓·芬德利(Lynne Hayden Findlay)樂此不疲,欣然接受挑戰,要把圣公會教堂圣壇變成泰勒屋酒吧,效果帶有點反諷(令我想起一個老笑話:“無論在哪里碰到四個圣公會教徒,那就必定能找到一瓶酒”)。年輕演員處理角色干凈利落,每個人的演繹都富有戲劇性。盡管演出場地是教堂,音效并不完美,但他們的吐字聽得清清楚楚。作曲家自己也參與演出,在樂隊中彈奏鋼琴(樂手坐在臺側,因為那里沒有樂池)。
切爾西的演出也令我留意到兩個特點。首先,編排兩部歌劇同場演出,讓我們察覺到作曲家自己在風格上的發展,也讓我有機會注意到兩個主題的反差。兩部歌劇都涉及時空交錯。《面孔》描述的,是從前與今天的三角戀,而《皇帝》的主線,是在演員排練一套關于歷史的話劇時,那段歷史故事再現舞臺上。在這兩部歌劇里,從前的歷史要比今天的情節更輝煌,更精彩,更引人入勝。
比時間的交錯更加讓人佩服的,是地點的特色。《面孔》這部歌劇歷時25分鐘左右,《皇帝》45分鐘的進展與節奏掌控得更有把握,但是兩部歌劇的重點都是把觀眾帶進他們熟悉的地點。演出的效果可能比不上當年《托斯卡》的首演那么壯觀——身處羅馬的觀眾在舞臺上看到他們熟悉的名勝地標——但是對舊金山或者中央城的觀眾來說,演出效果卻令人覺得額外親切、特別富有戲劇性。
相比大都會歌劇院推廣的豪華郵輪,切爾西歌劇團的制作一方面更容易掌握,另一方面更少威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