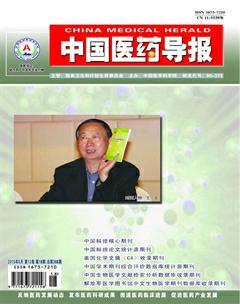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主觀認知減退及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展
劉江紅 董靜 邢怡
[摘要] 阿爾茨海默病是發生在老年人群中的常見癡呆類型,其進程是連續性的,包括臨床前期、輕度認知障礙期和癡呆期。癡呆期的患者其日程生活能力受損,藥物治療效果不理想,因此早期診斷和干預是至關重要的。利用生物標志物在臨床前期即主觀認知減退期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進展,本文對于主觀認知減退及其生物標志物的研究進行綜述。
[關鍵詞] 主觀認知減退;阿爾茨海默病;生物標志物;多模態磁共振
[中圖分類號] R74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5)06(c)-0030-06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是常見的中樞神經系統變性病。最初確診AD需要病理診斷結果。近年來,科學的發展推動著AD相關研究的進展,學者們對于生物標志物(biomarker)有了更多的研究和理解,并引入到AD的診斷之中,這使得AD的診斷不僅僅局限于病理診斷,而是能夠在生前結合生物標志物來診斷。更為重要的是,使得AD在癥狀前期就可以被診斷,甚至是在主觀認知減退(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SCD)期即可被識別,因而能夠推動早期干預和治療。
早在1982年,Reisberg等[1]將認知狀態共分為7個臨床階段,包括了從正常至極重度癡呆的整個過程。其中,第二階段是指患者有記憶障礙的主訴而不存在相應的客觀臨床表現,這個階段即是所指的SCD階段。在大量關于AD、 MCI和正常人的病理、影像、腦脊液的橫斷面和縱向研究的基礎上,2010年Jack等[2]提出AD的生物標志物和認知障礙隨時間動態變化的發展模式,認為當AD患者尚無認知障礙的臨床表現時,即可出現具有AD特征的生物標志物異常,且這些AD早期的生物標志物是隨著AD病變的進展依次出現的。目前,與AD早期診斷有關的生物標志物包括影像學和腦脊液指標兩方面[3-4]。本文就從這兩方面介紹有關SCD與AD關系的研究,以探討生物標志物對SCD發展成為AD的預測價值。
1 影像學標志物
1.1 結構磁共振(structural MRI,sMRI)
病理研究提示,由于多種機制的作用,AD患者可出現神經元及突起的數量下降、突觸減少,從而導致皮層體積縮小,甚至萎縮,且皮層萎縮具有特定的空間分布特征和發展順序[5]。利用sMRI檢查技術對AD患者進行動態觀察,有研究發現:AD患者某些部位皮層萎縮的程度和速度與認知障礙的嚴重程度和發展速度存在相關性[6]。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SCD患者的皮層萎縮情況,以尋找AD早期診斷的線索。目前,sMRI主要用于測量患者皮層的體積和厚度。研究者綜合采用多種算法和影像分析工具,在T1像上提取出皮層所占圖像區域并測量其厚度和體積;還可重建出皮層的三維結構圖,更加直觀地顯示皮層萎縮的分布范圍和程度;此外,通過與其他影像檢查手段(如功能MRI、PET等)進行整合,可進一步探討皮層萎縮與腦代謝及功能之間的關系。利用基于體素的空間統計學方法(VBSS),可比較各組患者間任意像素點代表的皮層體積和厚度的差異,從而可比較各組患者間皮層任意部位的萎縮情況[7]。自2004年以來,研究者開始利用sMRI研究SCD患者皮層不同部位的體積和厚度[8]。研究表明,與正常老年人相比,SCD患者的海馬、內嗅皮層、顳葉內側、扣帶回后部、楔前葉皮層可出現體積下降或厚度減小;與輕度認知功能損害(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或AD患者相比,SCD患者皮層萎縮的空間分布存在相似性,只是萎縮程度較輕[7,9-12]。SCD患者的皮層萎縮程度與其認知障礙主訴的嚴重程度存在相關性[8]。這些研究提示,雖然SCD患者不存在客觀認知障礙,但可能已經出現皮層萎縮的病理變化,且與AD患者的皮層萎縮表現相似。有研究對SCD患者進行了3.75~4年的隨訪觀察[7,13],結果表明伴有海馬體積下降或與AD相似的皮層萎縮模式的SCD患者更易出現客觀認知損害。這就提示某些結構影像學特征可能有助于預測SCD患者向AD的轉化。
1.2 彌散張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DTI)
除了皮層萎縮之外,白質纖維束的改變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關注。研究發現,AD和MCI患者多個部位的白質體積下降且纖維束的完整性受到破壞,特別是海馬旁纖維束、扣帶、胼胝體以及下縱束、鉤束、穿通通路(perforant pathway)等[14]。這可能是由于神經元變性壞死繼發軸索華勒變性所致,也可能是AD病變直接損害軸索和髓鞘引起的病理表現,其機制目前尚不明確[14-15]。目前DTI的主要測量指標包括分數各向異性(fractional anisotropy,FA)、平均擴散率(mean diffusivity,MD)、軸向擴散系數(axial diffusivity,AD或DA)、徑向擴散系數(radial diffusivity,RD或DR),其中軸向擴散系數與軸索即纖維束的走向有關,徑向擴散系數與髓鞘有關,通過測量這些指標可了解纖維束的顯微結構,即軸索和髓鞘的受損情況,而不僅僅是白質纖維束的體積和信號強度。采用圖像處理軟件,DTI可同時顯示所有白質纖維束的走行和分布。近年來,采用基于纖維束的空間統計學方法(TBSS),研究者可進一步分析不同患者在各纖維束彌散指標上的差異[16]。研究表明,相對于正常人,SCD患者的海馬旁纖維束、扣帶后部纖維可出現FA下降、DR升高,提示SCD患者這些部位已出現纖維束損害[16-17]。2013年Selnes等[18]對SCD患者進行了2~3年的隨訪觀察,發現進展為客觀認知損害的SCD患者更易出現各部位(包括內嗅皮層、海馬旁、胼胝體壓部、扣帶后部、楔前葉、緣上回附近)纖維束完整性的破壞,MD、RD升高及FA下降皆可預測SCD患者是否將出現客觀認知損害。然而,這項研究并沒有將SCD和MCI患者完全區分開,因此還需針對SCD患者的研究進一步探討纖維束完整性對SCD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此外,另有研究認為某些纖維束完整性的破壞情況不能完全與其聯絡的皮層萎縮情況相對應[19-20],提示白質損害與皮層萎縮可能是AD病理表現的兩個方面,因此,針對SCD患者的DTI研究與sMRI研究具有互補作用。
1.3 靜息態功能核磁(resting state functional MRI,rs-fMRI或R-fMRI)
靜息態功能核磁是研究清醒安靜閉目狀態(即無外界刺激狀態)下腦功能活動的磁共振技術。大量研究表明,人腦在靜息狀態下部分腦區的功能活動并不減少,反而較執行任務時有所增加,且這部分腦區存在同步的低頻振蕩,因此統稱為腦默認模式網絡(default mode network,DMN)[21]。由于DMN的存在具有時間上的穩定性,在休息、執行任務、睡眠、甚至麻醉狀態下皆可觀察到,因此它很可能反映了神經元的自發活動[22];DMN包括扣帶回后部、楔前葉、前額葉腹內側、頂葉外側、顳葉內側,與AD的特征病理表現部位存在重疊;此外,靜息態功能核磁操作簡便、無創、患者易于配合,因此,靜息態核磁技術適用于研究AD患者的腦功能活動。近年來,針對AD和MCI患者的研究發現,其DMN功能聯系的完整性受損,特別是胼胝體后部、楔前葉和海馬之間的功能聯系減少,甚至在腦萎縮之前已經出現[23-24]。此外,伴有ApoEε4基因突變或AD家族史的正常人也可出現DMN功能聯系受損[25-26]。這些研究提示AD確實可損害腦的功能聯系,尤其是在結構影像學表現不明顯時即可出現。然而,目前針對SCD患者的DMN研究較少,2013年Wang等[27]對23例SCD患者進行觀察,結果發現與正常老年人相比,SCD患者右側海馬區的功能聯系受損,但受損程度輕于MCI患者,提示SCD患者的部分神經元可能已出現功能損害,然而這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加以驗證。
1.4 碳11標記的匹茲堡化合物B正電子放射斷層攝影術(11C-PIB PET或PIB PET)
病理檢查提示老年斑和神經元纖維纏結是AD的兩大特征表現,而β淀粉樣蛋白(amyloid beta protein,Aβ)則是老年斑的主要成分;家族性AD的常見基因突變APP、PSEN1、PSEN2皆與Aβ的代謝通路密切相關,說明Aβ沉積是AD發病機制中的重要環節[28]。不僅如此,有研究對認知功能正常的老年人和SCD患者進行尸檢,結果表明即使是認知功能正常的老年人或SCD患者也存在腦內Aβ沉積[29-30],提示當AD患者認知功能尚未受損時,可能已出現腦內Aβ代謝異常。2004年,Klunk等[31]首次將PIB-PET用于研究AD患者,使活體顯示患者腦內Aβ沉積情況成為可能。PIB-PET不僅直觀,而且能進行定量統計分析,比較不同患者間不同腦區Aβ的沉積情況。采用這一技術,研究者針對AD和MCI患者開展了大量研究。許多研究[32-35]認為,AD患者認知障礙進展的快慢與腦內Aβ沉積的速度不相一致,提示AD患者腦內的Aβ沉積可能已進入平臺期,而MCI患者的認知功能受損程度與Aβ沉積量存在相關性[36],提示研究AD臨床前期Aβ的沉積情況應更有意義。2010年,Chetelat等[37]的研究發現SCD患者的Aβ沉積與某些部位的皮層萎縮存在相關性,包括眶額皮質內側部、扣帶回、楔前葉,而對無認知障礙主訴的正常人并不存在這種相關性。此后有研究進一步提示SCD患者的認知障礙主訴嚴重程度與PIB造影劑的滯留情況存在相關性[38]。2013年Dore等[7]對認知功能正常的老年人進行隨訪觀察,結果表明伴有Aβ沉積的老年人海馬和顳葉皮層萎縮的速度快于不伴Aβ沉積者。然而,這項研究并非完全針對SCD患者,因此,SCD患者的腦內Aβ沉積情況與認知功能障礙進展之間的關系還有待研究。
2 腦脊液標志物
1998年,AD分子和生化標志物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Molecular and Biochemical Markers of Alzh-eimer's Disease)提出了三個輔助AD診斷的腦脊液生化指標[39]:Aβ42、總tau蛋白(T-tau)、磷酸化tau蛋白(P-tau)。研究表明,病理確診的AD患者生前腦脊液中Aβ42含量下降,T-tau、P-tau含量升高,且這些指標的變化程度與腦內淀粉樣斑塊和神經元纏結的數量存在相關性[40-41],提示腦脊液中的這三項指標能夠間接反映AD患者腦部病變程度。腦脊液Aβ42水平下降可能是由于Aβ42易聚集成斑塊,使溶于腦脊液的Aβ42含量相應減少,而T-tau、P-tau水平升高可能與軸索、神經元受損導致tau蛋白進入細胞外液有關,其機制目前尚不明確[42]。有研究分析Aβ42、tau蛋白診斷AD的敏感性和特異性[42-43],結果表明這三項指標能較好地區分AD患者和正常人,而P-tau最有助于鑒別AD和其他類型的癡呆。研究還發現進展為AD的MCI患者和AD患者腦脊液中的Aβ42和T-tau水平相似[43],這不僅說明AD臨床早期即可出現腦脊液生化指標的異常,而且提示AD患者早期已有明顯的AD病理特征的腦脊液表現。因此,研究AD臨床前期的腦脊液生化指標異常具有重要意義。2008年,Mosconi等[44]對攜帶有ApoE ε4基因的SCD患者和非SCD正常人進行比較,發現腦脊液P-tau/Aβ42比值與腦代謝指標結合有助于區分二者。此后,DESCRIPA(development of screening guidelines and clinical criteria for predementia AD,DESCRIPA)研究[45]也發現SCD患者比非SCD正常人更易出現腦脊液結合型指標異常[Aβ42/(240+18×T-tau)<1為結合型指標異常](52%比31%),然而,研究對SCD患者進行平均2.8年的隨訪后并未發現這一指標能夠預測SCD向AD發展。于是研究者對更多的SCD患者進行了平均4年的隨訪,結果表明腦脊液Aβ42水平下降能夠增加SCD患者進展出現客觀認知損害的風險,且Aβ42優于其他結合型的指標[如Aβ42/(240+18×T-tau)][46]。這些研究表明,SCD患者腦脊液已有AD相關的表現,且Aβ42可能比tau蛋白或結合型指標更能預測SCD患者向AD進展,提示SCD患者Aβ代謝異常可能早于神經元損傷出現,但仍需更多研究加以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