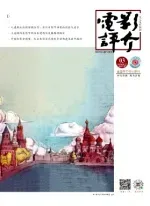對后現代主義語境下抗日劇影像抒寫的反思
蘇米爾
一、 后現代主義語境下抗日劇思想性與藝術性的消解
中國抗日戰爭題材電視劇(簡稱“抗日劇”)作為中國革命抗戰史的影像抒寫,由于所展現的歷史相去不遠,史料詳盡,素材豐富,所以創作空間較為廣闊。誠然,作為歷史題材劇的一類,抗日劇的創作亦是“立足今天,為了明天,抒寫昨天”。然而,紛至沓來的抗日劇在思想性與藝術性方面良莠不齊,尤其是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許多作品在創作上已然偏離了正確航向。
后現代主義,始于20世紀60年的歐洲,在藝術創作方面,主要表現為否認藝術經典,強調自我宣泄,崇尚標新立異。正如解構主義文學理論家保羅·德·曼所言:“美學自從它剛好在康德以前以及與康德同時得到發展以來,事實上是意義和理解過程的一種現象論,它(如其名稱所示)假設了一種很可能是懸而未決的文學藝術的現象學,這也許是十分天真幼稚的。”[1]又如,美國后現代學者哈桑揭示了后現代主義的兩個基本特征:不確定性和內在性。其中,不確定性包含了反叛、曲解、變形等特質;內在性則是對精神、價值、真理、終極關懷等傳統美學所關心問題的內縮。[2]顯而易見,保羅·德·曼和哈桑的論述反映出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審美理念對傳統美學持否認態度。這在創作上必然表現為對經典藝術的摒棄與主觀意志的強化,走向極端則是個人經驗主義下的主觀臆斷和自我宣泄。這種主觀性通過反叛、曲解、變形的“不確定性”和終極關懷等命題“內在性”的收縮得到強化。在思想性方面,精神、真理、價值等遭到摒棄,思想內涵遭到嚴重瓦解;在藝術性方面,以新奇荒誕取代藝術典型,美學效果遭受沖擊。不必諱言,后現代主義語境下的抗日劇創作也遭受了重大影響。
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對抗日劇的影響表現為個人經驗主義下的任意解構歷史,剝奪抗日劇的思想性。在這一語境下,創作者不是力圖在做足歷史功課的基礎上,追求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有機統一,而是把抗日題材看做是抽象的時空,極盡主觀臆造和戲說戰爭之能事。例如,電視劇《抗日奇俠》中,俠客均為飛檐走壁、以一當十的武林高手,赤手空拳亦可對抗日軍的機槍炮火;《永不磨滅的番號》中,八路軍獨立團三天消滅了敵軍半個師,已然超過歷史上歷經數月的百團大戰之戰績;《新地道戰》中,革命戰士的戀愛情節喧賓奪主,弱化了斗爭歲月的艱苦與勝利的來之不易。敘事上的任意戲說,解構歷史,猶如為莊重嚴肅的歷史蒙上了面紗,按照個人意志在面紗上任意涂改歷史。抗日劇創作中的個人經驗主義本質上是后現代主義摒棄歷史經典,強化自我宣泄的具體化表現,這必然無法實現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完美結合,更難以談及提煉歷史智慧,汲取歷史教訓,體察歷史情懷,從而喪失了作品的思想性。
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對抗日劇的影響體現為人物與環境的去典型化處理,消解崇高美感。抗日劇之所以能夠在歷史劇中獨樹一幟,從美學角度而言,是因為該類作品彰顯了崇高美感。根據康德的理論,客體在數量上的無限多、體積上的無限大、力量上的無限強超出主體想象力能夠把握的限度,使主體產生驚懼,從而否定主體,并喚起主體的理性觀念,最后理性觀念戰勝客體對象,進而肯定主體尊嚴,產生崇高美感。具體到抗日劇而言,其規定情境下的敘事本應給人以崇高的美感:戰爭對家園的摧毀,對生命的摧殘,對命運的裹挾,對人性的考驗,形成巨大沖擊力,構成力的崇高。特定情境中的典型人物從對戰火的驚懼到對戰爭的反思,再到抗爭,歷盡生離死別,經歷種種考驗,九死一生,使得觀眾在波瀾起伏的影像抒寫中如臨其境,感到震撼,得到凈化,受到激勵,從而產生崇高美感。然而,目前的抗日劇則普遍弱化了戰爭踐踏家園的殘酷性,弱化了敵強我弱的抗戰艱苦,弱化了特殊環境對信念的考驗,弱化了戰爭使“人”異化為“非人”的展現,弱化了戰火歲月人們復雜心境的表達,取而代之的是“手撕鬼子”“抗戰女神”“戰斗神器”等熒屏現象,導致典型歷史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遭受瓦解。標新立異固然能夠滿足眼球經濟的獵奇之需,但是去典型化的影像表達勢必難以產生震撼與凈化心靈的崇高美感,使作品喪失了本該具備的審美特征。
二、 后現代主義“困境”阻滯抗日劇非替代性文化價值的實現
正是由于許多作品逾越了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底線,使得后現代主義的語境演變為抗日劇創作的“困境”,使作品庶幾喪失了文化價值。誠然,抗日劇具有文化價值和商品價值的雙重屬性。其中,商品價值主要體現為作品的審美娛樂特性,重在滿足眼球經濟之需;文化價值主要體現為作品的審美認識、審美教育、審美組織特性,重在使觀眾培養審美情趣,引起歷史反思,提升精神境界。目前,抗日劇創作重商品價值,輕文化價值。電視娛樂節目形形色色,使得抗日劇的商品價值具有很強的替代性,一旦不能迎合需求,便難有立錐之地。因此,商品價值不是其價值的關鍵所在。
抗日劇作為特殊的一類歷史劇,其核心價值在于具有非替代性的文化價值。具體而言,回顧抗日戰爭這段具有切膚之痛、相去不遠的歷史,旨在令觀眾在獲得審美體驗的同時,正視歷史,思索歷史,感悟歷史。這一點與歷史教科書的作用類似,然而,抗日劇與教科書畢竟不同。電視劇作品重在通過真實可感的人物形象、生動逼真的規定情境、跌宕起伏的戲劇沖突來創造一個意象世界,還原一個存在的真。這個存在的真,是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是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是其文化價值的所在。這個存在的真,有戰火紛飛的殘酷,有妻離子散的慘痛,有艱難困苦的挑戰,有赤裸人性的暴露,有英勇犧牲的悲愴,有理想信念的堅守,這個意象世界使觀眾如臨其境,受到震撼,凈化心靈,從而在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共同熔鑄的藝術臻境中提升精神境界。相比之下,教科書通過列舉史實,公布數據,總結陳詞使讀者進行理性認知,展現的是一種邏輯的真,這種邏輯的真對于歷史學習固然不可或缺,但與存在的真相比,邏輯的真難以喚起情感體驗與審美體驗,無法取代存在的真。因此,即使是歷史教科書,也不可取代抗日劇特有的文化價值。
抗日劇文化價值的非替代性顯示了其存在的核心價值。然而,在后現代主義語境下,抗日劇的思想性與藝術性受到沖擊,文化價值難以彰顯。正如前文所述,個人經驗主義對自我宣泄的強化,難以透過鏡像客觀地揭示歷史本質,彰顯歷史精神,敲響歷史警鐘,引起歷史哲思,這在很大程度上使作品喪失了思想內涵;在創作中使用去典型化、標新立異的手法對環境、人物、情節進行編碼,由于脫離了藝術典型性和歷史真實性,使得抗日故事與英雄人物特有的崇高美感消解殆盡。因此,抗日劇創作只有走出后現代主義之“困境”,探求正確合理的創作航標,匡正作品的思想性,提升作品的藝術性,才能發揮出其非替代性文化價值。
三、抗日劇走出“困境”并發揮文化價值的路徑抉擇
正如宗白華所言:“象如日,創化萬物,明朗萬物!”[3]創造意象世界是藝術創作的首要任務,當然也是抗日劇創作的第一要義。意象世界所展現的是“存在的真”,是作品文化價值非替代性得以實現的根本,也是導引創作者走出后現代主義困境的航標。
一方面,要創造意象世界,須堅持創作的自覺性。抗日劇要審美地再現中國抗戰史,就必須自覺做足歷史功課。這是由于,歷史真實是藝術真實的基礎,一旦脫離了歷史事實,歪曲了歷史本質,摒棄了歷史精神,審美再現就會附庸于個人經驗主義,藝術創作就會失去思想內涵。在眾多革命戰爭題材作品中,經典作品《亮劍》第一部(2005年)以虛構人物李云龍一生的戎馬生涯從一個側面展現了中共革命抗爭史,并以“亮劍精神”為思想內涵統領了全劇,是一部典范之作。劇中的日寇坂田聯隊曾經“一個聯隊消滅中央軍兩個師”,李云龍面對強敵卻毫不退縮,經歷鏖戰最終取得勝利。這一過程體現了李云龍部隊面對強敵敢于“亮劍”的氣魄。但“亮劍精神”絕非匹夫之勇,李云龍在戰術上堅持“賠本的買賣咱不干”,表現出其戰斗中的審時度勢、精明強干。李云龍部隊所彰顯的“亮劍精神”正是中共革命軍隊不畏強敵、敢于犧牲的精神所在,也是“游擊戰”中紅軍戰術之縮影。當李云龍發現營長張大彪尚未突圍時,立刻冒險殺回重圍施救,張大彪感動涕淚,該情節的設計同樣詮釋了“亮劍精神”的豐富內涵,也印證了中共革命軍人之間的肝膽相照、生死與共正是抗戰勝利的關鍵所在。《鐵血紅安》(2015年)作為思想性深刻的另一部力作,其創作經驗同樣值得借鑒。該劇講述了在湖北省紅安縣的劉銅鑼、方杠子、戴慧平三個“把兄弟”的紅色革命成長歷程:三人從最初的“勇救戲班”,鋤強扶弱;到后來分道揚鑣,加入不同政黨,或自行安營扎寨;時至抗日戰爭爆發后的同仇敵愾,解放戰爭時期對不同信仰的追求;直至改革開放后,三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思想性方面,《鐵血紅安》表達出革命勝利不僅需要英雄將領的運籌帷幄與決勝千里,更需要“劉銅鑼”式平民英雄的理想堅守與浴血奮戰,全劇將人民創造歷史的唯物史觀融入到生動可感的人物形象中。雖然主人公經歷實屬虛構,但是由于創作者自覺地夯實史實之基礎,提煉出歷史之精髓,所以在唯物史觀的引領下,能夠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內涵,在創作時也沒有落入戲說戰爭、主觀臆造的個人經驗主義之窠臼。
另一方面,要創造意象世界,亦須堅持審美的獨立性。審美的獨立性強調的是,作品既不是歷史教科書的“政治圖解”,也不是“眼球經濟”之附庸,因而創作者應當以一個獨立的、客觀的、歷史的人的身份去觀照歷史,用典型化手法重塑歷史景觀。唯有如此,才能擺脫政治宣傳和“教科書”式的刻板形象塑造,才能避免只求養眼不求“養心”的泛娛樂化敘事,從而使情境的設置、人物的塑造、情節的設計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具有藝術典型性,富有藝術感染力,能夠使觀眾受到感動和振奮,得到凈化和提升。在藝術性方面,《亮劍》塑造了中共革命杰出將領的典型。李云龍形象代表了中共的廣大將領。這些將領并未受過正規教育,甚至滿口粗話,但是愛黨愛國,敢于犧牲自我,同時精明強干,富有戰斗經驗。李云龍帶領部隊擊潰日寇坂田聯隊的情節設計,正是中共杰出將領率領革命軍隊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藝術凝練。《鐵血紅安》則展現了“劉銅鑼”式的普通人在艱苦歲月中如何找到理想,如何經受考驗,如何堅定信仰,如何鑄就鐵骨,戲劇沖突可謂一波三折,故事情節充滿跌宕起伏。同時,該劇以平民化視角展現了包括抗日戰爭在內的重大歷史史實,洞察了在歷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內心世界,抒寫了以劉銅鑼為典型人物的中國革命普通戰士的成長史。波瀾起伏的劇情設置與典型化的人物塑造,使得觀眾在波瀾壯闊的影像抒寫中如臨其境,感同身受,激發了基于抗戰精神的崇高美感。
綜上所述,唯有堅持創作的自覺性和審美的獨立性,將兩者高度統一于抗日劇的創作中,才能在尊重歷史、正視歷史的基礎上創造出一個“創化萬物,明朗萬物”的意象世界,才能在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融合中呈現出一個“存在的真”,實現深刻思想內涵與精湛藝術再現的完美熔鑄,從而走出長久以來后現代主義籠罩下的創作困境,進而彰顯出抗日劇非替代性的文化價值,真正做到“立足今天,為了明天,抒寫昨天”,以恢弘磅礴的影像奇觀為紀念反法西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獻一份禮。
[1]保羅?德?曼.對理論的抵制[M]//最新西方文論選.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215.
[2]伊?哈桑.后現代主義概念初探[M]//后現代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126.
[3]宗白華.形而上(中西哲學之比較)[M]//宗白華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