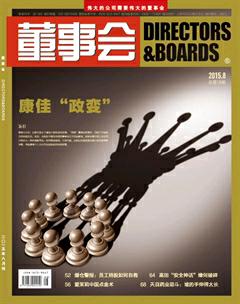高田“安全神話”緣何破碎
張玉來

“她是公司內(nèi)誰也不敢違抗的女王,在第二代掌門人去世之后,就形成了這種院政狀態(tài)”——迅速國際化的高田也面臨著成長的煩惱,那就是如何讓家族式管理適應(yīng)這種新趨勢,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向職業(yè)經(jīng)理人之路并不容易
“交通事故犧牲者為零。”這是高田公司一直倡導(dǎo)的經(jīng)營理念。正是常年積累所形成的高度信用,2005年美國聯(lián)邦道路交通安全局(NHTSA)授予高田社長高田重一郎特別貢獻(xiàn)獎(jiǎng)。兩年之后,美國汽車安全委員會(huì)(AORC)也授予他“開拓者獎(jiǎng)”,他是日本人、也是美國大陸之外的第一位該獎(jiǎng)項(xiàng)獲獎(jiǎng)?wù)摺?/p>
然而,榮光尚未褪色之際,使用高田產(chǎn)品的最大汽車廠商本田技研便因安全氣囊事故,于2008年在北美地區(qū)召回51萬輛汽車。緊接著,矛頭也直指高田。2009年一位美國女孩因被氣囊彈出的金屬片劃破頸動(dòng)脈而死亡,高田氣囊成為美國媒體眼中的“殺人武器”。
問題越加嚴(yán)重。作為全球第二大安全氣囊裝置制造商的高田,其客戶不僅僅限于日系車企,包括寶馬、奔馳在內(nèi)的歐美高端品牌也都是高田的使用者。這場暴風(fēng)驟雨之下,已然從白天鵝驟變成丑小鴨的高田真能挺過去嗎?
華麗轉(zhuǎn)身:從紡織到汽車
高田創(chuàng)立于1933年,它是以創(chuàng)業(yè)者高田武三的姓氏所命名的家族企業(yè),以棉紡織品加工生產(chǎn)為主業(yè)。二戰(zhàn)期間,它以降落傘材料生產(chǎn)為主。朝鮮戰(zhàn)爭結(jié)束后,高田武三訪美,目的是了解一家研究所發(fā)明的新材料,該研究所就是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前身。高田同時(shí)發(fā)現(xiàn),它正在研發(fā)一種叫做安全帶的新產(chǎn)品,其緣由是因?yàn)槊绹l(fā)現(xiàn)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飛行員,甚至相當(dāng)于朝鮮戰(zhàn)爭中死傷飛行員的數(shù)量。高田將樣品帶回了日本,還與日立金屬公司合作,花費(fèi)10年時(shí)間開發(fā)出實(shí)用化的車用安全帶。
1961年,高田在東京赤坂王子飯店舉辦“高田安全帶”新產(chǎn)品展示會(huì),這是日本第一個(gè)車用安全帶裝置。然而,這項(xiàng)創(chuàng)新產(chǎn)品卻遭市場冷遇:一是因?yàn)閮r(jià)格高昂,其售價(jià)2400日元,而大學(xué)畢業(yè)剛工作者的月薪也不過16000日元;二是汽車廠商普遍不為汽車加裝安全帶。
如何開啟市場成為高田從紡織轉(zhuǎn)型到汽車業(yè)的頭號任務(wù)。剛從美國留學(xué)歸來的高田重一郎擔(dān)綱此項(xiàng)重任,他做了兩件大事:一是游說政府,以撞擊實(shí)驗(yàn)證明車用安全帶的重要性;二是鎖定重點(diǎn)企業(yè),他瞄準(zhǔn)同樣是市場“新進(jìn)入者”的本田公司。1962年高田實(shí)施了日本歷史上第一次汽車碰撞試驗(yàn),各大報(bào)刊和電視臺紛紛報(bào)道了“安全帶的重大作用”。本田宗一郎欣然接受了高田的建議,還邀請高田參與本田車的設(shè)計(jì)工作。于是,本田S500加裝了兩點(diǎn)式安全帶裝置,并成為日本最初的標(biāo)準(zhǔn)配置。1969年,日本政府推出新規(guī),要求所有新車必須加裝安全帶。
高田繼續(xù)引領(lǐng)行業(yè)創(chuàng)新。1970年東京車展上展出了高田電子安全帶(TESS),它是采用電磁鎖方式避免了安全帶的迅速鎖死。該產(chǎn)品得到美國聯(lián)邦道路交通安全局的大加贊許,1972年該機(jī)構(gòu)負(fù)責(zé)人專程到高田公司訪問參觀。高田當(dāng)然不會(huì)放過這個(gè)進(jìn)入美國市場的良機(jī)。1973年NHTSA主辦了邀請世界汽車廠商和零部件供應(yīng)商參加的碰撞試驗(yàn),高田帶來了能高效吸收沖擊能量的新產(chǎn)品,展示了讓人體在48公里時(shí)速撞擊下仍無損傷的效果。這在美國主流報(bào)刊上被以“最高紀(jì)錄”廣為傳播,高田的優(yōu)秀品質(zhì)得到了世界矚目。
樹立品牌:做技術(shù)先行者
雖然搶占了車用安全帶的先機(jī),但仍有一個(gè)問題令高田難以釋懷,那就是駕乘者安全帶使用率極低。如1968年美國安全帶使用率僅為5%。于是,高田創(chuàng)造性地通過開發(fā)兒童座椅來推進(jìn)安全帶的使用,其理論邏輯是:若能形成使用汽車兒童座椅習(xí)慣的話,那么安全意識得到增強(qiáng)的成人也將形成使用安全帶習(xí)慣。1977年高田推出一鍵操作的車用兒童座椅,這是日本第一個(gè)正式車載兒童座椅。1985年高田又研發(fā)出樹脂材料的兒童座椅,至今這仍是主流,它還因此榮獲全美嬰兒家具零售協(xié)會(huì)(NINFRA)大獎(jiǎng)。
對于同樣是保護(hù)駕乘安全的安全氣囊產(chǎn)品,高田起初卻是堅(jiān)決反對的。它曾認(rèn)為安全帶與安全氣囊是“二選一”關(guān)系。后來,高田與寶馬汽車一起受邀參加了1983年在美國舉辦的安全氣囊現(xiàn)場實(shí)測。當(dāng)時(shí),同時(shí)加裝了安全帶與安全氣囊的奔馳汽車,著實(shí)讓高田耳目一新。不過,在接到本田一起開發(fā)安全氣囊的邀請之際,高田還是猶豫不決,因?yàn)樗斜绕胀ú考?000倍的信任感,“如果安全氣囊出了問題,高田就會(huì)破產(chǎn)。我們不想走上這個(gè)危險(xiǎn)之橋”。但很快高田改變態(tài)度,決心全力發(fā)展安全氣囊業(yè)務(wù)。它成為本田駕駛模塊開發(fā)單元的重要伙伴,深入到整車開發(fā)業(yè)務(wù)。1987年的本田高端品牌里程(LEGEND)就成為日本第一款裝配駕駛座安全氣囊的轎車。
此后,高田氣囊產(chǎn)品不斷推陳出新:2005年開始量產(chǎn)雙氣囊產(chǎn)品、2006年開發(fā)出摩托車用安全氣囊、2010年上市裝有氣囊的安全帶、2012年推出汽車前部整體氣囊、2013年銷售所謂FVT氣囊產(chǎn)品,這些都是世界首創(chuàng)技術(shù)。
如今,高田已經(jīng)成長為全球第二大安全氣囊生產(chǎn)廠商,僅次于瑞典奧托立夫。而且,在技術(shù)進(jìn)步方面,它更強(qiáng)調(diào)標(biāo)新立異、開拓新產(chǎn)品渠道。在安全氣囊膨脹裝置方面,20世紀(jì)90年代高田就開始采用硝酸銨而非其他公司普遍應(yīng)用的硝酸胍,因?yàn)檫@種材料可以使安全氣囊變得更輕、更小,在技術(shù)上有很多優(yōu)勢。另外,從有效專利申請件數(shù)也可以看到高田的優(yōu)勢。在日本市場上,它僅次于豐田合成,擁有487項(xiàng)有關(guān)安全氣囊的專利技術(shù)。
戰(zhàn)略隱憂:國際化與院政模式
1983年,在公司迎來創(chuàng)業(yè)50周年之際,高田開始走國際化道路。當(dāng)時(shí)正值日本汽車廠商大舉進(jìn)軍海外,作為零部件供應(yīng)商的高田,一邊為這些海外日本汽車供應(yīng)相關(guān)部件,一邊大膽開展“獨(dú)立外交”,積極拓展自己的一片天地。在美國,高田精心選擇攜手與通用汽車(GM)關(guān)系緊密的費(fèi)希博德(Fisher Body),1983年在密歇根州創(chuàng)立高田·費(fèi)希合資公司,制造、銷售車用安全帶產(chǎn)品。然而,由于日美紡織品貿(mào)易戰(zhàn)正酣,美國不允許日本向其出口產(chǎn)業(yè)用紡織產(chǎn)品。高田試圖收購伯林頓工業(yè)公司紡織品業(yè)務(wù)來解決這個(gè)難題,但涉嫌違反美國反壟斷法而被迫放棄。這時(shí),通用汽車則伸出援手,協(xié)助高田收購了兩家工廠讓其在美國生產(chǎn)獨(dú)立產(chǎn)品。
同樣是借力通用汽車,高田開始進(jìn)入歐洲市場。通過與通用授權(quán)銷售汽車的企業(yè)成立合資公司,高田產(chǎn)品開始在歐洲市場生產(chǎn)銷售。亞洲則是高田最早進(jìn)入的海外市場,1980年它在韓國設(shè)立Duck Boo International合資公司,制造和銷售安全帶產(chǎn)品。1992年它在新加坡設(shè)立高田亞洲持股公司,以此來加速推進(jìn)亞洲市場。之后,高田相繼在泰國、菲律賓、韓國、中國等地創(chuàng)辦生產(chǎn)基地。
截至2014年,高田集團(tuán)的銷售額已經(jīng)突破6000億日元,在全世界28個(gè)國家擁有58座工廠。而且,高田海外銷售占比已高達(dá)88%,其中,美洲地區(qū)是其最大市場,占總銷售比42%;其次是歐洲地區(qū),占比與達(dá)到26%。二者接近高田銷售額的70%。亞洲市場增長最快,已從2012年度923億日元迅速增長至2014年的1647億日元,兩年增長了78%。
然而,迅速國際化的高田也面臨著成長的煩惱,那就是如何讓家族式管理適應(yīng)這種新趨勢。曾幾何時(shí)這曾是高田迅速崛起的關(guān)鍵,特別是第二代社長高田重一郎,他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和卓越的領(lǐng)導(dǎo)力,“在高田員工們的眼里,就像天皇的存在一樣”。他1958年畢業(yè)于日本著名高校慶應(yīng)義塾大學(xué),1962年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xué)工商管理碩士學(xué)位,要知道,當(dāng)時(shí)這種學(xué)歷在日本可是寥寥無幾的。他回到高田工場并施展自身才華,積極致力于生產(chǎn)現(xiàn)代化和經(jīng)營國際化,并在1974年出任公司社長。2004年為了能夠符合現(xiàn)代上市企業(yè)要求,高田對公司實(shí)施拆分,讓生產(chǎn)和銷售汽車部件的子公司獨(dú)立上市,母公司則改稱為TKJ,2006年高田在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
高田曾試圖轉(zhuǎn)向職業(yè)經(jīng)理人道路。2013年它迎來博世日本公司社長斯蒂芬·斯托克擔(dān)任社長,這是高田82年經(jīng)營史上第一位外人社長,但2014年“氣囊門”事件卻讓這位新社長“出師未捷”便被迫辭職。于是,社長再次由高田家族出任,這次是創(chuàng)業(yè)者之孫高田重久。但這位資歷尚淺的年輕社長顯得束手束腳,這就使其背后一位關(guān)鍵神秘人物便浮出水面,其母高田曉子。她本姓山田,是讓日本凸版印刷公司實(shí)現(xiàn)復(fù)興的山田三郎的女兒。同樣畢業(yè)于名門慶應(yīng)大學(xué)的高田曉子進(jìn)入公司很快成為中堅(jiān)。她不僅主持嬰兒座椅開發(fā),極大拓展了高田事業(yè)范圍,留美經(jīng)驗(yàn)也讓其在開發(fā)美國市場顯得游刃有余。1991年她便成為公司董事,2007年成為特別顧問。在丈夫去世之后,她還接任了高田財(cái)團(tuán)的理事長。據(jù)高田相關(guān)人士透露,“她是公司內(nèi)誰也不敢違抗的女王,在第二代掌門人去世之后,就形成了這種院政狀態(tài)”。
神話破碎:高田出路何在?
“殺人犯就是安全氣囊。”高田成為美國媒體的眾矢之的。這場風(fēng)暴源于2008年,當(dāng)時(shí)使用高田氣囊的本田汽車發(fā)生了多起氣囊爆裂的問題,本田為此被迫實(shí)施召回。但作為零部件供應(yīng)商的高田則認(rèn)為汽車召回是“汽車生產(chǎn)商自己的舉動(dòng)”。2009年美國發(fā)生首次因氣囊爆裂而致人死亡的事件,仍然采取不配合態(tài)度的高田陷入輿論批評的風(fēng)口浪尖。2014年高田社長斯托克的辭職未能平息這場風(fēng)暴,相反,馬來西亞新一件氣囊致人死亡事故則將這場風(fēng)暴蔓延至全球。2015年年初,美國以高田不配合調(diào)查工作,宣布處以每日1.4萬美元罰款的決定。
高壓之下,高田不得不轉(zhuǎn)變態(tài)度。2015年5月,高田與NHTSA簽署了一項(xiàng)共同聲明,它承認(rèn)關(guān)于產(chǎn)品缺陷的4項(xiàng)指控,并同意召回其生產(chǎn)、銷往美國的約3380萬個(gè)存在安全隱患的汽車安全氣囊。這與半年前美國參議院舉行聽證會(huì)的態(tài)度形成了鮮明對比,當(dāng)時(shí)高田僅僅派出一位高級副總裁出席聽證會(huì),并且仍然表示召回與否應(yīng)由車企負(fù)責(zé),僅表示“全面協(xié)助”。
由于承認(rèn)缺陷并承諾召回,高田將面臨在美國召回3400萬臺、全球合計(jì)召回4000萬臺以上的重壓,這將導(dǎo)致怎樣的巨額成本呢?2014年度財(cái)務(wù)報(bào)表中,高田以“特別損失”計(jì)入了召回關(guān)聯(lián)費(fèi)用586億日元,但這并不包括2014年11月以后的召回費(fèi)用。以2012和2014年為例,其總計(jì)856億日元特別損失對應(yīng)的召回?cái)?shù)量約1000萬臺。如此計(jì)算,其未來將面臨超過3000億日元的巨額費(fèi)用,而當(dāng)前高田資產(chǎn)卻僅為1500億日元。
入不敷出的高田出路在哪?
首先是自救為主的模式。一是增加股本的方式,但此舉將威脅高田家族對公司的控制。高田家族持有公司約59%的股權(quán),但股價(jià)今年已下跌60%,因此現(xiàn)在需新發(fā)1.5億美元股票,該家族持股比例將因此而降至不足50%。二是“瑞薩模式”的援助,也就是在新管理層監(jiān)督下,以汽車制造商和政府基金的投資來對高田進(jìn)行資本重整,這就類似于2012年瑞薩電子的紓困模式。
其次是以汽車廠商救助為主的模式。作為高田第一大客戶的本田技研已明確表示,如果高田因此陷入經(jīng)營危機(jī),將基于零部件穩(wěn)定采購的角度提供支持。日本、也是全球最大廠商豐田公司則表示,愿意出資委托獨(dú)立第三方進(jìn)行調(diào)查,本田、日產(chǎn)、通用、福特等均參與此項(xiàng)支持方案。汽車廠商之所以愿意聯(lián)合救助高田,一是因?yàn)槠囋O(shè)計(jì)復(fù)雜性,使得整個(gè)鏈條形成“一損共損”特征;二是零部件供應(yīng)商長期為汽車廠商承擔(dān)著壓縮成本的重任;三是更換供應(yīng)商需要時(shí)間和更大成本。
毋庸置疑,此次“高田門”或?qū)⒃斐扇蚋窬肿兓呺H成本將成為汽車廠商戰(zhàn)略選擇的關(guān)鍵。一場圍繞安全氣囊的供應(yīng)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即將到來。
作者供職于南開大學(xué)日本研究院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