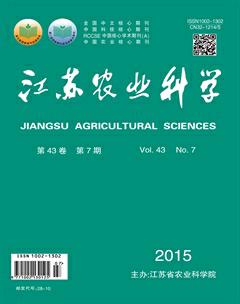維生素C拮抗草甘膦對蚯蚓急性毒性的作用
陳建華 盧敏 蔡志斌



摘要:通過赤子愛勝蚓急性毒性試驗,探討維生素C拮抗草甘膦對蚯蚓急性毒性的作用。將蚯蚓引入草甘膦濾紙中,觀察草甘膦作用下蚯蚓的形態變化并評估草甘膦的毒性等級,結果表明:草甘膦對蚯蚓的48 h半數致死濃度為(125.35±0.06) μg/cm2,為低毒型農藥。在試驗濃度范圍(23.75~380.00 μg/cm2)的草甘膦中,蚯蚓體表逐漸出現黃色液體,表現為環節腫大及充血、斷尾、體節斷開等中毒現象。高濃度草甘膦對蚯蚓具有較強的致死作用,中、低濃度亦具有一定致死效應,并隨染毒時間的延長、草甘膦濃度的升高而逐漸增加,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向草甘膦基礎液中加入維生素C(0.8~100.0 mg/L)后,蚯蚓的存活率顯著提高,并隨維生素C濃度的升高而不斷提高,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蚯蚓在含高濃度維生素C的草甘膦中未死亡,提示維生素C具有拮抗草甘膦毒性的作用。
關鍵詞:草甘膦;毒性;蚯蚓;維生素C;拮抗作用
中圖分類號: S481+.1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5)07-0411-03
草甘膦(glyphosate)是20世紀70年代開發的廣譜除草劑,由于劑型較多且不具選擇性,草甘膦不僅被用于各種農田雜草的防除,也被用于非農田雜草的治理,如園林、苗圃、道路、林業、森林、湖泊等。目前,草甘膦已成為全球用量最大、應用最廣的農藥,其年銷量穩居各農藥之首[1]。隨著草甘膦使用量、使用范圍的增加與擴大,農藥噴灑、雨水沖刷、植物根系等可使草甘膦進入環境并造成污染,目前已在全球范圍表層水體中發現草甘膦的存在,美國河流曾檢測到草甘膦的濃度高達2.2 mg/L[2]。殘留于蔬菜瓜果的草甘膦可進入人體并影響人類健康。據報道,草甘膦不僅對魚類、兩棲類動物具有急性毒性作用,對人類等哺乳動物的肝臟、免疫系統、生殖系統、內分泌系統等也具有一定毒性作用[3-8]。因此,研究如何拮抗草甘膦所引發的毒性作用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維生素C又名L-抗壞血酸,是一種廣泛存在于各類水果中的水溶性維生素。維生素C作為具有抗癌、抗腫瘤作用的抗氧化劑進入生物體后,可清除體內自由基,抑制某些化學物質氧化為致癌物,并能阻斷致癌物的活化,同時參與體內氨基酸的代謝與神經遞質的合成,以提高患者的抵抗力。此外,維生素C還具有解毒功能。本試驗擬以環境土壤模式動物蚯蚓為材料,探討草甘膦對土壤生物的急性毒性作用,并研究維生素C拮抗草甘膦對蚯蚓急性毒性的作用,旨在為機體內草甘膦毒性的防治提供理論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材料
赤子愛勝蚓(Eisenia fetida)購自福建省福州市鰲峰花鳥市場,于試驗室馴養1周后,選取體色鮮亮、行動活躍、體節完好、環帶明顯、大小一致、體質量為400~500 mg的蚯蚓進行試驗。草甘膦購自福州市農藥化肥經營部,為30%水劑,試驗時稀釋為10.24 g/L的草甘膦母液。維生素C購自福州海王福藥制藥有限公司。
1.2 草甘膦對蚯蚓急性毒性試驗
1.2.1 蚯蚓清腸處理 于直徑9 cm的培養皿底部鋪置1層濾紙,用蒸餾水潤濕后,將洗凈的蚯蚓置于其中,以保鮮膜封口,并用橡皮圈捆緊防止蚯蚓跑出,在保鮮膜上扎孔通氣,于室溫下清腸24 h。
1.2.2 急性毒性試驗 采用濾紙法對蚯蚓進行染毒試驗。設置不同濃度的草甘膦試驗組和清水對照組,取試驗組和對照組溶液各3 mL潤濕濾紙,分別置于9 cm直徑的培養皿中,使各培養皿的草甘膦終濃度分別為380.00、190.00、95.00、47.50、23.75、0.00 μg/cm2。各濃度培養皿中投入5條蚯蚓,設置4個平行試驗。投入蚯蚓后6 h內觀察其活動變化,并分別于24、48、72、96 h統計蚯蚓的死亡情況,以蚯蚓尾部對機械刺激無反應視為死亡。通過寇氏法計算得出48 h草甘膦對蚯蚓的半數致死濃度LC50及其95%置信限。寇氏法計算公式為:LC50=lg-1[Xm-i(∑P-0.5)],式中:Xm為最大劑量組劑量對數值,i為相鄰2組對數劑量的差值,P為各組動物死亡率,∑P為各組動物死亡率總和;LC50的標準誤sLC50=i×(∑P-∑P2)/(n-1),其中n為各組動物數;LC50的95%置信限=lg-1(lgLC50±1.96×sLC50)[9]。
按表1對濾紙法測定的草甘膦毒性進行等級評估[10]。
1.3 維生素C對草甘膦所致蚯蚓急性毒性的拮抗試驗
根據48 h時LD50的95%置信上下限,選取95%置信下限的草甘膦濃度為拮抗試驗基礎液的濃度,在此濃度草甘膦中加入不同濃度的維生素C作為試驗組。試驗組的維生素C終濃度分別為20.0、4.0、0.8 mg/L。試驗設置清水對照組、草甘膦基礎液對照組、系列濃度的維生素C試驗組,分別取不同試驗用液3 mL浸濕濾紙并置于相應培養皿中,各培養皿放入5條蚯蚓,設2個平行試驗組。在6 h內觀察蚯蚓的活動情況,并分別于24、48 h統計蚯蚓的死亡情況。
1.4 數據統計
采用SPSS 11.0軟件分析試驗數據的線性回歸關系,以相關系數r表示相關程度,P<0.05表示差異顯著。
2 結果與分析
2.1 草甘膦對蚯蚓的急性毒性
2.1.1 蚯蚓的中毒表現 試驗開始6 h內觀察時,清水對照組的蚯蚓在濾紙中自由爬行,一段時間后部分蚯蚓聚集成團;草甘膦試驗組的蚯蚓在濾紙中爬行一段時間后,表現出對草甘膦濾紙的回避,分別爬到濾紙下方、濾紙與皿壁邊緣、培養皿豎側邊緣,有些甚至爬到保鮮膜與培養皿的縫隙中;在高濃度草甘膦(190~380 μg/cm2)試驗組中,部分蚯蚓體表分泌黃色液體。24 h觀察時,380 μg/cm2草甘膦試驗組的濾紙上出現很多黃斑,蚯蚓保持靜止,身體拉長并貼于培養皿邊緣,部分蚯蚓開始死亡,部分蚯蚓呈“假死”狀態,用牙簽刺激蚯蚓尾部會使其迅速蜷成團。48 h觀察時,高濃度草甘膦(190~380 μg/cm2)試驗組的大多數蚯蚓環節腫大、充血,并出現斷尾、尾部體節斷開,呈“藕斷絲連”的形態,蚯蚓死亡數量增大。
2.1.2 草甘膦對蚯蚓的致死效應 由表2可知,蚯蚓在清水對照組中可正常存活96 h,而草甘膦試驗組中的蚯蚓則呈現不同的死亡率。中、低濃度的草甘膦(23.75~95.00 μg/cm2)對蚯蚓毒性作用較弱,可使其存活24 h,并于48 h內出現死亡,草甘膦對蚯蚓的致死效應隨染毒時間的延長而增強,蚯蚓在中濃度草甘膦(95 μg/cm2)中的耐受時間不超過96 h。高濃度草甘膦(190~380 μg/cm2)對蚯蚓的致死效應較強,24 h內即可致死部分蚯蚓,而380 μg/cm2草甘膦中的蚯蚓于48 h內全部死亡。
由表2可知,草甘膦對蚯蚓的48 h半數致死濃度為(125.35±0.06) μg/cm2,介于100.00~1 000.00 μg/cm2 之間,根據評估標準,草甘膦對蚯蚓的毒性等級為低毒。
2.1.3 草甘膦濃度與致死效應的關系 由圖1可知,在各作用濃度下染毒時間相同的蚯蚓,72 h內死亡率隨草甘膦濃度的升高而升高,兩者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以草甘膦濃度為橫坐標,對同一染毒時間蚯蚓的死亡率進行回歸分析,其相關性具有顯著意義(P<0.05)。染毒時間達96 h時,各濃度草甘膦對蚯蚓的致死率均接近100%,因此,染毒96 h后蚯蚓死亡率不再隨草甘膦濃度的升高而升高,兩者間的相關性沒有顯著意義(P>0.05)。
2.1.4 染毒時間與致死效應的關系 由圖2可知,在同一濃度(23.75~190.00 μg/cm2)的草甘膦作用下,蚯蚓死亡率隨染毒時間的延長而上升,兩者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以染毒時間為橫坐標,對蚯蚓死亡率進行回歸分析,其相關性具有顯著意義(P<0.05)。蚯蚓在高濃度草甘膦(380 μg/cm2)中僅能生存48 h,因此死亡率不再隨染毒時間的延長而上升,兩者間的相關性沒有顯著意義(P>0.05)。
2.2 維生素C對致死效應的拮抗作用
以濃度低于48 h半數致死濃度95%置信下限的草甘膦(95 μg/cm2)為對照組,在此基礎上加入不同濃度的維生素C以進行蚯蚓致死拮抗試驗,統計不同濃度組蚯蚓的存活率。結果(圖3)顯示:向草甘膦基礎液中加入0.8~100.0 mg/L的維生素C可明顯提高蚯蚓存活率,且存活率隨維生素C濃度的升高而升高,兩者呈明顯的劑量-效應關系。以維生素C濃度為橫坐標對蚯蚓存活率進行回歸分析,其相關性具有顯著意義(P<0.05)。向草甘膦基礎液中加入高濃度(100 mg/L)的維生素C可完全拮抗草甘膦對蚯蚓的致死效應,使蚯蚓的存活數量、生活狀態皆與清水對照組相似。
3 結論與討論
草甘膦已被證實為低毒性,從而使其在農業中的應用更加無節制。土壤中殘留的草甘膦由根吸收并積累于農作物體內[11]。目前已在食品、動物飼料中檢測到草甘膦,大豆中的草甘膦含量甚至高達17 mg/kg。有資料顯示,草甘膦在白菜中代謝緩慢,大棚噴藥5 d后仍能檢測到超標的草甘膦[12]。草甘膦可通過各種途徑進入食品,并通過食物鏈最終進入人體,此類低毒型農藥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已引起廣泛關注。草甘膦及其代謝產物氨甲基磷酸不僅可以損傷DNA,還可干擾DNA的修復,從而影響細胞周期的檢測點,細胞周期功能的失調將導致染色體不穩定,增加人類患癌癥的風險[11,13]。草甘膦通過誘發染色體斷裂、DNA損傷對動物產生的遺傳毒性已在小鼠等哺乳動物試驗中得到證實[14-15]。厄瓜多爾的一項研究發現,與草甘膦噴灑區邊界80 km外的居民相比,草甘膦噴灑區域的居民具有較高程度的DNA損傷[16],可見草甘膦對人類遺傳同樣具有潛在毒性。Benachour等用遠低于農業標準的含量,或低于糧食、飼料中殘留的草甘膦濃度對人臍靜脈內皮細胞、293胚胎腎細胞、JEG3胎盤細胞株進行染毒,發現細胞于24 h內全部死亡,提示低濃度草甘膦對人類細胞也具有一定毒性[17]。對草甘膦的生殖毒性研究表明:一方面,草甘膦通過改變睪丸雄激素受體的表達而改變其血清睪酮與雌二醇的分布,最終影響生殖細胞的產生;另一方面,草甘膦可誘導機體過氧化水平的增高,從而破壞細胞膜通透性,導致細胞氧化損傷及DNA損害,使精子數量減少、畸形率上升[18]。對大白兔的試驗表明,草甘膦可使其體質量與性欲降低,并導致異常精子、死精子的比例增加[19-21]。有關流行病學的研究發現,暴露于草甘膦的孕婦早產與流產的比例增加,且后代兒童存在生育缺陷、患多動癥的風險增加了2.6倍[11,22]。可見草甘膦雖為低毒性,進入人體后對細胞、遺傳、生殖系統等仍存在威脅。2008年,巴西對草甘膦進行了重新評估以確認其對人類健康的影響,官方建議將其毒性等級由第4級(微毒)提升為第1級(劇毒)[23]。如何降低或緩解草甘膦毒性已迫在眉睫。草甘膦對動物的制毒機制尚未明確,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誘發DNA損傷;干擾激素的合成;使機體產生過量氧自由基從而導致細胞的毒性作用[11,18,24]。
維生素C為水溶性維生素,廣泛存在于各類蔬菜、水果中,具有解毒、預防癌癥、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等作用,是人體必需的營養素。動物試驗表明,維生素C通過調控bcl-2、p53的表達使DNA免受化學誘導劑造成的損害,提示維生素C可拮抗草甘膦引起的遺傳毒性[25-27]。同時,維生素C作為抗氧化劑具有強大的清除自由基能力,可通過還原反應消除有害自由基對細胞的毒性作用。試驗前期工作已證明維生素C對草甘膦誘發的斑馬魚急性毒性、遺傳毒性具有緩解作用,本研究通過蚯蚓的急性毒性試驗再次證明維生素C可緩解草甘膦誘發的急性毒性。
草甘膦應用廣泛,雖為低毒性但仍可通過食物鏈對人體健康造成威脅。經常于飯后食用新鮮水果進行維生素C的補充,將有利于緩解微量草甘膦對人體造成的危害。
參考文獻:
[1]蘇少泉. 草甘膦述評[J]. 農藥,2005,44(4):145-149.
[2]Contardo J V,Klingelmann E,Wiegand C. Bioaccumulation of glyphosate and its formulation Roundup Ultra in Lumbriculus variegatus and its effects on biotransformation and antioxidant enzymes[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09,157(1):57-63.
[3]竇建瑞,錢曉勤,毛一揚,等. 草甘膦對人體的毒性研究進展[J]. 江蘇預防醫學,2013,24(6):43-45.
[4]Dallegrave E,Mantese F D,Oliveira R T. Pre-and postnatal toxicity of the commercial glyphosate formulation in Wistar rats[J]. Archives of Toxicology,2007,81(9):665-673.
[5]Dallegrave E,Mantese F D,Coelho R S,et al. The teratogenic potential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Roundup in Wistar rats[J]. Toxicology Letters,2003,142(1/2):45-52.
[6]傅建煒,史夢竹,李建宇,等. 草甘膦對草魚、鰱魚和鯽魚的毒性[J]. 生物安全學報,2013,22(2):119-122.
[7]肖永紅,龍婉婉,羅斯成,等. 草甘膦脅迫對中華大蟾蜍(Bufo gargarizans)神經沖動產生和傳導的影響[J]. 生態學報,2007,27(3):1177-1184.
[8]歐陽鳳. 2種農藥對牛蛙蝌蚪的急性毒性試驗研究[J]. 新鄉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7(4):63-64.
[9]武煥陽,丁詩華,唐 毅,等. 硫丹對草魚外周血紅細胞微核及核異常的影響[J]. 淡水漁業,2011,41(5):28-34.
[10]王彥華,俞衛華,楊立之,等. 22種常用除草劑對蚯蚓(Eisenia fetida)的急性毒性[J]. 生態毒理學報,2012,7(3):317-325.
[11]俞 慧,江城梅,趙文紅. 草甘膦毒性作用研究進展[J]. 蚌埠醫學院學報,2012,37(6):743-745.
[12]謝 郢,李水清. 草甘膦在大白菜中的殘留動態研究[J]. 湖南農業科學,2004(5):43-45.
[13]Bellé R,Le B R,Morales J,et al. Sea urchin embryo,DNA-damaged cell cycle checkpoint and the mechanisms initiating cancer development[J]. Journal de La Societe de Biologie,2007,201(3):317-327.
[14]康菊芳,曾 明,關 嵐,等. 草甘膦對小鼠的致突變作用研究[J]. 癌變·畸變·突變,2008,20(3):227-230.
[15]Prasad S,Srivastava S,Singh M,et al. Clastogenic effects of glyphosate in bone marrow cells of Swiss albino mice[J]. Journal of Toxicology,2009,2009:308,985.
[16]竇建瑞,錢曉勤,毛一揚,等. 草甘膦對人體的毒性研究進展[J]. 江蘇預防醫學,2013,24(6):43-45.
[17]Benachour N,Séralini G E. Glyphosate formulations induce apoptosis and necrosis in human umbilical,embryonic,and placental cells[J]. Chemical Research in Toxicology,2009,22(1):97-105.
[18]Beuret C J,Zirulnik F,Giménez M S. Effect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on liver lipoperoxidation in pregnant rats and their fetuses[J]. Reproductive Toxicology,2005,19(4):501-504.
[19]Oliveira A G,Telles L F,Hess R A,et al. Effects of the herbicide Roundup on the epididymal region of drakes Anas platyrhynchos[J]. Reproductive Toxicology,2007,23(2):182-191.
[20]Romano R M,Romano M A,Bernardi M M,et al. Prepubertal exposure to commercial formulation of the herbicide glyphosate alters testosterone levels and testicular morphology[J]. Archives of Toxicology,2010,84(4):309-317.
[21]Yousef M I,Salem M H,Ibrahim H Z,et al. Toxic effects of carbofuran and glyphosate on semen characteristics in rabbit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Health:Part B,Pesticides,Food Contaminants,and Agricultural Wastes,1995,30(4):513-534.
[22]Marc J,Mulner L O,bellé R. Glyphosate-based pesticides affect cell cycle regulation[J]. Biology of the Cell,2004,96(3):245-249.
[23]呂 芬. 巴西重新評估農用化學品[J]. 農藥研究與應用,2008,12(2):46-47.
[24]Bellé R,Le B R,Morales J,et al. Sea urchin embryo,DNA-damaged cell cycle checkpoint and the mechanisms initiating cancer development[J]. Journal de La Societe de Biologie,2007,201(3):317-327.
[25]Basiak J,Kowalik J. Protective action of vitamin C against DNA damage induced by selenium-cisplatin conjugate[J]. Acta Biochimica Polonica,2001,48(1):233-240.
[26]Bagchi M,Kuszynski C A,Balmoori J,et al. Protective effects of antioxidants against smokeless tobacco-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and modulation of Bcl-2 and p53 genes in human oral keratinocytes[J]. Free Radical Research,2001,35(2):181-194.
[27]Assayed M E,Khalaf A A,Salem H A. Protective effects of garlic extract and vitamin C against in vivo cypermethrin-induced cytogenetic damage in rat bone-marrow[J]. Mutation Research,2010,70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