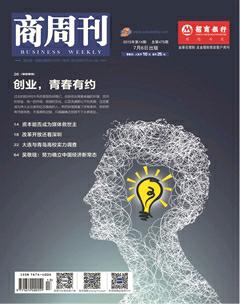致我們無處安放的鄉愁
付如初
無論如何,在文學界總是被認為沒有崛起、沒有創作出標志性文本的70后,實際上以更為深廣的方式,參與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也承擔了一代人的使命。這種使命,橫跨鄉村和城市,見證了“文革”后中國的每一步發展。
梁鴻的“鄉村傳記”
2008年到2013年,圍繞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穰縣吳鎮梁莊村,梁鴻寫了兩本書:《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前一本寫“留守”在梁莊的人,后一本是“出梁莊記”——寫梁莊人在全國各地的打工生活。隨后,兩本書獲得了巨大反響。在各類好書評選中榜上有名自不必說,梁莊也由此從中國近70萬個行政村中脫穎而出,成為文化意義上的典型村——中國改革進程中的一個縮影。
梁莊雖不能和華西村、小崗村、大寨那樣因參與重大歷史進程而成為標志性的歷史名村,但假以時日,它或許可以和費孝通的江村一樣,獲得一定的社會學地位。梁鴻在田野調查和“非虛構”基礎上呈現的梁莊生態,某種意義上也為三農問題、城鎮化問題、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等問題提供了普通大眾可知可感的抽樣標本。
或許,兩本書的反響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包括梁鴻自己。正如她在很多訪談中反復表達的那樣,作為梁莊的女兒、從梁莊走出來的文學博士,她本來想做的,只是一件跟文學、跟自我、跟生命有關的事兒。
她警惕書齋生命的空洞,警惕任何潮流或派別,警惕自己可能產生的啟蒙者的眼光,她只是想重新感受自我來處,感受大地和生命本身。甚至在寫下第一本書的時候,她還不知道什么是“非虛構”,更不知道這種寫法還能夠在“小說力竭的邊界之外”,獲得一種“‘史詩般的精神品質。”(李敬澤語)
“文變染乎世情”,世情總是比文學更豐富,而文學總是比世情更本質。在時代太過復雜,資訊太過發達的當下,文學幾乎失去了對現實的提煉能力和概括能力。或者說,擅長“大處著眼,小處落筆”的虛構文學欠缺描摹現實的功力,從而欠缺與這個復雜的時代相匹配的大作品——君不見,有很多小說都是直接把新聞素材收進去了。
而此時,梁鴻以調查采訪為基礎為梁莊寫的“傳記”,反而擔當了通過小人物命運捕捉現實、概括時代的使命:梁莊之小與中國之大,梁莊人物之卑微與時代問題之宏大,如佛家的芥子須彌一般,在梁鴻的兩本書里自然而然地渾然一體。
于是,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的每一個事件:大到南水北調工程,小到黑摩的和城管的矛盾,無不與梁莊有關。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曾經或多或少遇到的大大小小的問題:環保、土地流轉、留守兒童、農村醫保、傳銷、富士康、城中村、蟻族、職業病、垃圾電話等等,無不與梁莊有關。
可以說,為一個梁莊立傳幾乎就是為近四十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中國立傳。而倘若附會錢鍾書先生“史蘊詩心,詩具史筆”的理論,那么,為梁莊立傳也是在為中國鄉村修史。
從雙水村到梁莊:中國鄉村史的一種寫法
雙水村是路遙筆下的奮斗青年孫少平的家。時隔30年之后,見證新一輪“路遙熱”的讀者和觀眾對它都已不再陌生。而因為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展現這個村莊的生態,雙水村就更加讓人印象深刻了一這一點說起來非常難能可貴,要知道,《平凡的世界》這種被很多人當成勵志書讀的原著,被改編成電視劇的時候極容易墮入庸俗成功學的套路。
雖是小說,但路遙在描寫雙水村時,是當成紀事型文本來寫的。路遙出身鄉土,對鄉村社會的一切并不陌生。而為了寫這個小說,他更是查閱了1975年到1985年幾乎所有的《人民日報》和《參考消息》,還用了3年的時間體驗生活,做田野調查。
在路遙筆下,1985年之前的雙水村,父慈子孝、長幼有序、中國鄉村傳統的倫理秩序頑強而堅韌。盡管也有階級斗爭、有家族矛盾、有以孫福堂為代表的舊勢力對新事物的抵制,甚至還有孫玉亭的通奸丑聞等等,但傳統美德作為村莊精神的底盤,還堅如磐石。或者說,那時候的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形成,而且,因為遠離建國后一系列政治波動的中心,鄉村受到的沖擊反而比較小。
于是我們還在經濟貧窮的雙水村看到了倫理的富足,誠信、仁義、自尊、忠貞、善良、美好等一切美好的品質都在雙水村閃耀著誘人的光芒。路遙說,“只要有人的地方,世界就不是冰冷的。”于是,離鄉背井的孫少平能夠一直用雙水村的行為方式,走在“脫村進城”的路上。他的精神困境總是來自于貧窮本身,而沒有倫理方面的困惑。
到了梁鴻筆下的梁莊,改革開放30多年后,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鄉二元結構已然形成,“以姓氏為中心的村莊,變為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于是,我們看到了為了種弟弟的地,吃弟弟的低保而拒絕認弟弟尸首的哥哥;看到了強奸80歲老太太的16歲少年;看到了感嘆“世界上最壞的東西就是理想”的離鄉青年;看到學校變成了養豬場;看到了黑色的河流;看到了因為淘沙賣錢而形成的“吃人的坑塘;看到了因為性壓抑而自殺的留守婦女……
應該說,鄉村的絕對貧窮有改觀,但鄉村的破敗,從環境到倫理,從外在到內在,更讓人揪心。雙水村一切讓人依戀、向往和懷念的東西,在梁莊都變成了“隱結構”,只有在深入人物內心的時候,才偶爾得見,但稍縱即逝,脆弱不堪。在梁鴻筆下,他們每個人都有名字,甚至他們每個人都有性格,但在讀者心中,他們又往往是實實在在的時代的“無名者”,因為在他們身上,命運感要遠遠弱于問題感,個體特征要遠遠弱于群體色彩。
從雙水村到梁莊,或許可以勾勒出一種中國鄉村歷史的變遷圖:依戀鄉土的孫少安越來越少,投奔城市的孫少平越來越多,而在這種“人的流動”中,鄉村秩序被改寫了一不僅是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所說的鄉村秩序被改寫,即便是新中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的鄉村秩序也被改寫了。梁鴻試圖用一個個在時代洪流中微不足道的“無名者”的經歷,捕捉這種鄉村歷史變遷的痕跡。她極力讓“我”退居幕后。索爾仁尼琴在“全景歷史”著作《紅輪》中說:“歷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決于個人的細枝末節,而這些細小的東西又經常為歷史所鮮知。”
當然,路遙有烏托邦化雙水村的筆調,正如陳忠實有烏托邦化白鹿原的筆調、賈平凹有烏托邦化商州的筆調一樣——文人的鄉愁,或者知識分子對鄉土文化的懷想,往往容易流露出這樣的傾向,一種類似沈從文“人性小廟”的情懷。這也是中國自“五四”以來,社會結構發生較大變動之后,文學的潮流之一。
而梁鴻極力想避免的,正是這樣的筆調。或者說,新的歷史環境和新的文體要求,都決定了她須得擯棄骨子里的抒情和寫意,正面迎視這些問題。但她的迎視和面對,又時常帶著困惑和猶疑。她毫不回避自己的無力、煩躁和想逃離,也坦陳自己的傷感、痛苦和軟弱,由此她陷入了有關“真實”和“知識分子道德”的困惑,她說,“我終將離梁莊而去”,也“終將無家可歸”。
坦率說,作為一個讀者,最害怕在面對令人心痛的鄉村破敗、面對令人心痛的小人物命運的時候,作者有太多的感性和憤激。中國不缺少這樣的文學,讀者也不愿意被這樣“煽情”。某種程度上,梁鴻的梁莊之所以獨特,恰恰在于她沒有任由自己的情感四溢,她沒有犯知識分子面對復雜社會問題時候容易出現的“意圖倫理過剩,責任倫理匱乏”(馬克思·韋伯語)的“藥方師”的幼稚病。準確地說,是梁鴻在尊重生命基礎上的自我控制能力,是她在感性采訪之上的理性思考,是她向內轉的自我審視和自我反省,是她用文學的復雜性精神呈現現實的復雜性的方式,深深打動了我。
“田野里響起誠摯的旋律”
其實,將歷史命運化,將命運歷史化,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就好像做田野調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一樣。在寫兩本書的過程中,梁鴻多次返鄉,跟梁莊人聊。尤其是寫第二本書,她追蹤鄉親們打工的足跡,跑了10余個省市,采訪了340多個人,歷時兩年。
她跟他們一起住出租屋,進他們所在的有毒的生產車間,進富士康的工廠。她像一個走親戚的鄉親一樣,貼近他們的生活,聽他們談自己的經歷、甚至是“隱私”。他們信任她,甚至是不求回報地“配合”她。每一次的交流,開始、結束,都是具體的過程;每一個記錄,開始、結束,都和具體的性格有關。人與人的接觸是最微妙的,人與人的深入交流是最難的,尤其對于梁鴻這樣離開故鄉的人,距離感其實是可想而知的。
好在,有她的父親。父親是她“重返田野”的橋梁。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注意到,每一次采訪,甚至每一次電話聯系,都是通過父親。而東奔西走于各個城市的時候,也常常能夠見到梁鴻父親的身影。梁鴻說,自己每次見到母親的墳,對故鄉的歸屬感都會更加清晰。實際上,有父親在身邊,她重新尋找歸屬感的每一步才得以實現。父親在梁莊這個“熟人社會”所建立的基于血緣和鄉情的人際關系,是梁鴻得以為梁莊立傳的重要支撐。某種程度上,父親也是梁莊與外界聯系、讓外界了解的一個通道。隨著一代代的人老去,城鄉二元結構的日益固化、社會階層的日益固化,不知道,這樣的通道會更多還是更少……
在聽哥哥毅志講故事的時候,梁鴻說,這么多年過去了,她居然不知道自己的親哥哥曾經有被收容、被打的經歷。而她反復提到的,自己從小一起長大的小柱的死,更是讓人痛徹心扉。她沒能采訪到小柱,因為那時候她還沒有開始做調查。后來,從別人的講述中,她才理出了小柱的生命軌跡。從1989年開始,16歲的小柱開始打工,先后到過北京的煤場、河北的鐵廠、青島的電鍍廠等等,直到2001年,28歲的小柱返鄉去世。除了小柱,還有那個和北京人談戀愛,被傷得千瘡百孔的“狐貍精”梁歡;還有被鄰居猥褻了的黑女兒,她讓人在名譽和法律求助之間游移不定……其實,“無名之死”豈止是一個小柱,歷史車輪碾壓的,又豈止是梁莊人。
里爾克在《故鄉之歌》中這樣寫道:“田野里響起誠摯的旋律;不知道,我心中發生了什么……‘來吧,捷克的姑娘。給我唱支故鄉的歌。姑娘把鐮刀放下來,又是嗬來又是哈,便坐在了田埂上唱起‘哪兒是我家……現在她沉默了,眼睛朝著我,雙淚交流——拿著我的銅十字幣,無言地吻著我的手。”
70后的文學使命和社會責任感
除了梁鴻,另一個70后熊培云也在關注鄉土中國的問題。他的《一個村莊里的中國》,試圖從文化的、歷史的角度關注江西鄉村的變遷。跟梁鴻直接寫中原農村的現實痛感相比,熊培云寫的是江西農村歷史的和文化的痛感。而且,跟梁鴻的白省和困惑相比,熊培云顯得更為自信、自我更為強大。
顯然,這有地域的差別,河南作為人口眾多的農業大省,在城鎮化進程中受到的沖擊可能是最大的。同時,或許也有性別的差異,熊培云的鄉村中國是向外的,縱橫捭闔的,有國外經驗的參照、有歷史的參照;而梁鴻的鄉村中國是向內的,溫婉內聯的,大多是人與人、人的內心和人的情感。因而,熊培云的村莊中國顯得理念更為強大,而梁鴻的梁莊中國細節更為豐富。
當然,最根本的是角度和立場的差別。熊培云說:“我們著力改造一個社會,首先需要做的是改造關系,改造制度,而非改造人性。”而梁鴻說:“它不是一個為民請命的文本,而是一種探索、發掘和尋求。它力求展示現實的復雜性和精神的多維度,而非給予一個確定性的結論。”
在轉型期的中國,熊培云和梁鴻的不同選擇,除了個體的原因,或許也涉及有關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和身份意識的問題,而這又是一個大問題。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而言,最常談到的是北宋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自從“士”具有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某些特征之后,薩義德的《知識分子論》開始受到推崇。因為特殊的經歷,薩義德強調學術和政治的結合,他贊賞站在弱者一方的知識分子,贊賞知識分子的圈外人狀態,他特別警惕知識分子的專業化。當然,同時他也指出:“知識分子不必是沒有幽默感的抱怨者”,他們要“知道如何善用語言,知道何時以語言介入。
或許,結合閱讀熊培云和梁鴻的書,更有利于對農村問題的體會和認識。梁鴻缺乏的歷史視野能夠在熊培云的書里找到,而熊培云缺乏的現象支撐能夠在梁鴻的書里找到。后來,梁鴻從梁莊拓展到吳鎮,從去年開始,她的“云下吳鎮系列”開始在《上海文學》連載,不過不是訪談的形式,而是小說。如果梁鴻的梁莊系列訪談能夠繼續下去,采訪一下跟梁莊人打交道的城里人,《中國在梁莊》或許會更為完整和震撼吧。
無論如何,在文學界總是被認為沒有崛起、沒有創作出標志性文本的70后,實際上以更為深廣的方式,參與了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也承擔了一代人的使命。這種使命,橫跨鄉村和城市,見證了“文革”后中國的每一步發展。文體上,當然也不局限于“非虛構”。除了梁鴻和熊培云,這個名單里還有徐則臣、阿乙、路內、王十月、張楚……只是他們生不逢時,趕上了文學被市場沖擊得落寞無邊的時代。
如果故鄉背后站著的是整個時代
梁鴻的采訪對象,不全是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也有走出梁莊的大學生和成功人士。這兩個采訪對象在北京。
大學生畢業于師范學院的美術專業,到北京打拼之后,住在著名的蟻族聚居地唐家嶺,后來慢慢成長為一名商裝設計師。工作中,他飛機來去,住高檔酒店,接觸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面對的是世界各地的高端客戶,喝的是高檔紅酒,偶爾還說英文。然而,回到家里,就是城中村的小房子。他沒戶口,沒房子,孩子生出來了,還需要回鄉托人才能辦農村戶口。他一直積極努力,也對職業前景充滿信心,但就是“沒有歸屬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條腿插進城市,另外一條腿一直舉著,不知道往哪兒放”。
成功人士是個千萬富翁。成功的過程充滿曲折,曲折之一是因為自己是河南人。所以,他不做家族企業,而用“現代管理”。他一方面說要回縣城買山坡蓋別墅,一方面“很鄙夷那個他曾經生活了將近30年的地方”,并以“現代管理”的名義遮蔽他的厭棄和逃避。
其他的采訪對象,那些奔波在窮愁之路上的梁莊人,固然讓人同情、讓人憂思,但情感上是有間離的。而這兩個人的命運,尤其是大學生的命運,更讓人有代入感。而且,他因為受過教育走出梁莊、走進城市,而不是因為生活所迫,這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應該是最合理、最正常、甚至是最值得鼓勵的階層流動。惟其如此,他的生存狀態、他的情感心理,才更令人深思,也牽涉更多的、更深層次的問題。他們比那些沒有受過教育的梁莊人更有“鄉愁”,但他們卻更加無處寄托。
2013年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中這樣的表述曾經讓很多人意外:“依托現有山水脈絡等獨特風光,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城市居民望得見山、看得到水、記得住鄉愁。”據說“鄉愁”這種情感化的詞匯是第一次進入中央文件。可見,它成了一個多大的問題——“鄉愁”之無處托寄何止是鄉村淪落的結果,它還是整個時代中,所有靈魂和精神被物質沖擊得無處安放的狀態。
梁鴻顯然不愿意自己的書成為“問題文學”,因為那可能限制這本書可能達到的深度和廣度,也因為作為學者,她開不出藥方,她甚至不能化解自己的焦慮。她只想用自己的筆寫寫故鄉,卻沒想到,故鄉背后站著一個時代。
有誰會有勇氣跟大時代談談自己的鄉愁呢?
偉大的德語詩人里爾克一生漂泊,他寫過很多關于村莊的詩,其中一首叫做《我懷念》,這樣寫道:
“我懷念:
太平盛世一個樸素的小村莊,
里面有公雞長啼;
而這村莊久已迷失
在花之雪里。
在穿著星期日盛裝的小村莊里
有一座小屋;
一個金發頭顱從網眼窗帷里
窺望出去。
戶樞迅速沙啞地
向門呼救,一一
然后在房間里飄著一縷淡淡的
淡淡的/薰衣草的芳香……”
(據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