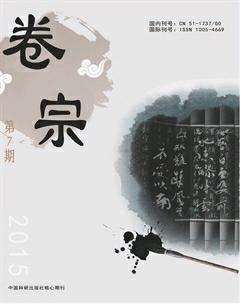從波伊斯看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特征
未小妹
摘 要:本文試以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大師博伊斯為例淺析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特征。
關(guān)鍵詞:波伊斯;后現(xiàn)代主義
對后現(xiàn)代藝術(shù)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兩位大師,約瑟夫·波伊斯屬聰明實干型,馬塞爾·杜尚屬自娛自樂型。波伊斯誠心誠意的投身于藝術(shù),反對權(quán)威,反對虛無;杜尚用虛無反對權(quán)威。波伊斯認為“人們高估杜尚上的沉默”,他看不慣杜尚對藝術(shù)和社會的若即若離。他本人則是一個積極地改革家,認為藝術(shù)應該介入生活,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改造社會。他關(guān)注藝術(shù)的人類學意義,以及它對社會的影響。杜尚則不然,他看到,所謂藝術(shù)活動,不過就是人類的無數(shù)行為之一,它的出現(xiàn)是由于需要,跟我們烹飪或者制作實用器皿一般無二。他選擇了藝術(shù)作為來表達他的放下。
波伊斯關(guān)于藝術(shù)的想法:“藝術(shù)的目的是使得人們自由,因此藝術(shù)于我是關(guān)于自由的科學。”他的藝術(shù),與其說是為了展示藝術(shù)使人自由的可能性,不如說是讓自己自由。藝術(shù)于他不是游戲不是娛樂,是療救,是不得不說的表達。他的“擴展的藝術(shù)概念”把一切媒介和人類的行為都囊括到藝術(shù)中。
1 多元化
在20世紀60年代晚期,藝術(shù)在形式和內(nèi)容上都呈現(xiàn)出百花齊放的狀態(tài)。自然在觀念藝術(shù)中解放,藝術(shù)家個人身體成為形式與意識的舞臺。藝術(shù)也更多的與藝術(shù)家的意圖、想法有關(guān),而與風格樣式、技巧無關(guān)。藝術(shù)家豐富多彩的內(nèi)心世界投射到千奇百怪的多元化的藝術(shù)上。藝術(shù)家把豐富多彩的個人生活經(jīng)驗與創(chuàng)作過程聯(lián)結(jié)在一起,把不同的藝術(shù)樣式、材料、方法、技巧等匯通于一體,觸及到知覺世界的一切層面。藝術(shù)史的書寫不再以風格樣式主義為標準來寫作,個體的藝術(shù)家不再被圈定在某一個藝術(shù)風格流派之中,任何形式都可為其所用。
波伊斯提出的“擴展的藝術(shù)概念”把一切媒介和人類的行為都囊括到藝術(shù)的概念中來。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方式更是信手拈來,不拘一格。《給卡賽爾的7000棵橡樹》、《清掃運動》、《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講解圖畫》和《荒原狼:我愛美國,美國也愛我》歸為行為藝術(shù);《給卡賽爾的7000棵橡樹》因其在卡塞爾市內(nèi)街道旁被作為公共藝術(shù);《歐亞—西伯利亞交響曲第32章》屬于以混合媒介為經(jīng)典模式的激浪派,把不同的藝術(shù)形式都同時并且不一致地在事件中展現(xiàn);現(xiàn)成品被賦予新的定義成為藝術(shù)品或其中的一部分,《油脂椅子》、《大鋼琴》、《磔刑》和《綠色提琴》中的現(xiàn)成品則是最日常的物品,它們同時也可以被裝置藝術(shù)所囊括;《如何向一只死兔子講解圖畫》和《蜜蜂.面包》則被分在過程藝術(shù)中;波伊斯認為聲音也是雕塑,雕塑也可以被聽到,因此經(jīng)常演出“聲音雕塑”,《伊菲格尼/蒂多.安東尼》由斧子、麥克風、喊叫、吹哨、呼叫、嘶鳴、獨唱、打擊樂、朗讀、播放錄音帶、白馬、柵欄、草料組成,被放到聲音藝術(shù)一欄中;如果他組織的德國學生黨可作為一種行為藝術(shù)的話,那么也不妨把它看作一種政治藝術(shù)。
同時也可以看出多元化的藝術(shù)形式分類也不存在嚴格的界限,重點在于它們?yōu)樗囆g(shù)家所用。波伊斯做的是所謂“通感藝術(shù)”,他的作品是對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和意識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
2 互動性
受接受美學影響,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不必對自己的藝術(shù)品負闡釋的權(quán)責,藝術(shù)品涵蓋寓言、個人幻像、符號意象以及對社會、環(huán)境、政治等的反應、冥想,歡迎觀者主動介入。
然而波伊斯的《給卡賽爾的7000棵橡樹》、《清掃運動》不僅體現(xiàn)出與大眾的互動,還有與自然的緊密聯(lián)系。在《如何向死去的兔子解釋繪畫》和《荒原狼:我愛美國,美國也愛我》中不但與動物互動,更可貴的是前者的一種剔除人獸之別,表達人獸同感,進而質(zhì)疑“人類中心主義”,后者以實際行動證明人與動物相互交融、和平共處的可能性。
博伊斯不僅用作品訴于人,而且讓人參與其間。觀眾的欣喜和震怒都是藝術(shù)的一部分。
3 大眾化
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可選擇的東西是從大眾生活、消費、生產(chǎn)和大量的及其復制中產(chǎn)生的,是豐富多樣的。波伊斯提出的“擴展的藝術(shù)概念”把藝術(shù)的主體從單個藝術(shù)家擴展到整個人類。
《給卡賽爾的7000棵橡樹》包括7000次反復栽植樹和豎玄武巖的儀式性動作,把人同其所處的地點相聯(lián)結(jié),透過7000棵樹和7000個玄武巖,將自然、城市、人緊緊地聯(lián)系到一起,而整個時間過程也是計劃的一部分。這種跨越時空的、活動的社會雕塑,以全新的形式及載體反映了人類對自身生存空間環(huán)境的破壞問題,并試圖進行補救。表達了他對城市文明使自然遭到破壞的質(zhì)疑,城市越大,對自然的破壞就越大,各種矛盾的根本在于人類生存與自然資源之間的矛盾。整個作品不僅僅建造了一片森林,更借助一遍遍儀式的重復,使作品的主題更加明確、放大,提出了是建造還是破壞、是生存還是死亡的反詰,不斷地提示人們關(guān)注自然、關(guān)愛生命。
在二戰(zhàn)中身受重傷的波伊斯被韃靼人用油脂和毛氈所救,所以他認為油脂和毛氈最能體現(xiàn)“暖性特質(zhì)”,在《油脂椅子》中便用這些材料做成社會雕塑來表達自己對人間的愛。《清掃運動》亦是讓普通民眾參與其中。
4 不確定性
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在二戰(zhàn)后面臨人類的價值準則混亂的局面,藝術(shù)不再適于明確的定義。波伊斯的“社會雕塑”,將不可塑的材質(zhì),如油脂、蜂蜜、聲音、光影、動作、語言乃至動物和人都借用到創(chuàng)作中。《油脂椅子》在視覺形象上簡單得令人困惑,它只是一塊成楔形的黃油,置放在椅座上,成45°角。正是這樣一件有巫術(shù)意味的“擺設”體現(xiàn)出不確定性精神。波伊斯自釋道:我用油脂的愿意是要激發(fā)討論……這種可塑性具有心理上的影響力——人們本能地感覺到它與內(nèi)心的過程及感情有關(guān)系。
這為藝術(shù)觀念增添新的活力,追問雕塑能夠是什么,引入時間和變化的因素,他所有的雕塑都是流變的、未完成的過程在它們的大部分中繼續(xù)著:化學發(fā)酵、變色、腐爛。干枯。每種東西都處于變化的狀態(tài)中。
當他手持刀刃被割破流血的時候,卻專心地去包扎刀刃而不是手指,他在常識的規(guī)定性之上確實達到了超越的精神境界。也許這意味著當人受到傷害時是選擇彌和創(chuàng)傷,還是選擇消除再次受傷害的可能性。于是,他的不確定性突然具備了深刻的意義。
5 寓言性
波伊斯是寓言儀式的大師,他的藝術(shù)從語言、思想開始,在說話里學得,形成觀念,反過來又將言辭、思想做雕塑,在物性中彰顯。“社會雕塑”是其寓言方式,救贖是其寓言的主題,貫穿于他古怪的歷史/文化/政治的圖像志和修辭學:以國際主義取代種族主義,以創(chuàng)造取代毀滅,以人類的生存感取代民族感,以綠色取代棕色,以暖取代冷。這些指向作用于語言學轉(zhuǎn)喻而富有社會功能。波伊斯的作品反復使用油脂、毛氈、十字架、雪橇救護車,使用冷/暖相對立轉(zhuǎn)化的媒材,使用傷殘軀體模擬物:死動物標本。骨頭、繃帶、燒焦的香腸、剪下的指甲、牙模。這些表象隱晦的存在物即構(gòu)成隱喻的基本材料,而隱喻又是寓言得以成型的材料,是構(gòu)成其“社會雕塑”的前提。在時間的縱聚合軸上帶有隱喻性質(zhì)的物象,被移置到特定的環(huán)境中,或移置列空間化的現(xiàn)象式環(huán)境中,因而改變其含義和性質(zhì),這就是轉(zhuǎn)喻。轉(zhuǎn)喻對波伊斯的救贖寓言來說,是一種順勢療法。《油脂椅子》、《綠色提琴》、《磔刑》等都是如此。
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特征的多樣性不是僅僅通過波伊斯一個人能說得清,但是波伊斯不僅在藝術(shù)史上開拓出現(xiàn)的理念和形式,還為整個人類與自然的關(guān)系做出貢獻,不愧為知行合一的藝術(shù)大師。
參考文獻
[1]馬永健,后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20講,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
[2]王瑞蕓,杜尚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
[3]島子,后現(xiàn)代主義系譜,重慶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