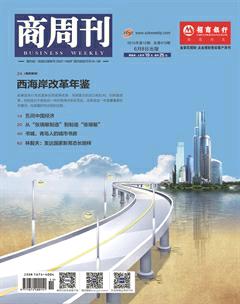會(huì)思考的新區(qū)
孫婧
國(guó)家戰(zhàn)略、區(qū)域性自貿(mào)區(qū)、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自貿(mào)區(qū)協(xié)定,這些大題材、大利好無(wú)疑會(huì)給新區(qū)乃至整個(gè)國(guó)家注入強(qiáng)大活力,但把利好變?yōu)楝F(xiàn)實(shí),歸根結(jié)底取決于新區(qū)的實(shí)力。
從1992年到2012年10年時(shí)間,中國(guó)只設(shè)置了上海浦東、天津?yàn)I海、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群島、甘肅蘭州、廣州南沙等6個(gè)新區(qū)。而從2014年1月開(kāi)始到今年4月,不到一年半的時(shí)間,國(guó)務(wù)院就連續(xù)批復(fù)了6個(gè)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使新區(qū)總數(shù)達(dá)到了12個(gè)。從10年6個(gè)到16個(gè)月6個(gè),新區(qū)已經(jīng)從高層意志轉(zhuǎn)變?yōu)榈胤阶杂X(jué)。
盡管同為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12個(gè)新區(qū)卻并非平分秋色。從管理體制看,只有浦東新區(qū)、濱海新區(qū)是行政區(qū),設(shè)立區(qū)委區(qū)政府,其余新區(qū)都是行政管理區(qū),只設(shè)立管委會(huì);從行政級(jí)別上看,只有浦東、濱海、兩江依托其所屬直轄市,行政級(jí)別一般都調(diào)整至副省級(jí)。而其余新區(qū)依托的城市均為地級(jí)或副省級(jí),這些新區(qū)想要得到與上面三區(qū)同樣的行政級(jí)別,就意味著脫離了依托城市的管轄,幾乎不可能實(shí)現(xiàn)。
但作為新一輪改革開(kāi)放的試驗(yàn)區(qū),新區(qū)的所作所為絕不會(huì)被出身限制。如果說(shuō)過(guò)去10年的新區(qū)設(shè)置往往反映了國(guó)家意志,而新一輪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則更像是中央對(duì)地方政府進(jìn)行的新區(qū)建設(shè)成果的肯定。
發(fā)展到今天,即使是浦東這樣“高配”的新區(qū),也感到土地、人力成本、政策優(yōu)勢(shì)不再。所有新區(qū)都意識(shí)到,傳統(tǒng)依靠稅收減免、廉價(jià)勞動(dòng)力與土地進(jìn)行招商的模式已經(jīng)過(guò)時(shí)了。相比GDP與財(cái)政收入,積極探索效率與公平統(tǒng)一的新機(jī)制與新體制尤為重要。對(duì)新區(qū)而言,發(fā)展不能局限于地域經(jīng)濟(jì),而需要從國(guó)家的戰(zhàn)略層面考慮,通過(guò)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huì)與文化等基本制度的創(chuàng)新,依靠各自獨(dú)特的地緣優(yōu)勢(shì),為全國(guó)新一輪綜合改革走出新路。
基本制度設(shè)計(jì)方方面面,而制度創(chuàng)新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從根本上切斷政府公權(quán)力與市場(chǎng)私立之間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系,讓“有限的政府、公民社會(huì)與完善市場(chǎng)”成為未來(lái)區(qū)域發(fā)展的基本制度框架。觀察新區(qū)們的大動(dòng)作,制度創(chuàng)新帶來(lái)的效果不是“減稅”就是“簡(jiǎn)政”。天津?yàn)I海新區(qū)在李克強(qiáng)總理的見(jiàn)證下封存了109枚公章;南沙新區(qū)要吸引香港地區(qū)共同建設(shè),則更需要解放思想,進(jìn)行關(guān)鍵制度的創(chuàng)新;在西海岸的創(chuàng)新行政管理體制,用一個(gè)月左右時(shí)間基本完成了國(guó)家級(jí)開(kāi)發(fā)區(qū)和縣級(jí)市合并,是全國(guó)首個(gè)完成這項(xiàng)改革的國(guó)家級(jí)新區(qū),擺脫了行政體制的束縛。
如果花一天時(shí)間去瀏覽12個(gè)新區(qū)的報(bào)紙,會(huì)發(fā)現(xiàn)他們幾乎無(wú)一例外地發(fā)出了“決不能走老路”、“成敗取決于制度創(chuàng)新”的呼喊。大占土地、大蓋高樓、大進(jìn)大出的粗放制造不能再出現(xiàn)在新區(qū)的土地上,取而代之的是不遺余力地推進(jìn)創(chuàng)新創(chuàng)造,并有向自己“動(dòng)刀”的精神。
新區(qū)之后,各地又展開(kāi)了一輪自貿(mào)區(qū)申報(bào)競(jìng)賽,但在爭(zhēng)取批復(fù)的同時(shí),理性與思考的痕跡更加明顯。上海自由貿(mào)易試驗(yàn)區(qū)消息剛公布時(shí),社會(huì)還按照以往思維慣性猜測(cè)試驗(yàn)區(qū)能享受到的優(yōu)惠政策,然而國(guó)務(wù)院會(huì)議將“轉(zhuǎn)變政府職能,探索負(fù)面清單管理”放在首位,顯示制度創(chuàng)新才是試驗(yàn)區(qū)的重心所在。上海自貿(mào)區(qū)意識(shí)到,自己存在的目標(biāo)不是爭(zhēng)取多少優(yōu)惠政策,而是要建立一套與國(guó)際接軌的、新的制度體系,實(shí)現(xiàn)對(duì)投資、貿(mào)易等領(lǐng)域的高效管理。
沒(méi)有優(yōu)惠反而有任務(wù),國(guó)務(wù)院常務(wù)會(huì)議給了上海自貿(mào)區(qū)一份“探索負(fù)面清單”考卷。這與10年批復(fù)6個(gè)新區(qū)的節(jié)奏完全不同,過(guò)去自上而下由中央統(tǒng)一調(diào)度的改革開(kāi)放發(fā)展到今天,國(guó)家更注重區(qū)域自下而上的創(chuàng)新對(duì)外開(kāi)放模式。考卷發(fā)給上海自貿(mào)區(qū),但答題并非是上海的特權(quán),這更像是一種啟發(fā),其他區(qū)域也開(kāi)始了自己的改革與嘗試。
中韓自貿(mào)區(qū)于6月1日簽署,這是中國(guó)迄今為止涉及國(guó)別貿(mào)易額最大、領(lǐng)域范圍最全面的自貿(mào)協(xié)定,形成的將是一個(gè)人口高達(dá)13.5億、GDP高達(dá)11萬(wàn)億美元的共同市場(chǎng)。把新區(qū)或自貿(mào)區(qū)放在中國(guó)越加深刻融入WTO框架的大背景下,各地之間的無(wú)差別、統(tǒng)一市場(chǎng)和公平競(jìng)爭(zhēng)只會(huì)成為常態(tài),因?yàn)橄拗菩浴⒈Wo(hù)性或有差別地享受優(yōu)惠政策根本不符合WTO游戲規(guī)則。
國(guó)家戰(zhàn)略、區(qū)域性自貿(mào)區(qū)、國(guó)與國(guó)之間的自貿(mào)區(qū)協(xié)定,這些大題材、大利好無(wú)疑會(huì)給新區(qū)乃至整個(gè)國(guó)家注入強(qiáng)大活力,但把利好變?yōu)楝F(xiàn)實(shí),歸根結(jié)底取決于新區(qū)的實(sh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