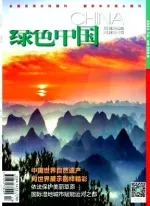“貧二代”勿讓尊嚴在夾縫中生長
文 夕 月

“貧二代”,是相對于“富二代”的叫法,是指在中國改革開放環境下社會經濟發展而帶來的社會分層,在改革開放中的普通工人、農民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帶來的財富的人依然貧窮,將這類人稱之為“貧一代”,而他們的子女由于基礎環境差,同時得到教育少仍然未能擺脫貧窮,稱之為“貧二代”。2015年年初,《人民日報》刊文指出,在中國已經發生了貧困的代際傳遞,產生了“貧二代”:“貧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并形成了階層和代際轉移,一些貧者正從暫時貧困走向長期貧困和跨代貧窮。如果不想辦法改變這一情況,貧富差距便會趨向穩定化和制度化,成為一種很難改變的社會結構,社會階層流動通道也將被嚴重堵塞。”
大學生“貧二代”未來堪憂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委托有關單位開展的一項針對1200名接受過資助的貧困學子的調查顯示,受資助學生的家庭經濟情況困難,呈現“常態化貧困”趨勢。從困難類型上看,父母雙方均有收入來源的家庭占61.7%,其中大部分是父母雙方務農(46.3%);32.3%的家庭僅靠父母其中一方的職業收入;另有6%的子女,從父母任何一方都得不到經濟支持。家庭供養率(家庭人口數與家庭勞動力數比值)高,平均值達到2.85,意味著1個勞動力要供養接近3個家庭人口。而致貧因素上,職位收入低是主要因素,家庭變故位居第二。即使父母雙方都有工作,家庭的收入依然處于較低水平,成為一種“常態化貧困”。
在調研中,有學生表示:“不怕苦,不怕累,只怕沒機會。”這份調研報告指出:“機會公平是最重要的公平,然而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最缺乏的恰恰就是機會。他們曾經將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現實是這條路越走越難,不少專家認為我們的教育體制已逐漸失去了承載階層流動的職能。”
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3年應屆生就業調查報告》顯示,從畢業生的城鄉來源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的普通本科院校畢業生成為就業最為困難群體,失業率高達30.5%。
農村貧困大學生是“貧二代”中頗引人關注的群體。高失業率意味著大學4年的書本知識并未給他們帶來一份體面的工作,意味著他們無顏面對父老鄉親,意味著“貧二代”中本來最有希望依靠知識改變命運的這一部分人,他們的夢想還未出發,在現實面前就已經折損。對受調查的受資助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而言,很多情況下上大學需要以犧牲父輩的生活為代價,背負著整個家庭甚至家族的期望,壓力頗大。
另一方面,許多貧困大學生畢業了沒人給指導,沒有太多可靠的信息源,父母都是田間地頭的農民,除了認識苞米黃豆哪還認識像樣的社會資源?沒見識沒門路也沒錢,農村出來的孩子對父母、對自己都有著很復雜的情緒,既自卑又自負,很多都不愿聽父母的建議,況且父母也給不出什么建議。
專家分析,近10年來,中國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基尼系數已接近0.5,社會底層勞動者的收入增長嚴重滯緩,這是造成“窮二代”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體制障礙讓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流動成本提高。例如,教育是現代社會流動的最主要機制,然而,由于高校擴招后全面收費以及就業難的出現,貧困家庭子女通過教育向上流動也越來越難了。
對于農村大學生的未來,相關人士呼吁,需要更多的社會力量介入,阻止貧困的代際傳遞。
貧富懸殊折射殘酷社會機制
外來民工,為了生活,帶著淘金的心情,離鄉背井來到陌生的大城市謀生。可是,下代的教育難題卻擺在了他們面前:他們的子女,那些“貧二代”們,因為有著貧窮的民工父親,他們無法在大城市辦取戶口;他們無法讀正規的公立學校;他們受盡歧視,無法正常交友;他們居無定所,顛沛流離;他們也許要忍受饑餓,病痛難熬……
雖然中國是農業大國,農業是第一產業,可是有些農民的生活水平卻沒有得到顯著提高,他們仍然是社會中的貧困群體。在當代,仍然有很多農民的子女因沒錢不能讀書或中途退學,他們無法選擇地成為了人們口中的“貧二代”。他們在田地里日曬雨淋,把對讀書的渴望深深地埋在了心底。這些小孩,似乎被命運詛咒著,一世當農民,就世世當農民,即使他們心里有著許多的不愿意。
留守兒童是貧二代的主力軍。農村留守兒童現象的產生來自于家庭和社會兩個方面。一方面,家庭的貧困,使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走出農村到城市務工;另一方面,中國長期的城鄉二元制以及社會對農民工不公平的待遇,使廣大農民沒有辦法及能力帶著孩子一起走進城市。即使勉強帶孩子在大城市打拼,戶籍、教育等一系列問題同樣困擾著他們。
有評論員稱:“窮二代的處境,可以通過蟻族之類的生存狀態了解一二。”評論者表示,“窮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過下去、但活得相當痛苦的事。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房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產綁架了,不僅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于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并不確定,每個月的收入要精打細算才能支付,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沖的積蓄都可能沒有。
人們對財富和地位的“世襲”現象如此敏感,以至于影響了對未來的想象——“窮二代”是否應該生出“窮三代”。
近日,一名女性網友又在天涯上發帖:“已經生了窮三代的窮二代,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孩子嗎?”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此類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論更是引發議論無數。據說,她和丈夫是“因愛情而結合”的大學同學,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穩定,還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認為,生孩子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與其讓我的孩子一出生就輸在起跑線上,我倒寧愿不讓他來到這個世上。我們已經是‘窮二代’了,孩子成為‘窮三代’的可能性絕對在95%以上。”
由此可見,貧二代所面臨的殘酷生存現狀不僅影響到大學生就業,還影響到今后的結婚與育兒。因此,塑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就成為破解農村大學畢業生困境的關鍵。而這又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作為培養人才的搖籃——大學,要設置更合理的專業,更多的教育和引導,讓他們找到奮斗的方向,提高他們的綜合實力。企業在招聘的時候,也要本著公平公正的原則,不問出身,對所有大學生一視同仁。此外,國家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大學生“貧二代”的上學和就業支持,給他們提供更多、更合理的助學貸款,給他們營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提升貧困大學生的就業信心。
貧窮是最不該被繼承的
“知識改變命運”,曾經是多么響亮的一句口號。如今,這句曾經被無數人奉為真理的話語,卻引來了諸多質疑。近年來,很多大學畢業生發現,一定程度上來說,決定他們就業狀況的不再是成績、能力,而是家庭背景、社會關系。套用一句網絡語:“找工作變成了比拼父輩財富和權勢的‘拼爹’游戲”。據某媒體在北京、浙江、河南等地7所高校進行的一項調查,500名受訪者中有70%的人認為,在就業應聘中或多或少遭遇過來自家庭狀況的壓力,65%的應屆畢業生表示最擔心家庭狀況使自己在求職應聘中處于不利地位。
今年7月,北京大學公共傳播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和安平公共傳播公益基金為一個大學貧困生助學項目作影響力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助學行動已經幫助受資助學生在諸多方面發生改變,貧困的先賦影響已經在受資助學生身上得到有效地消弭,助推他們成功地進入大學,實現“鯉魚跳龍門”這一關鍵一跳。受資助學生的信心指數的提升,將會帶給學生對于學習、生活以及自己未來的強大動力。
調研的主辦方同時發布《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展信心指數》白皮書。根據該白皮書,社會發展信心指數,指通過諸多指標的綜合測量,指向受資助大學生對自身未來發展以及社會發展的信心。指數能夠揭示受資助大學生群體處于的具體生活環境和其對個人、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發展態度和信心。
調研主辦方對受資助學生的家庭情況、學業情況、心理健康、社會支持、未來發展、戀愛狀況、資助效用、愛心傳遞等諸多方面進行測量,通過系列的加權和匯總計算,得出90后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社會發展信心指數為80.4分。
根據調研,父輩的職業分化、民族差異、生源地區別、學校所在地的不同、在東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流動方式、年級的增長,都沒有在學生的社會發展信心上造成明顯分歧;甚至在經濟狀況稍好與稍差的家庭之間、在完整家庭與不完整家庭之間、在農業戶籍和非農業戶籍之間,受資助學生均表現出大致相同的對社會發展的正向判斷和積極態度。“換言之,在社會信心這個問題上,沒有哪一個子群體明顯落后”。
調研的組織者認為,一方面,社會整體的快速前行和流動機會的多樣化,在普遍意義上給了當代大學生更充分的社會信心;另一方面,對于貧困家庭大學生的社會資助,在相當程度上彌合了由于先賦因素帶來的現實生活中的鴻溝,也極大程度地、整體性地提升了受資助學生的社會發展信心水平。
該白皮書指出,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的社會信心,不僅僅是依靠單一的某個主體,而是需要社會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互聯網提供了一個連接的平臺,需要通過互聯網實現多元主體的協同合作,打破階層的固化,促進社會的流動,提升社會發展的信心。受資助貧困大學生不僅自身參與協同合作中,還可以帶動更多社會主體的參與,促進更多社會資源的傾斜。這不僅能夠提升受資助貧困大學生本身的社會信心,更能夠提升社會各個階層的社會發展信心。
“貧二代”所反映的問題似乎道出了很多普通百姓的心聲。進入新世紀第二個10年,更多80后步入而立之年。是有房有車,職場得意,還是婚姻美滿?一個“立”字,讓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面臨沉重的壓力。貧窮的繼承是可怕的,如果貧窮者缺乏改變命運的機會和機制,其危險性更加可怕。改變命運,“貧二代”既需要自身的不懈努力,也需要全社會共同的支持與攙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