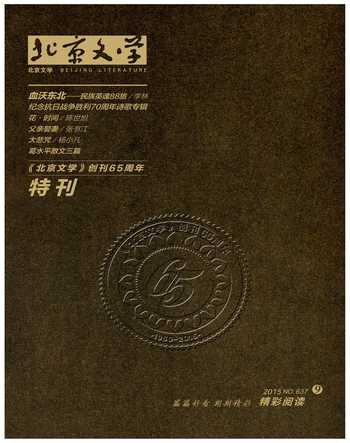葛水平散文三篇
想起四月,便想起桃花挑開的月色,一壺熱茶退隱到呼應的氣息之后,一群女子挽腰搭背吆喝著看戲去。
戲在民間,讓歷史有一種動感。大幕二幕層層開來,開,好端端的歷史開合在人間戲劇里。鄉間的風花雪月都是在舞臺上和舞臺下的,舞臺上的行事帶風,一言一行一招一式,都程式化,“上場舞刀弄槍;張口咬文嚼字”,“臺上笑臺下笑臺上臺下笑惹笑;看古人看今人看古看今人看人”。
《三堂會審》劇中蘇三受審那場戲中,潘必正問:“鴇兒買你七歲,你在院里住了幾載?”蘇三答:“老爺,院中住了九春。”劉金龍問:“七九一十六歲,可以開得懷了,頭一個開懷的是哪一個?”蘇三答:“是那王……啊郎……”蘇三那蘭花指一蹺,那些花陰月影下,照他孤零,照奴孤零,輕彈淺唱出奴給你的溫柔就全部殷出來了。那是“情”之一字貫穿古今的熱鬧啊。蘭花指,挑撥歲月的一種味道。蘭花指,纖長而優雅,舉手投足間便有了一種情緒、欲望的指向。我極喜歡那一蹺。在古代,蹺蘭花指是男人的專利,是他們顯示男子氣概的標志。如今,男子極其單調且流于僵直的手勢,怎么看都缺失了一種內斂的氣質。
戲是用來教化人的,看戲的人很會看出戲劇人物的深刻。生活中的呂不韋是大流氓,流氓的行徑都出自一個套路,偷而奸。說他是大流氓,是因為他釣得一個難得的女子,這個女子生了一個皇帝,不是一般的皇帝,是始皇帝。好像沒有后來者,有偷而奸者,沒見生出過皇帝。帝王家的史料并不能直接產生藝術感染力,它必須經過戲劇化轉換之后,才能作用于觀眾的情感,吸引觀眾的感性關注。
真或假?“以史說為內核,以戲說為外衣”,說是“戲”,可人人都相信始皇帝的爹就應該是呂不韋。我一直覺得呂不韋之后再沒見過超越他的商人。呂不韋畫像中,大多把他畫得很丑,奸詐干癟的瘦老頭兒,太卡通,有點無厘頭。人對不及的人,都會產生厭倦、妒忌,站在矛盾中,以虐待來享受那些優秀者。其實,古時選拔干部大都要相面的,做生意也一樣。戲劇中的呂不韋和始皇帝相比有極大的反差,很戲劇,反而有點傷了歷史的筋骨。
除了演繹歷史,戲劇臉譜也好看,來源于生活,也是生活的概括。生活中曬得漆黑、嚇得煞白、臊得通紅、病得焦黃的人臉,在戲劇中勾勒、放大、夸張,成了戲劇的臉譜。關羽的丹鳳眼、臥蠶眉,張飛的豹頭環眼,趙匡胤的面如重棗,媒婆嘴角那一顆超級大痦子等,夸張著我們的趣味。不管怎么說,歷史都是一張面具,帶著面具離審美才會很近。
上海有一位藝術家,因人權問題,常沒事琢磨把秦檜弄得站起來,不管緣由對否,這不是拿棍子在廣大人民的精神心理積淀層攪亂時局嗎?戲劇是啥東西?就是老不正經。
早幾年我在京看過人藝的一臺話劇《俄亥俄小姐》,是以色列重要劇作家、導演、詩人哈諾奇·列文的作品,講的是一個老乞丐,一輩子都夢想找一個高檔次的美國妓女——俄亥俄州小姐,共度浪漫良宵。70歲生日這天,他決定送給自己一件可以安慰一生的禮物,可由于囊中羞澀,他只能找一個街頭流螢舒緩一下饑渴的靈魂和肉體。戲劇就這樣不正經。一面是美好的理想,一面是崇高的理想;一面是骯臟的現實,一面是卑瑣的行徑。劇作家的本事就是在充滿矛盾和多樣性中并不憚撕開來給大家看,讓你笑,讓你哭,讓你感慨,讓你妥協。戲里演繹的看似生活,實際是夢幻的殿堂。
從前的舞臺上沒有麥克,聲音不裝飾,將自身作為人物的一部分,盡量讓音樂從人煙當中響起,對熱鬧糟亂到極致;現在不是了,變幻多端的燈光讓戲劇花里胡哨。我很迷戀戲劇里的戲文,有時候聽一段唱,不無寂寞面對著空無學兩句。在一個時間段上,我覺得只有戲劇才是人性的,看電視,我只看戲劇頻道和少兒頻道。《功夫熊貓》看了好幾遍,每琢磨熊貓有那么細小的一個爹就想笑。美國人居然如此理解了中國的戲劇化。
歷史上亂世英雄,都是來歷不明的飛賊,都是由戲劇演繹出來的。
《蘇武牧羊》里的蘇武,一身單薄的青衫,天地蒼茫間,大片的雪花飛落在他身上,他手握那根漢使節杖,那一聲:“娘啊——”會叫我難過好久。再看那演員,一切酸苦都隱藏在那副嚴峻的面孔后面,一身單薄,一身骨節,一個最有意志的人,一身塵埃,一身歲月,世間沒有一個人能從精神和信念上戰勝他。幸福是一種心境,我刻意追尋和揣度的蘇武應該是一個真實的人。有一段時間,蘇武就是我喜歡的那種男人的樣子:瘦、高、耐凍,最主要的是有一顆滿懷對君王無限忠情的種子,生長期間寧肯讓自己的世界變得狹小。歷史中有些人物天生就是來入戲的,現實中真要有那樣個人在,愛起來怕也吃力。
看戲多,且老與鄉間觀眾坐在一起,戲看進去才有味道。看戲看熱鬧,臺下的看見哪個女子水靈了,一涌一涌,涌到人家跟前,拉人家手一下,有些時候兩個人就往莊稼地去了。生活和戲劇一樣,只要能動情,合理性也是要大膽忽略的。舞臺上唱到激動處,舞臺下男人們沉重的咳嗽,婦女們尖利的噪音就小了。蘇武牧羊,貝加爾湖的北海,那一聲異族的聲音響起:“你什么時候能讓公羊生下小羊,我就放你回去。”就這句為難人的話,我就覺得蘇武就是整個漢朝的氣節。看到這里,臺子下常常是噓聲四起。
戲劇演奏樂器里我最喜歡二胡,真要能配合上演員的唱是板胡,各個劇種有各個劇種的頭把。京劇里有京胡,兩根弦,拉出來的音千嬌百媚。我無端地喜歡悲情的東西,二胡很適合對我煽情。現在戲劇樂隊里增加了許多西洋樂器,只是還沒有鋼琴。舒伯特和托賽里的小夜曲也好,但我還是喜歡二胡;德萊克曼的鋼琴曲也好,比較下來,我也還是喜歡二胡。我根本就是個山漢么!小時候,家里喂養了一頭母豬,生了小豬,不知何故不愿意喂小豬奶,我爸用他自己做的二胡在豬圈上坐著拉,狗脖子豎著,不能發出正經音調,我爸拉了一段梆子戲哭腔,那聲音灌滿了整個村莊,那段曲子拉完后,母豬主動靠墻躺下叫小豬吃奶。
人養一個定乾坤,豬養一窩拱墻根。豬是家庭中最沒出息的家畜,也懂得藝術。我認定是二胡特質的美感動了母豬。
戲劇樂器里沒有簫,有笙。漢人的簫極好聽,比箏和古琴都早。是否與劍和簡書同一時代產生?簫是竹子做的,很適合淡薄仕途的人吹奏。也有神仙眷侶的戲中有簫,也只是一段落落寡歡地吹,不和眾多樂器合奏。徐悲鴻先生畫過一幅畫《簫聲》,畫作于20世紀20年代,那幅畫很唯美,據說畫中的青年女子是他的前妻蔣碧薇。朦朧的色調下那個吹簫的蔣碧薇很閑雅,有云端的意境,猶如遙遠的天籟。簫的獨奏名曲有《妝臺思秋》《鷓鴣飛》等,但都很適合月下或空谷里孤獨吹奏。不知為什么,我一聽簫音就感到山水要起霧了,大概簫聲中有古典文化氣息吧,喜悅和哀愁都是淡淡的,有一種含蓄的內斂。簫有安詳知足的與世隔絕的大美,遼遠空闊,但我好像沒有見過在麥地或稻田里吹奏。陜西出土過一種樂器——塤。陶做的,粗糲、不勻稱,甚至有些變形,吹出來的音也很古遠。戲劇里的樂器是可以進入歲月的,凡是能入了歲月的東西都很適合生存。能存活下來的入了戲,存活不下來的,只能停留在某一個時期,顧影自憐等待入了小說中的傳奇。
舞臺是一扇窗戶,如果你是演員,你可以由此而向外觀望;如果你是觀眾,舞臺是四維空間,它是你選著觀望歷史和現實的途徑。不知為什么,我特別喜歡看《兩狼山》。《兩狼山》是楊家戲,由楊家衍生出來的戲很多。楊家的男子、女子,就連風燭殘年的佘太君最后都要向她的國家交還一把骨頭,有大國子民的氣魄。楊家戲在舞臺上用得最多的是馬鞭,馬上馬下,奔波于疆場要依靠的,是他們的坐騎——強悍的馬匹。馬是龍的近親,工業文明沒有到來之前,農耕文明推動了戰爭,良馬可以使萎靡的軍隊振作起來。
我的一位本家爺爺喜歡唱戲,也算民間把式,唱《兩狼山》里的楊繼業,唱到《蘇武廟》碰碑那場戲,臺上臺下遍地哭聲。蓋世英豪,撩起征袍遮面,一頭向李陵碑碰去!嘆壞蘇武,愧煞李陵。蒼天啊,淚雨漾漾,灑向人間都是怨!
我的本家奶奶,性子滾燙,地里做工不輸男人,摟茬割麥,打場,沒有人敢把她看作是個女子。家里也是一把好手,做黃豆醬、腌蘿卜芥菜,稍帶做醋,日常生活拿得起,還要趕會,看丈夫唱戲。有一年看丈夫唱《兩狼山》,在臺下看到丈夫碰碑而死,她托小腰,一步三晃,走上舞臺遞一罐頭瓶泡了胖大海的水給他的丈夫,臺下笑場。
人間紛擾,形形色色的誘惑比仙界多得多。白蛇變化成白娘子下凡來了,想過人間的日子,說白了,是下凡找性愛來了。《白蛇傳》是佛和俗展開的內心搏斗和尖銳的世俗交鋒。人生會有這樣的世俗情景,它需要某個人成全某件事,假如沒有法海,一本戲就泄了;假如沒有許仙左右搖擺的性情,兩個人的愛情則無戲可演。斷橋是《白蛇傳》里的重要背景,背景對于劇情有非常重要的凝神作用,極大地形成了故事的向心力,并告訴我們愛情是在雨中誕生的。一把傘是道具。下雨的時候,關于天空是什么顏色?我好像覺得就是灰蒙蒙,傘下是什么顏色?是兩個人的氣息。氣息之下呢?是一層雨水,搖曳著無數的雨渦渦。昏沉沉、冷颼颼、臟兮兮、濕漉漉,而這是塵世里才有的東西,云朵之上誰見過有雨。
戲劇就是這樣,在熟識的世界里盡量叫你感覺陌生化。
西湖最美好的季節是秋天,道路兩邊長滿了粗壯的金桂樹、銀桂樹,地上星星點點,樹上趴著一遇冷風就射尿的蟬,蟬鳴聲卻很有感覺。白蛇就出入在這里。我一直不喜歡許仙,沒有啥好喜歡的,動不動就來句:“啊呀呀,娘子救我——”倒得牙一嘴口水。
戲劇講究“無巧不成書”,一個“巧”字,就有戲看了。我喜歡去恭王府的戲園子,它暗藏著青磚瑩潤內斂的霸氣。享受在演出中,有昂貴的欲望,那是王爺和珅的府邸。嘉慶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弘歷歸天,次日嘉慶褫奪了和珅軍機大臣、九門提督兩職,抄了其家,估計全部財富約值白銀兩千萬兩,相當于清政府半年的財政收入,所以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的說法。在這樣的園子里,喝茶嗑瓜子聽戲,一時間覺得很知足,歷史的政治舞臺上自己的當下也有了幾分出息。從前,死后的鬼魂都進不了這戲園子。說實在話,去恭王府聽戲,我更喜歡享受夜晚走過那胡同的幽暗。
我在恭王府聽過一次古琴演奏,如裂帛,撕開絲綢的感覺。覺得古琴是接近古人的唯一路徑。聽音,聽的是山水、是胸襟;陶醉,醉的是寄寓、是心曲、是志趣。朋友說,古琴有點孤寂冷澀,有點不近煙火。仔細想想也是,少一些意濃姿逸,人心世情的氣溫。本來嘛,清風月白之夜,一曲《廣陵散》就是鬼交給嵇康的。竹林七賢中性情最真的一位,也是最有骨氣的一位。一進境界,則魂魄升騰。那一晚我聽了《仙翁操》《秋風辭》《關山月》,聽到最后忽想起:“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醉倒非人推”來。古時還有一種樂器叫“瑟”和“筑”。瑟無徽而有柱,是二十五弦,李商隱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現在也無法爭清楚是瑟五十弦,還是人五十壽。至于“筑”,現在也只有《荊軻刺秦王》里高漸離在易水河邊“擊筑”送行了。每一次聽琴,我都要焚香打坐,全身心進入,想那些曲子背后的戲劇故事,仿佛自己也穿越到了古時。
我不喜歡大紅的艷,比如,看誰家客廳有一幅那樣的紅梅,看到了會極其不舒服,不想停留,看戲劇舞臺上那艷俗反倒喜歡得不想動步!生動的色彩,是民間的,我賞讀它們時會心生一份雅童的眼光,覺得世俗是喜人的。戲一開場,鑼鼓家什都不安分了,金枝欲孽都搖曳在舞臺上了,讓我眼睜睜地醉下去,醉在快要被人遺忘的戲劇里,到最后遺忘了我自己,才好!
一個夏日的午后,我讀一本關于首飾的舊雜志。一篇文章說胡蘭成的女人懷孕了,找張愛玲去傾訴,那女人講到她肚子里的孩子時,臉上有哀婉之色。張愛玲打開她的箱子,取出一只金手鐲遞給那女人。愛,生活的,全都逝去了,寂寞和孤獨撲面而來。張愛玲要那女人去當了鐲子,取掉那個孩子。那個孩子的出現本就帶了一點鬼氣。鐲子如胡蘭成的市井情調,即刻煙消云散了。對胡蘭成的認識有賴于一張照片,照片上一個耗盡陽氣的男人,嘴角輪廓還算柔和,不知為什么,也許是因為張愛玲,我看他時我的嘴角略帶嘲諷。一個女人用一只金鐲子給他愛過的男人埋單,這個女人容我五花八門去想,始終會想到她的大氣。愛情本來并不復雜,來來去去不過三個字,不是“我愛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嗎?對不起。”仨字兒,動搖著這個世界建立起來的愛情。
這個社會沒有一個人敢穿一襲清朝大袍走在大街上,張愛玲敢,她有那份舉手投足間的氣度。我看張愛玲的照片,她手上戴著的手鐲不像是金子的,老照片已盡見她的雍容和嫵媚,有一段時間我老想她的氣質,那腕間戴著的該是什么材質?她的耳環長長短短,倒是都很明朗,每一張照片都可說是配得上經典。
舊雜志里我看見了宋美齡,106歲,那張素臉,那兩粒翡翠耳扣,左手腕上一圈翡翠玉鐲,右手腕上一圈翡翠玉鐲,長長的一串翡翠珠子掛在脖子上,我猜她一輩子是喜歡翡翠的。一個女人,年老時臉上已經掛不住胭脂和薄粉了,她依舊畫嘴唇涂指甲油,依舊戴環飾。一輩子顛倒眾生,迷惑人心,到老都保持著政治界貴夫人的格調。欲望對女人的誘惑沒有權力支撐時,首飾可以代替并滿足一切。
我想起了林徽因。我沒見過一張照片上林徽因手腕上有環飾,最多時候是脖子間的那一粒小巧的雞心長項鏈,黑裙白衣,她是以書卷味與才女氣質行走在民國。從個人化的詩人轉型為北京的設計師,當年她拍案大罵吳晗保護北京不力,并勇闖北京市市長彭真的辦公室,百試無功下,她痛心疾首地問天:有朝一日,悔之晚矣!這個女人,天也妒忌。我一直無法想象她戴鐲子的樣子。那么,如果她手上戴了玉鐲呢?有人說,首飾很大程度上是圍繞人的生殖區而裝飾的。假如是,那一定是吸引。
林徽因不需要,好看的人不戴什么也好看。
說真的,我很喜歡腕間有悅耳的叮當聲。有一位朋友,手腕上常戴著沉香珠子,知道他是什么珠子協會的。珠子協會里的人都喜歡收藏什么樣的珠子呢?瑪瑙?琉璃?玉石?珍珠?金子呢?水珠、淚珠、鋼珠算不算?“淚落連珠子”,我想“淚珠子”也該算一種珠寶,因為它有情感。凡是掉淚珠子的人,內心都受到了外傷的沖擊。其實,任何一種珠子都來自一次意外的傷害。比如珍珠,當海底一只海貝的身體被無意中嵌進一粒沙子的時候,為了保護沙子給身體帶來的疼痛,海貝們開始分泌一種液體包裹那粒沙子,時間的最后讓它們凝結成一粒珍珠。還比如琥珀,無端地把一只在塵埃中飛行的昆蟲膠死在里面。“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試把臨流抖擻看,琉璃珠子淚雙滴。”我當年看電影《紅河谷》,當它的主題曲響起,我一聽到那句“我的眼睛里含著你的淚水”這一句,我便也想落淚珠子。
想起來了,我有一串元青花包銀手鏈,老瓷黑褐色的斑點上有帶點錫光。我一看到它便懷想蒙古帝國控制下的漫漫絲綢之路,到達亞洲的另一端,已經是七百年前的事情了。青花瓷作為中國古瓷中最茁壯的一支,曾經為17、18世紀的歐洲人所迷戀。2009年7月我去新疆看到艾提尕爾清真寺,我突然明白了青花最初的發展壯大,卻是為了響應伊斯蘭世界的審美要求。包括后來用的“蘇麻離青”就很可能直接來自伊拉克那個至今仍然稱薩馬拉的地方。艾提尕爾清真寺外墻貼滿了青花瓷磚,一個叫香妃的女子葬在里面,聽當地的人講,棺槨里葬有她用過的首飾。
我的那串手鏈,一些時間里成為我著裝的一個“眼”,我穿什么樣的衣服,它在腕間都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婉約。
舊雜志包含的信息量很多,仔細閱讀,似乎辦刊宗旨就是為了取悅女人。依舊是說女人的配飾,下意識地,我看我胸前的三粒“蜻蜓眼”,出土的玻璃料器,也叫琉璃。琉璃被譽為中國五大名器之首(金銀、玉翠、琉璃、陶瓷、青銅),也是佛家七寶之一。到了明代已基本失傳,只在傳說與神怪小說里有記載。《西游記》中的沙僧就是因為打破一只琉璃盞而被貶下天庭。我用粗麻編了一條繩,那三粒琉璃就墜在我的胸口上。它沉積了歷史的華麗,早晨一起床洗漱完畢我掛上它,抬眼時便看到世界到處是絢麗的快樂。
和“金”比較,我喜歡“銀”,并且一定要老。喜歡老銀的色調、質地、做工的樣式,因為它傳達著一個時代更為豐富的個人氣息。有一段時間,我的手腕上會戴五六只很素的銀鐲,它的聲響不是翠響,是若即若離。我舉起手,放下,動作里我得到銀的慰藉,真的很好,它讓我愉悅。什么可以讓女人愉悅?我認為就該是首飾。手腕上的銀鐲,如早晨的樹,陽光升起來,隱約間閃亮著銀的光,那光如喜動的蜜蜂。
那一年去德國,在海德堡的老店里,我買過一只民國特色的卡扣鐲,可以開合,有簧片扣,兩端有銀鏈相系。與漆器手鐲同戴在一只手上有意想不到的特殊美感。我在海德堡還買過一只紅金手鐲,是一條蛇,兩只眼睛是紅寶石,蛇頭鑲嵌綠松石,一頭一尾是紅金雕花,身子是一種麻,我說不出到底它是麻類的哪一種植物。蛇頭下有一行英文,大意是1865年打造的,為一個女人。天光迅速流盡的冬日傍晚,它彎曲在我的手腕上,我舉著一杯紅酒,酒精在體內涌動,情緒在流淌中高漲,它從一個歐洲女人的手腕上來到中國,它誕生的那個時代,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故事?我的女友說,它的出現有可能是為了紀念他的母親。首飾天生就是為女人打造的,母親也是由愛情進化過來的名詞,終歸是和感情有關。我一直弄不懂,但我完全相信,這個世界發生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彩豐富。
我還有一只藤包銀的手鐲,上面刻有暗八仙、壽字紋、葵花、盤長、芙蓉等紋飾,分別代表著幸福、長壽、多子、吉祥、富貴。它的空白處有一行小字,上面寫了“月下美人來”,另一空白處寫了“慶爺”。都是后刻上的。我覺得這幾句話有些蹊蹺,像是一個女人在偷情。銀上的寓意已經明白,再寫就是多余。何況那兩個字“慶爺”江湖味兒又很是十足。我不管它的曾經,我戴著它,我想象我和那個“慶爺”調情,我不給他拒絕感,我只能告訴他,我是你想不到的唯一的一個例外,你已舊去,我還半新。
清代到民國時期精工打造的鎖片、項圈之類也是我頸上配飾,如果搭民族風的衣裳走出去,也會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老銀耳環中隆重的點翠和嵌寶耳墜我也有,一般不戴,我怕丟失。如果要戴,也要選面料柔軟、不帶蕾絲或網眼的衣服,以防摩擦或勾拉損壞。老首飾全是老銀匠手工一點一點打制出來的,可見古代銀匠工藝非凡。我朋友的父親年輕時是一位小銀匠,他說,在古代,好的銀匠沒有三年是出不了師的。好的首飾戴在氣質般配的女人身上會叫人眼前一亮,會讓我有惴惴不安的心跳。
舊雜志上有文章紀念屈原,詩人把屈原當作自己的祖先。多少富貴榮華,多少功成名就,多少道德文章,多少方略宏圖,一概遠去了,可是誰的生命能夠嵌入歷史呢?那些被欲望絆著腳的享樂不能,歷史把屈原抬到了文字的高處。不想那些沉重的話題了,想五月端陽是一個節日。我想起了端陽節前,生得白里透粉的女孩兒手腕間和腳腕間拴上了五彩絲線,溫婉清麗的樣子。在黃昏蒼茫的院子里蹦蹦跳跳,時間和空間在氤氳之中被分割為兩段,小女孩最幸福的年齡時段我認為是一無所知。端陽節好像是給女孩兒過的節日。各種絲線粗粗細細,袖管挽了很高,洗臉玩水都不舍得打濕了。我現在回想起來,那個年齡怎么回憶都是一團影子,只記得腕上最早的首飾是母親給的。“彩線輕纏紅玉臂,小符斜掛綠云鬟。佳人相見一千年。”是女孩兒的另一段開始。蘇軾寫這首《浣溪沙·端陽》的第二天就是端午節,他寫給他心愛的女人朝云。嶺南的舊歷五月,天氣應該是很熱了,他的女人要用蘭花香草來沐浴,然后用彩線纏臂,以期祛病除災。男人是不是每一首詩歌里都要珍藏著自己的情感秘密和生命氣息?
端陽節拴五彩絲線,有的地方叫“五彩長命縷”或“五彩續命縷”。“系出五絲命可續”,“五月五日,以五色絲系臂,名長命縷。”后人也稱“續命縷”。我小時候戴端午彩線要戴到八月十五,躲過酷夏,在一個有雨的日子,我母親幫我剪下扔進河里。母親說,五彩絲線可以避邪和防止酷夏五毒近身。我還記得剪下絲線時,我和母親站在河邊,母親口里念念有詞:“叫河刮走吧,刮走近我閨女的邪門歪道。”我看著那舊了的絲線漂在水面上,一個小波浪、一個小波浪翻滾著遠去了。河流帶走了許多,我一直希望,守著一條河流,過世界上最美的日子。我知道我已不能,每個人都無法逃脫命運的悲劇。
說到悲劇,這本舊雜志上也寫到了“杜十娘”,女人一生的財富是她全部心身換得的首飾,她想戴著她的首飾離開那個淫言穢行的下流之地,去尋求清潔雅淡的風流。她不知,世間的“風流”原本都是露水恩情。她只能感嘆:“妾腹內有玉,恨郎眼內無珠。”翠羽明珰,瑤簪寶珥,祖母綠、貓兒眼,值錢么?要我看最值錢的是睜著眼看世間百態。我認為,女人自己買首飾,某種程度可以助長女性的獨立意識和歡喜,男人送女人首飾只能說一時之間可以擴大感情的衍生空間。
有一年去棗莊,去時已是冬天。去看“李宗仁史料館”。經營史料館的女人已經逝了,是李宗仁最后一位太太,影星蝴蝶的女兒,叫胡友松。她活著時說:“一生有著太多的迷茫,胸中有著萬千溝壑。”影星蝴蝶告訴她:“記住,你只有母親,沒有父親。”她是蝴蝶和人偷歡而來的。她和李宗仁的婚姻只有兩年半。不知道她是否也一樣擁有母親“蝴蝶”的花容月貌?我問那個講解員,那女孩看著我半天想不出來該如何回答。走到樓上的陽臺前,她突然回轉身說:“她手上一直戴著一個綠色的塑料鐲子,因為她的首飾都捐獻給了桂林李宗仁官邸,就那個塑料鐲子,沒有人看得出它的賤來,六十多歲的她戴著,襯托得她貴氣逼人。”
我想到了女人手上的指環。在古代,戒指是用來區別和記載宮廷女子被皇帝“御幸”的標志。女人“進御君王”時,都要經過女史登記,女史事先向每位宮女發放金指環、銀指環各一枚。如果某一宮女左手著銀指環時,表示已安排將要與皇帝同歡,而右手著銀指環時,表示已與皇帝同歡完畢。如果右手著金指環時,表示正當月事、懷孕之時,應該暫避君王御幸,女史見了就不將其列入名字,起到“禁戒”作用。項鏈和手鐲就不用多說了,最早則起源于原始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轉變時期所發生的搶婚。在從夫居的制度下,男子往往掠奪其他部落的婦女或在戰爭中俘獲的女子作為妻子。為防止被搶婦女趁戰亂或夜間逃走,勝利者往往用一根繩索或樹環套住女性的脖子或雙手,企圖使她們馴服。后來逐漸演變成用金屬套住脖子或手。耳環也是馴服女性的“刑具”之一。女人們啊,一路風雨而來,因禍得寵了。生命不可以返回初衷,到后來卻點綴得女人風情萬種。
看好萊塢大片,會發現好萊塢從來都是混跡著世界上最有型的帥哥,這些人的舉手投足,包括他們的各種行頭通過鏡頭傳遞到世界各地,手環、耳環、項鏈,就是潮流和魅力的標桿。再配上獨具個性的發型,一副酷勁十足的眼鏡,若隱若現著內斂奢華的袖扣,抑或是標準的六塊腹肌……這些面子功課無非是“耍帥裝酷”打造出一個酷型男。只是任何的修飾都不如一款有分量的手表和首飾來得畫龍點睛、切中要害。看強尼·戴普,他可以算是手鐲的忠誠粉絲,嬉皮的、西部的、搞怪的……你可以在他手腕上看見各種稀奇古怪又個性十足的手鐲、手鏈。想想看,一個魅力十足的男人,必須是一個懂得在合適的場合借助恰當的配飾表達自我的男人。男人的首飾對接了男人的氣質,有時候就是女人的毒藥。
雜志的封底是一張老照片,舊的月份牌上穿旗袍的女子,旁邊放著一包香煙。和中國的香煙比,我更喜歡西方的雪茄。其實雪茄之于男人,正如首飾之于女人,雖然男人表現魅力不在于膚淺的形式,而在于品位和生活態度。可我總認為雪茄在男人身上的表現,可以讓生性浮躁的心有收山之勢。作家里邊陳忠實抽雪茄。抽抽停停,說說話話。似乎李敬澤也抽,記憶不起來。對陳忠實想起來較多,主要是因為那張臉,溝壑縱橫,似乎是灞河水的波紋深嵌到了臉上,他那張臉很適合畫油畫。想他頭頂撲打臉的塵土,一路走來,在一片金黃色的麥地前圪蹴著,嘴里一根長長的旱煙袋,溫暖、結實、安泰。可他偏偏抽雪茄。雪茄與他的《白鹿原》的關系,實在容不得我們在閱讀中太過傲慢。我和他聊天,雪茄的香氣總是在談話的背景中繚繞,很好聞,有一種促使話談下去的潛移默化功用。仔細想來那種范兒,不是人人都能抽雪茄的。
真正西方現實生活中,能代言雪茄的大佬恐怕只有一人,那便是英國首相丘吉爾。歷史風云人物,都有自己的嗜好。幾乎所有的歷史圖片中他都是抽著雪茄的,因此雪茄被認為是他的標志性符號。據說,丘吉爾一生中吸過的雪茄的總長度為46公里,吸食雪茄總重量為3000公斤,是世界上吸食雪茄吉尼斯紀錄的保持者。一個首相抽雪茄抽出了自己的牌子,為前衛的世界帶來了豐富的人文意義。這些都還是其次了,我欣賞二戰期間丘吉爾和一個記者的對話,記者問:“莎士比亞與印度哪個更重要?”邱吉爾回答:“寧可失去50個印度,也不能失去一個莎士比亞。” 他之后再沒有一個領導知道:能夠征服世界,主宰世界,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擁有文化的精神力量。
“郎騎竹馬來,繞床弄青梅。”如今郎騎竹馬漸漸遠,遠的過程就是一切。懷舊,是人的通病,也是人的不正經,這些年很盛。說白了,不正經,是刻意營造一個自由寬松的環境,去想象歷史,調侃生活。當下中國傳統秩序嚴重退化成“一本正經”,從一個層面上展示了民間情懷的瓦解,另一個層面上又和政治銜接得緊張;再一個是懷舊風泛濫時,很多時候人會變得“醉生夢死,百無聊賴”。其實,“一本正經”和“不正經”就差那么一丁點兒。前者,毫無人味,有生活崇高志向作怪;后者,有人性解放,看淡衣食苦而風情不減。前者,把天下早已經整明白了的道理拿起當思想說;后者,則是把社會和那個常和社會打交道的神經,從崩潰的邊緣拉回來的東西。
不正經,林林總總,俯拾即是閑言話語,和文人的情懷有關。文人堅守的領域,一直有一層神秘的面紗。在他們文字的不同敘述中似乎仍然是中國最后的精神和道德堡壘,仍然懷有和民眾不同生活信念或道德要求,仍然生活在幻影和惡作劇當中。在社會中敘述故事,卻不是故事中心,蠢蠢欲動又方向不明的社會里,文人的性子不能夠盡情張揚,在社會的消費欲望中開辟發展新的領地,這個領地里的文人越發拿不正經當情趣了。
古時民間飲食是有規矩的,兩宋之后百姓才有了一日三餐制。在此之前,按禮儀天子一日四餐,諸侯一日三餐,平民兩餐。西漢時,給叛變被流放的淮南王的圣旨上,就專門點出,“減一日三餐為兩餐”。普通平民日常飲食能從兩餐到三餐最欣喜的是文人。
把飲食描寫融入吟詠的詩詞文賦中,蘇軾的不正經決定了他的情趣。他寫有《東坡羹頌》《豬肉頌》《老饕賦》《試院煎茶》《和蔣夔寄茶》等。飯飽生余閑,見人家婦人賣餅利少,心血來潮幫賣餅婦人寫下了廣告詩: “纖手搓來玉色勻,碧油煎出嫩黃深。 夜來春睡知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
“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那個時代的蘇東坡,有失意的處境,沒有失意的人生。有一盤菜叫“東坡肉”,既是居士又吃肉,可說是人生修養的一個范例。“黃州好豬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它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不正經的貪吃改變了他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歷史才讓他長久活在了當下。
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被前人稱作以孤篇壓倒全唐。那一句“誰家今夜扁舟子,何處相思明月樓?”真叫把風月推向了四級之高。聞一多曾給這首詩極高的評價:“在這種詩面前,一切的贊嘆是饒舌,幾乎是褻瀆。”又說:“這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從這邊回頭一望,連劉希夷都是過程了,不用說盧照鄰和他的配角駱賓王,更是過程的過程。”聞一多1925年留學歸國。走下海輪的剎那,他難以抑制心頭的興奮,把西服和領帶扔進江中,看著它們漂向西方,他的中國身子急切地撲向祖國懷抱。
我見過出土的陶俑唐代侍女,乍一看就很溫暖,暑氣撩人的樣子。元稹詩句“藕絲衫子藕絲裙”,歐陽炯詩句“紅袖女郎相引去”,能看出唐代文人喜女子紅裝,喜媚俗。清風日朗,寫虢國夫人身著描有金花的紅裙,裙下露出繡鞋上面的紅色絢履,走在長安郊外曬富,倦意來了,幾個肥肥的女子,停留在日頭曬不到的涼亭下飲酒,一幅揮汗而就的奇異畫面,酒喝到火候,哥哥妹妹魚水情深的樣子。盛唐的音樂文化在與各民族的音樂文化融合后,發展興盛到了歷史頂峰。如是說文人不正經那份開放,不如說不正經那口酒和女子胸口前的大朵牡丹。
歷史上不正經的文人被女人懷念的文人多了,比如北宋詞人柳永,是一個具有藝術家氣質的詞人,他風流、落拓而又飽富才情。只是他那個時代,入仕是所有文人追求的核心目標,也是文人唯一的出路,因此藝術才能也要為之服務。那些在文壇執牛耳的領袖都能將兩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所以柳永雖有令人敬佩的才華,也只是用于花街柳巷。柳永最后家無余財,死后被一群妓女送葬,如果不是那活著時不正經的深廣情懷,怎么能在歷史上獨成風景?
喜歡看文人不正經的書屋。文人的書屋安適獨立,于世間紛亂爭逐之外,不一定大,有書足可以裹卷文人的氣場。
豐子愷先生在他的“緣緣堂”里寫作、畫畫,多少打擊和創傷能傷及他那顆善良的心?他的心一定具備了自給自足的本領,不然他不會給自己起名字叫“緣緣堂”。他不露聲色地點化著凡塵俗世中心亂意迷的人們,他是可以在亂世中獲得文化定力的那種。看看先生的漫畫便知先生有多么不正經。他讓一個孩子嘗試雪花膏、牙膏的味道,他就想告訴世人,不為執著還為灑脫,人就這樣一天天在無知、有知中把自己堆疊成了歷史。
文人在歷史上一直處于寂寞之中。又不甘寂寞,努力地在社會空間尋找自身的位置和確立話語權,尋找容身之地。文人率直,有一種莽撞地介入現實的力量,文人的不正經應該算是社會角落里的一朵奇葩。
現實生活并不是一般意義的一本正經,適用性太強的俗世,很容易激發人的功利體系,太正經的文人在此間活著,既不能真正的精神獨立,又不能真正的空間獨立,有幾個字支著,很容易“看不慣一切”,很容易營造出一個“偏靜”之境。中國文字在當代中國實用性中一直處于衰變過程,自己的書屋取一個什么樣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點不正經。文人活在精神田園里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你看他那“桃花源”似的生活,千百年來,無論平民百姓還是王胄貴族,都在聲色犬馬的天地間念叨這種生活。現代社會,農民都不能夠守節,真要讓文人過這樣的生活,恐怕文人不比農民強。
見過許多書屋的叫法,“人境廬”“雙忘齋”等,無非是“堂”“齋”“軒”,所有的出現形態大都是從古文人的文章間獲得啟悟。什么樣的名字能有豐子愷的“緣緣堂”好呢?什么樣的名字能有魯迅的“三味書屋”好呢?什么樣的名字能有郁達夫的“風雨茅廬”好呢?
歲月粗糙如煤渣,又粗糙了多少情懷?“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到最后變成在淚眼中爭吵度日的夫妻,寂寞一旦被世俗化,郁達夫也只好不正經地拿起筆,飽浸濃墨,在那衣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而已。
不知為什么,我一直不喜歡文人的山水畫,偏重人物。再好的山水,也明知人家是在取法宋人元人,也具備了雄渾沉穩一格,可我偏就不喜歡。可能是住在太行山上,看多了自然山水的緣故,看那雨淋山崖皺的樣子,一看就是為畫畫走進山中的,少了縱酒放筆,任氣使才的性情。喜歡看文人的人物畫,喜歡那一臉的人事之渺小,天地之唯我的樣子,很耐琢磨。
文人不正經是俗世的窗口,有呼吸,有體溫,有古今。看看當下的社會鬧騰得多有陣勢,閑余看看文人不正經的文字,文人說:看看吧,看看吧,陽世哪里有鬼,鬼都在人心里,藏著呢。
文人里的字畫最難求的,大家認為是賈平凹,其實是錯誤的認為。平凹老師的字很好求,只要你和他不正經。那一年去四川郎酒集團開筆會,酒桌上我說:“平凹老師,外界對你評價不好呀,都說你小家子氣。”他說:“我哪里小家子氣了?”我說:“比如想求你字……”他沒等我把話講完,急忙說:“你把你的地址給我,我回去就寫好寄給你。”果然,半月后收到十個大字:“鳳棲常近日,鶴夢不離云。”和一個人正經,怎么可以求得到他的字呢?
文人喜竹子的人不少,由喜而畫。畫竹可以寫實,可以寫心,來得快,有文人難得的高雅在紙上。我一見難得的高雅就想到了難得的流俗。能畫好竹子的人是有畫者骨格在里面,竹影疏朗,看似畫得自在,卻能看出筆頭生拙老辣,意態清新俊逸來。風流才子唐伯虎曾在一扇面上畫了竹子,鋪紙沾毫,他的畫如何?倒是《畫竹詩》:“一林寒竹護山家,秋夜來聽雨似麻。嘈雜欲疑蠶上葉,蕭疏更比蟹爬沙。”可說是“流俗”得太不正經了。王維有“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之句,與《黃岡新建小竹樓記》有一比,王維是唐時難得高雅的詩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說竹子是好東西,也有罵的,“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人是個怪物,多少好詩句我沒有記住,偏偏這尖酸、不正經,反倒鮮活在我心里。
古今能說出“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只有東坡一人。“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只為了確證一件事——不可一日眼中無竹。可知他的另一面的不正經呢,“十八新娘八十郎,蒼蒼白發對紅妝。鴛鴦被里成雙夜,一樹梨花壓海棠。”一個“壓”字,道盡無數未說之語!
我的書房里掛過一幅字,不是名家寫的,很普通的一位友人應我要求寫下。八個字:“真水無香,假山有妖。”我喜歡這八個字。如今人到中年,覺得越老越難正經,倒不是想“玩世不恭”,實在是對自己很難正經。我不是名人,但知道名聲卓著的人都有點兒不正經。看盧梭、托爾斯泰、雨果,包括我們的魯迅。周先生給許廣平寫信是這樣的:“廣平兄,我是你的小白象呀!”那年他44歲,長得又老又黑又瘦。
幾年前在京看電影《東邪西毒》,東邪帶著一壇新酒,從綠色遍染的東邊,到風沙干烈的西域,送給那里的西毒。一壇酒,一世人,就只為了一個女人——桃花。桃花是以此試探西毒的真心,東邪是為借此一睹桃花的芳容,西毒是為了從此得到桃花的消息。一年一次,壇底見空。極喜歡王家衛那句把心掏走的臺詞:“今年因為五黃臨太歲,周圍都有旱災,有旱災的地方一定有麻煩,有麻煩,那我就有生意。我叫歐陽鋒,我的職業就是幫助別人解除煩惱的。”王家衛的電影有一種文人在美學上,甚至空間關系、人際關系上自己的解釋,有些不正經的強調詩情畫意。
我喜歡莊子說過的一句話:“天地豈私貧我哉?”但,這句話一時沒有想出來叫哪個不正經的文人來寫。
責任編輯 王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