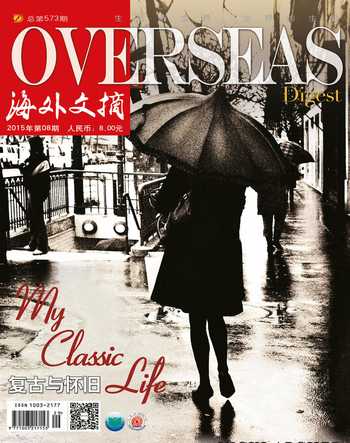漫漫通勤路
斯蒂凡·施密茨、芭芭拉·奧皮茨

英國研究者將上班族派往通勤途中,觀察其身體數據,結果發現他們的心臟每分鐘跳動次數高達145下,有些人陷入輕微的恍惚狀態,體內出現一股壓力荷爾蒙流。同時他們還測量了戰斗機飛行員在執行任務時的數值,結果令人吃驚:通勤途中的上班族承受的壓力比坐在駕駛艙中的飛行員還要大。永恒的等待,喜歡罷工的列車司機,永不停工的建筑工地,都讓他們對漫漫通勤路感到絕望。
通勤意味著壓力,可能危害婚姻,毀滅健康和生活樂趣,但每個人對此的感受都不盡相同。工業采購員克勞迪婭·克萊恩為上班路途感到筋疲力盡,而來自北德無子女的遠程通勤族帕特里克·舒爾茨-亨茨爾卻在汽車中感受到安靜和自由。每個通勤族都在尋找更聰明的通勤解決方案:例如犧牲賺錢和升職的可能性,以獲得更有價值的東西——更近的距離、更加健康的氣色和孩子們的笑容。

通勤影響伴侶關系?
在德國,每天有2000萬人開車去上班,約300萬人擠火車和地鐵上班,約150萬人坐公交上班。600萬人的上下班路途單程超過25公里,約1000萬人的通勤單程距離在10-25公里之間。
以前,克勞迪婭·克萊恩每天的通勤距離就是50公里。早上6點她端著一杯咖啡坐進汽車,希望能避免趕上大堵車。“但是可能6點半就堵上了。”她聽著瑞典Mando Diao樂團的音樂,盡可能放大聲音。她說:“你必須讓自己盡可能保持舒服。”
但是壓力仍然一天天增大。冬天,克萊恩有時需要開車3小時才能到達公司。“當你開車回到家時,感覺自己如同一灘爛泥。”她的丈夫帕特里克也通勤,兩人一不留神就會因沮喪而開始吵個不停。“如果你帶著怨氣從高速公路歸來,的確需要一個拳擊梨形球來發泄一下。”她回憶說。終于有一天,一切都崩塌了:克萊恩的父親生病,上司更換,休假被取消。28歲時她想生個孩子,到了30出頭卻仍未實現。當時她說:“這樣我們永遠也建不起一個家庭。”今天,克萊恩在房子后的花園里剪得很短的草地上搭起了一個攀援架,這是為她4歲的小兒子準備的。她笑著說:“我現在是家庭主婦和母親,我很喜歡這種生活。”
漢堡大學社會科學學者斯特凡妮·科雷著手進行的一項研究的主題就是:通勤會危害到伴侶關系嗎?她的結論是: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當妻子或女友通勤時,離婚或分手的風險就會升高。因為她們身上常常擔負著大部分家務壓力,當她們不僅要去上班,還要每天都在路上度過兩小時甚至更久時,雙方關系就會變得非常危險。
“尤其是那些夫妻雙方都做著緊張、忙碌工作的家庭更容易陷入壓力之中。”德國聯邦人口研究所的托馬斯·斯科拉說。有兩年時間,43歲的醫生菲利普·恩澤爾曼從伍珀塔爾去魯爾區黑爾訥上班,因為那里的升職可能性和高工資都很吸引人。現在他坐在伍珀塔爾的一家咖啡館中,他的住所就在不遠處。“現在是4點半,我下班了。”他說。如今他只需要步行10分鐘就能到家。他的妻子也是醫生,也曾在黑爾訥工作。他們本想盡快賺到足夠的錢建一棟房子。女兒科雷奧出生時,他們交替著休育兒假。當他從診所回家時,總是會先給妻子打個電話。然而經常發生的是,45分鐘后他的電話響起,妻子問他在哪里——毫無疑問,他還處于堵車長蛇中。有時候妻子也會把電話給女兒,話筒里傳來女兒稚嫩的聲音:“爸爸,你在哪里?”他一再詢問自己:“如果生活在里面的人不快樂,要著房子有何意義呢?”終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遞交了辭呈,接受了伍珀塔爾的職位。如今他賺的錢少了很多,但是能為孩子、妻子和生活留出更多時間。
在《明星》雜志進行的一次調查中,約三分之一受訪的通勤族宣稱他們會關注住所附近的工作機會,只有14%想著搬家去工作地點附近居住,避免將如此長的時間耗費在路上。
法比安·斯圖克拉特就是他們中的一個。長期以來他都從北威州的山城地區到科隆上班,通勤方式是乘坐公交車和列車,他要將家里的小車留給老婆。“走出空曠的火車站,我得大半夜在空無一人的城市街道上走20分鐘。”最初他還可以忍受,但是漸漸他發現“每天缺少的這些時間累積起來,會造成毀滅性的后果”。他常常在兒子卡斯帕上床睡覺后才能到家,無法控制和老婆吵架。“我倆會因為一些瑣碎小事很快就大發雷霆。”現在這家人生活在科隆,盡管這里房租貴得嚇人,而且雙方母親都住在山城地區的伍珀塔爾。
公司可減少通勤族壓力
在單親家庭中,通勤往往會帶來更多麻煩。實際上必須建議單親父母不去路途遙遠的地方上班,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能夠選擇如何生活。在城市中,尤其是在慕尼黑這樣的大城市中,生活成本十分高昂,而農村的工作機會很少。斯科拉表示,對很多人來說,通勤與其說是自由意志的表達,不如說是生存問題。“三分之一的通勤族都是被迫的。”
“我不能細想這些事情,否則會變得很沮喪。”一個在施塔恩貝格生活、在慕尼黑工作的年輕人事經理說。她是一對11歲雙胞胎的母親,早上開車20分鐘去火車站,然后坐城鐵進城,繼續坐地鐵,再走一段,才能到達辦公室。她不能只做兼職,因為她需要錢。回到家后,她常常在脫下外套之前就要開始做飯。昨天她回得有點晚,兩個孩子顯然生氣了,沉默地繃著臉鬧別扭,讓他們疲倦的母親為難。“我有時候真的覺得自己很失敗。”她說。
這位人事經理和她的雇主協商,她一周有兩天可以在家工作。老總們要接受這種模式,就必須放棄讓他們的員工圍著他們團團轉的思想。對很多人來說,這很困難,盡管在因特網時代,坐班實際上常常并不必要。奇怪的是,比起90年代中期,如今在家工作的人更少。2008年仍有80萬人在家完成工作,如今只有約60萬人大部分時間在家工作,200多萬人有時在家工作。在國際上,德國的名次處于匈牙利和波蘭之間,遠遠落后于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英國。
公司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來大大減小通勤者的壓力。例如不在早上組織每個人都要按時到場的會議。德國心理學家斯特芬·哈夫納在薩克森州巴德埃爾斯特鎮開辦了一家綜合醫療診所,他自己也是周末通勤族。早上他診所的上班時間是流動性的。“我們的雇員中,有很多早上先送孩子去小學或幼兒園、再來上班的母親,”他說,“我們這里不開晨會。員工們得知道,通勤壓力并不是必然存在的。”
利用通勤時間的軟件
機械制造工程師托爾斯騰·路姆佩爾在環繞斯圖加特城的城鐵和公交上耗費了很多時間,直到他意識到:不能繼續這樣下去了。如今他早上在家打包好襯衣、褲子、內衣和襪子,放進一個防水背包中,騎著自行車穿過山坡葡萄園,走小路進入工廠,然后沖個澡。最初他需要的時間比坐車多,現在已經基本持平了,而且晚上到家時他也會更加舒服、清醒。周末他無需再專門出去進行體育鍛煉,而是可以和家人一起做點什么,因為借助通勤途中的鍛煉,他已經足夠健康了。
這也許是最有希望的解決方式:既然通勤是必須的,那就好好利用這段時間。根據一項研究,有54%的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中用智能手機上網,主要是利用交流軟件瀏覽社交網絡。顯然人們渴望在去公司的途中進行社會交流。而在小車中,大部分人不僅無法上網,往往還是獨自一人。
德國軟件公司SAP的員工大衛·索梅爾在早上的堵車途中發現了這一點。他和一位同事合作開發出一種軟件,可以幫助通勤族找到一起上下班的伙伴。“這個系統可以辨識出,注冊用戶中誰可以一起上路,接著通知他,并馬上向司機展示同伴的路線。”索梅爾說。這款軟件并未減少通勤時間,但是改變了通勤內容,汽車中的無聊時間變得如此有趣而充滿交流的可能性,至少對于所有早上7點就已經準備好和來自市場營銷領域的天才或是銷售精英一起聊天的人來說是這樣。在該軟件的幫助下,SAP員工丹尼爾·施密德在短短3個月內就結識了50位新同事。
同時,這個小程序也已被和SAP無關的公司、醫院、大學和管理部門投入使用。例如化工巨頭巴斯夫公司位于路德維希港的總部。自2012年起,那里有了一條新的公司協議:員工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和上級商定好后就可在家工作。“巴斯夫想為員工提供便捷,以爭奪專業人才。”巴斯夫德國的人力資源經理漢斯·奧貝爾舒爾特說。至少一些公司已經認識到必須在這方面多做點什么。自今年初起,寶馬公司的工作小組可自行決定,在何時何處完成辦公室日常工作。“領導和員工一起確定游戲規則。”寶馬人事經理尤爾根·利普說。
這樣,工作和生活地點之間的遠距離就不再會導致長久的沮喪和效率下降。卡拉迪亞·克萊恩、法比安·斯圖克拉特和菲利普·恩澤爾曼等認為,孩子和親情比職場成就更為重要。但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通勤的壓力是可以忍受的。對一家漢堡航運公司計算機部門的經理帕特里克·舒爾茨-亨茨爾來說,住在一棟老房子里,幼兒園時期的朋友就住在附近,狗、馬隨處可見,這樣的生活根本不可能在大城市實現。凌晨很早他就坐進他的黑色Dacia Duster汽車中,手里拿著半升咖啡,先聽聽新聞,再聽聽播客。“我幾乎感受不到路途的漫長。”他說。每天在高速公路上度過約3個小時當然不容易,為此他放棄了手球運動,因為他空閑時間太少,而且精力有限。盡管如此,他仍然說:“我感覺自己很健康。”
大都市的高額生活開支常常讓人難以承受。下面是一些人的日常通勤生活。
巴西里約熱內盧,戴安娜·蘇扎,26歲。
蘇扎每天從家所在的Colubande郊區到里約富裕的城區Ipanema上班,全程40公里,約2個半小時,需先后乘坐小巴士、渡輪、地鐵和市內公交車等交通工具。這位單親媽媽在一家旅館接待處工作,每月能掙350歐元,通勤費為120歐元。“我沒有其他選擇。”蘇扎說。里約的房租令她望而生畏。在有著1250萬居民的里約都市圈內,沒有一天不堵車。蘇扎在路上睡覺,晚上8點回到家中。孩子們11點上床睡覺后,她開始洗衣服,然后去一家酒館工作。
倫敦,尼克·摩爾比,45歲。
摩爾比的一天開始于清晨5點45分。他在倫敦工作,住在英格蘭肯特郡的皇家唐橋井鎮。他乘坐列車上班,單程一個小時,而且已經這樣上下班22年了,可謂“遠距離通勤專家”。摩爾比當然也考慮過搬到城里去,但是后來他認識了現在的妻子,生了兩個兒子。肯特郡的學校很好,生活開支也在可承受范圍內。摩爾比在車上閱讀或打盹兒,甚至注意不到列車晚點或是停下來不走了。作為通勤專家,他知道生氣無濟于事。
紐約,阿克塞爾·馬爾滕斯,42歲。
兩年半以來,這位計算機科學家在曼哈頓上班。他和妻子、兒子一起生活在40公里開外的白原市。他先乘坐火車來到中央車站,據時刻表需要32分鐘,實際上卻需要45分鐘。很多女人利用路上的時間化妝,男人們則任憑領帶松松垮垮地掛在脖子上。到達市內后,他再換乘地鐵。很少有人開車上班,因為停車場收費昂貴,每小時至少20美元。最近他工作的辦公樓開始出售車位,標價為每個100萬美元。
[編譯自德國《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