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身邊的“布魯圖斯”
麥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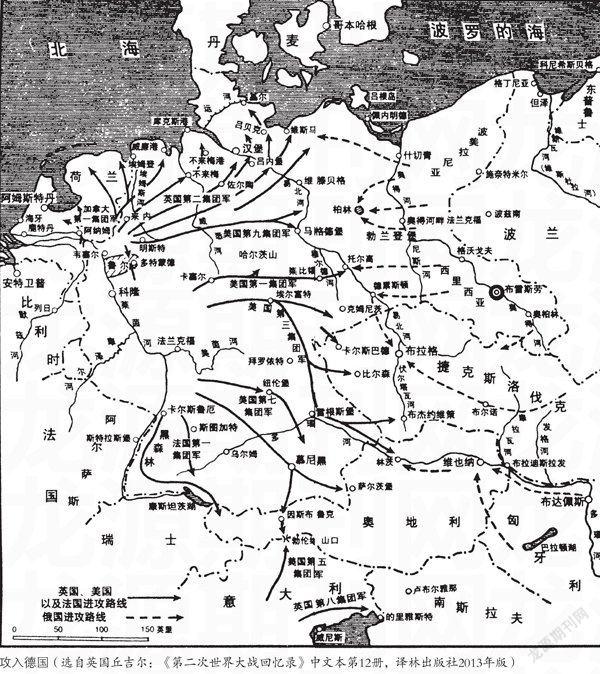
阿爾貝特·施佩爾(1905-1981)在希特勒上臺前還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無名建筑師。1933年秋,他在參與柏林舊帝國首相府的整修和布置期間被希特勒看中,很快便被接納為希特勒私交圈內(nèi)的一員。1937年,他被委以“德國首都建筑總監(jiān)”頭銜;1942年,又爬上了軍備和戰(zhàn)時生產(chǎn)部部長的高座;在納粹政權(quán)中曾一度是僅次于希特勒的第二號人物。他同當時大多數(shù)的技術(shù)治國論者一樣,“曾經(jīng)長久地生活在謀殺者之中而毫無感覺”。作為現(xiàn)代工業(yè)第一流的組織者及效率專家,他將德國軍備生產(chǎn)從1941年的平均指數(shù)98增加到1944年7月的322這個最高點。希特勒的戰(zhàn)爭機器在那些個災難年月中之所以能達到令人驚恐的高速運轉(zhuǎn),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這位“天才的建筑師”。
不過,施佩爾畢竟不同于那些死心塌地的納粹黨徒:在他身上還殘留著早年德國理想主義青年運動所獨有的氣質(zhì)與色彩,雖說他晚出生十年而未能趕上。他不幸像浮士德與魔鬼梅靡斯特訂立契約一樣去依附希特勒,是以為這個人可以為他充分提供施展才干與抱負的舞臺,并帶領(lǐng)他們?nèi)昝摲矤栙惡图s的羈絆,進而推動德國的復興和強盛。然而,當這個人在不斷玩弄、蹂躪了千百萬人的感情之后,還準備不顧一切地摧毀德意志民族的生存基礎(chǔ)時,施佩爾似乎才如夢初醒。建筑師的職業(yè)本能及蘊蓄深沉的愛國情愫使他鋌而走險,迅速作出了類似施道芬堡上校那樣的決定;盡管希特勒的“知遇之恩”使他缺乏直面手刃的勇氣。
1945年2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施佩爾只身驅(qū)車前往寒冷而凄涼的柏林威廉廣場,視察了希特勒藏身的總理府暗堡的整個通風系統(tǒng)。他計劃利用希特勒晚間的定時聚會,往通風口輸入毒氣,消滅暗堡主人及其三位死黨:馬丁·鮑曼、約瑟夫·戈培爾及羅伯特·萊伊。他對摯友、他的彈藥司司長迪特爾·施塔爾說:“這是結(jié)束戰(zhàn)爭的唯一出路。”他打算使用的毒氣叫“塔布恩”,是一種十分厲害的神經(jīng)毒瓦斯新產(chǎn)品——即便在露天中灑上幾滴也能毒死一個排。后來,由于預見到可能出現(xiàn)的某些技術(shù)障礙,他又擬另用一種叫芥子氣的常規(guī)毒氣——1918年10月13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索姆河戰(zhàn)場,當時的希特勒下士就曾中過這種毒氣造成雙目暫時失明。但是,在施塔爾提供給施佩爾的芥子氣還未運抵時,希特勒已命令警衛(wèi)隊在通風口安裝了一支大約十英尺高的金屬煙囪,并讓它牢牢控制在武裝人員操縱著的數(shù)臺探照燈的強烈光柱下。當施佩爾3月初發(fā)覺時,驚得簡直瞠目結(jié)舌。下毒的通道被有力地扼住了,他以為自己已被發(fā)現(xiàn)。然而在以后的數(shù)月中竟什么事也未發(fā)生。原來這是希特勒作為預防毒氣而下令采取的一項正常措施。乖戾古怪的希特勒憑借奇異的第六感官,曾鬼使神差地多次躲過地下抵抗運動精心策劃的暗殺;他十分樂道的“神意”這次又讓他避開了施佩爾已繃在弦上的死亡的箭矢。
暗殺失敗后,施佩爾便集中全副精力加緊他在此之前的活動——近乎公開地破壞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早在德軍從蘇聯(lián)、法國以及德國西部前線地區(qū)撤退之際,希特勒就曾陸續(xù)下令執(zhí)行此政策。1944年9月7日,納粹黨的《人民觀察家報》根據(jù)希特勒口授,將這種汪達爾式(按:汪達爾式或汪達爾主義的內(nèi)涵是對物質(zhì)、文化的極具毀滅性的破壞。汪達爾人是古羅馬時生活在北歐的游牧民族——日爾曼民族之一,羅馬人視之為“蠻族”)的大破壞概括成:“不讓敵人吃到一粒德國小麥,沒有一個德國人會向敵人提供情報,沒有一個德國人會幫助敵人。敵人會發(fā)現(xiàn)每座橋梁都破壞了,每條道路被封鎖了——迎接他的唯有死亡、毀滅和仇恨。”
希特勒的命令加深了他自己與施佩爾及其他稍具理智的德軍軍官們自斯大林格勒之役敗北以來就日漸顯露的裂痕。希特勒并非沒有覺察到這種裂痕。1944年3—5月間,他曾向他的副官尼·馮·貝洛透露:雖然施佩爾對勝利缺乏信心,但是唯有他才能駕馭錯綜復雜的軍火部門。因此他不準備追究他對戰(zhàn)爭所持的懷疑態(tài)度。施佩爾當然深諳此理,才敢于有恃無恐地對抗希特勒。不過這畢竟不是一件兒戲。1945年3月10日,他在貝爾瑙召集他的工業(yè)界的同事們開會,向他們表示了甘愿丟性命去保護工業(yè)設施的決心。3月15日,施佩爾起草了他向希特勒的最后一份工作報告。在這份長達22頁的文件中,他極為坦率地認為德國經(jīng)濟行將徹底崩潰,戰(zhàn)爭實無繼續(xù)進行的必要。他直斥希特勒說;“任何人都無權(quán)持這種觀點,即德國人民的命運系于他個人的命運。”“我們無權(quán)在戰(zhàn)爭的這個階段上,由我們采取針對人民生存的破壞措施。”他第一次不加掩飾地宣稱:“即使無望再收復,也必須保留民族的生存基礎(chǔ)。”3月18日,德國國防軍公報公布了四名軍官因未及時炸毀雷馬根附近的萊茵河橋而被處死的消息。當晚,希特勒正式頒布撤退萊茵河以西800萬德國人的野蠻命令。翌日凌晨,施佩爾在柏林暗堡向希特勒面交了他15日起草的這份反對焦土政策的備忘錄。希特勒并未震怒,他緩慢卻是執(zhí)拗地回答他的這位“藝術(shù)家同僚”的指責:“如果戰(zhàn)爭打輸了,人民也被輸?shù)袅恕]有必要為德國人民基本生存將來需要什么而操心了。相反,對我們來說,甚至連這些都被破壞掉反倒是上策。……不管怎樣,在這場斗爭之后,只有劣等人會留下來,因為優(yōu)等人已經(jīng)被殺死了。” 希特勒那殘忍而又冷漠的態(tài)度使施佩爾事隔25年后想起還不寒而栗。曾經(jīng)的希特勒偶像連同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的理想在他心中已被擊得粉碎了。
在第三帝國剩下不多的日子里,施佩爾風塵仆仆地奔走于全國各地,使盡渾身解數(shù)去說服當?shù)氐能娛率啄X、大區(qū)區(qū)長及市長們,去發(fā)動自己所有朋友和工業(yè)界的同事,利用全部能夠利用的關(guān)系,從而結(jié)成一個十分廣泛與強大的聯(lián)盟以對抗來自希特勒及鮑曼的尼祿式的命令。在魯爾區(qū),他們將可用作毀壞煤田的一切炸藥、雷管和導火線全部扔進了礦井水倉,甚至向電廠工人和警察分發(fā)輕機槍,以對付鮑曼的特別爆破隊。在巴登,他們竟將希特勒要求炸毀所有自來水廠與公共設施的命令輕蔑地丟進即將放棄地區(qū)的郵筒。在柏林,他們還取走了安置在交通要道上的炸藥,使950座橋梁中的866座保持完好……差不多同時,施佩爾又接連從他的軍備和戰(zhàn)時生產(chǎn)部向各地發(fā)出與柏林暗堡希特勒相左的命令(僅在3月18日至4月7日的19天中,兩種命令已不下12道),故意制造出指揮混亂,讓人無所適從的局面。經(jīng)過施佩爾和他的朋友的一致努力,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始未及推行。以魯爾區(qū)為首的各工業(yè)區(qū)在戰(zhàn)時尚存的價值1000億英鎊的工業(yè)設備歷經(jīng)千辛萬苦,終被保留下來。
施佩爾在前半生的大部分時間,特別是在希特勒上臺后的十余年內(nèi),在抹畫德國歷史最黑暗的篇章中,曾扮演過可憎復可悲的角色。但是,作為一個帶著技術(shù)救國愿望投入法西斯懷抱的知識分子,他到底良知未泯。他在德意志的工業(yè)文明就要充當行將就木的第三帝國的殉葬品之際挺身而出,替戰(zhàn)后德國的基本生存與重建,爭取到最起碼的條件。無論他當時是從德國實業(yè)界、即大資產(chǎn)階級的根本利益考慮,抑或是以罪己懺悔之心去做這些事,這對歷史的進步終歸是起了好的作用。 1946年9月30 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在處以他20年監(jiān)禁的判決書中也認為:“在戰(zhàn)爭最后階段,他是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人之一:他們有勇氣告訴希特勒戰(zhàn)爭已經(jīng)打敗,并采取步驟保護德國和占領(lǐng)區(qū)的生產(chǎn)設施,使之免遭毫無意義的破壞。”施佩爾是德國那種有過不堪回首經(jīng)歷的較多知識分子的典型。他們最終能多少有些反抗希特勒的表示,是很需要一番勇氣的。施佩爾在垂暮之年出版回憶錄——《第三帝國內(nèi)幕》,為戰(zhàn)后人們對那段特定時期的歷史反思提交了一份苦澀的記錄。
參考文獻:
1.〔德〕阿爾貝特·施佩爾:《第三帝國內(nèi)幕》中文本,鄧蜀生譯,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版。
2.〔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中文本下冊,董樂山等譯,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年版。
3.朱忠武等編著《德國現(xiàn)代史(1918—1945)》,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4.〔德〕斯文·費利克斯·克勒霍夫:《納粹軍備部長阻止希特勒“毀滅德國”》(原題《希特勒在地堡中判了德國死刑》),載《參考消息》2015年3月26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