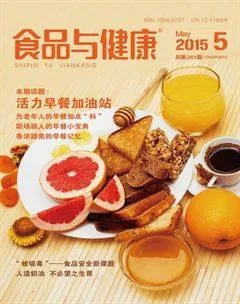香濃甜美的早餐記憶
黃璐
小時候,因為我個子長得很快,爸媽總是擔心我缺鈣,早餐中雷打不動的是牛奶。記憶中的早晨是行軍打仗一般的,媽媽要趕班車起得很早,她煮牛奶時才會叫起貪睡的我。等我磨蹭好坐在飯桌前,媽媽只趕得及給我梳上小辮兒便要急匆匆地出門了。等我睡眼惺忪地醒過神來才和爸爸開始吃早餐,這時爸爸會把已經溫吞吞的牛奶再熱一遍遞給我。
等我學會用電打火的煤氣灶,就開始自己熱牛奶了。點火、調成中火,等上一會兒,直到牛奶沸騰,關火。蓋著鍋蓋,很難判斷什么時候開,只好不停地掀蓋子。很小就從物理課本上學到“開水不響、響水不開”,也還試過“在鍋蓋上滴一滴水,水快干的時候,鍋就開了”的小竅門。煮沸的牛奶向上涌的過程,途經之處鍋壁會發出滋滋的聲音,越來越大,在即將溢出來的時候關火,在唰的一聲伴隨下,液面陡然落了下去。兒時記憶里,似乎只有經歷了這樣大起大落的牛奶,才是最好喝的。
喝奶這件事兒最具儀式感的時刻要數在姥爺家喝奶茶。每人面前放一個大碗,里面放著半碗剛燒開的牛奶,然后眼巴巴地等著姥爺煮磚茶。姥爺會端著熱騰騰的鍋,給每個碗里倒茶水。濃濃的紅褐色茶水混入雪白牛奶的時候,會泛起漂亮的、不規則、褐白相間的花紋,就如隨機而至的舞曲一般,每次都不同。剛沖好的奶茶很燙,姐姐和我要不停地沖著碗,吹啊吹,直到吹出奶皮子。把鏡面一般的奶皮子吹得微微起皺,再恢復鏡面,再吹皺,這是我們樂此不疲的喝奶伴生游戲。用一根筷子,把奶皮子挑起來,吃掉。再捏一小撮鹽,撒在碗里,感受筷子頭和食鹽粒在碗底摩擦的觸碰感,攪勻后就可以喝了。
大學學到牛奶均質這個工藝時,來自新疆的我和來自內蒙古的榕兒聊起小時候喝牛奶的經歷。她說她從小就討厭奶皮子,而奶皮子又很有營養,為了破解這個難題,她媽媽在煮牛奶的時候,會不停地攪啊攪,讓形成奶皮子的那點乳脂都散開,算是一種很初級的均質。在同樣來自牧區的我們的心中,好牛奶的標準不是用蛋白質含量多少衡量的,而是煮開晾涼能否結出奶皮子。
大學時期是在天津這個美食之都度過的,吃早餐成了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校園食堂會有十幾種選擇,大餅雞蛋、煎餅馃子、鍋巴菜、肉龍、肉包子、菜包子、豆包、各種甜粥、咸粥等等。只有在來不及的情況下,才會在宿舍小賣鋪的碩大電飯煲里撈一袋熱度合適的袋裝奶作為早餐,方便路上能迅速喝完。
學了食品專業,沒成為學霸,但也牢牢地記住了乳制品老師講的話,保質期和營養的損失成反比,保質期越長,說明殺菌溫度越高,營養損失也就越大。買牛奶首選巴氏殺菌牛奶,然后是利樂包,最后是利樂枕、利樂磚。對我而言,不同的選擇取決于購物的便利程度。我很少喝進口牛奶,縱然比國產奶香濃。而因為對超高溫殺菌造成的“燒過了”的“煳味”很敏感,我也著實不喜歡利樂包裝的牛奶。
工作之后,每天喝牛奶的習慣幾度中斷過,等撿起來的時候,我才后知后覺地發現自己原來和父親一樣對乳糖不耐,喝牛奶會脹肚腸鳴,甚至輕微腹瀉。真是個“相愛容易相處難”的尷尬境地。為此,媽媽給我制定了“對抗計劃”,我開始喝奶茶,原本奶、茶對半的比例,被調整成奶1茶2,等到腸胃習慣了,再調整成奶茶對半,再適應,再調整成奶2茶1,經過半年多的時間,我終于不那么敏感了。
不知不覺中,我也不再非熱牛奶不喝,甜奶茶、咸奶茶、咖啡也都是我所喜愛的。現在家里訂了鮮牛奶,早晨的時候,煮一杯咖啡,用半瓶牛奶打奶泡做卡布奇諾,剩下的半瓶牛奶用來做酸奶,晚上喝。既完成了“每天一瓶奶,強壯一個民族”的補鈣重任,又避免了過多地直面乳糖。
我不知道將來我的孩子會不會也乳糖不耐,心底很是希望能將這個早餐喝牛奶的家庭傳統繼續下去,希望他也同我一般個高、腿長,智齒一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