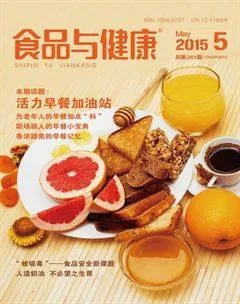場院
西風
1975年時,我生活在東北老家——遼寧省黑山縣四間鄉的大吳家村。在俺們那嘎達,沒有人會說打谷場這么文縐縐的稱謂,一般都管它叫場院。春種秋收,忙活了一年的莊稼人為的就是顆粒歸倉。而那兩個籃球場般大小、呈方形的場院上,所存放的不僅是大家伙汗水的結晶,更是一村人一年的口糧和性命。從這個意義上講,場院可牽掛著一村老少爺們兒的敏感神經,誰毀壞了它,村里人非跟他玩命不可。
場院在生產隊隊部的后面,因為種上了綠油油的蓖麻,平時不顯山不露水。蓖麻收割后,一開春場院上殘留的谷粒就開始玩了命的瘋長。動鐮收秋之時,先要做的準備工作就是——平場。壯勞力割去野草,再吆喝著幾頭牲口,牽動著帶把兒的石磙,從早晨轉到晚上,像壓路機般將地面碾平。約摸一個禮拜,場院的空地被弄得平展舒爽起來。接下來就是用高大的高粱秸將場院四周密不透風地圈起來,防止小偷或牲畜的侵犯,只在靠隊部的這面,留著一個五米來寬的豁口,以供車輛和行人出入。做完這些瑣碎的活計,一個氣派、拙樸的場院就靜待糧食的到來了。只是偌大的空地一時還沒有派上用場,顯得格外冷清空寂。不過不用擔心,過不了幾天,熱鬧就該來了。
秋收終于到了。高粱割了,大豆割了,谷子割了,玉米棒子擗下來了,往常綠得讓人心醉的田野,仿佛一下子開闊空曠起來。莊稼們整齊的茬子在秋陽下閃爍著微弱的銀光。這時你可以從一個村莊毫無遮蔽地望到幾里開外的另一個村莊。當田里的糧食被一車車運到場院的時候,全村的勞動力就基本都轉移到這兒來了。在場院的周圍,堆放著十幾座小山似的糧垛,人們用席子扎了一個又一個的圓囤,然后把肥肥胖胖的玉米棒子裝進去。場院的中央地帶暫時閑置,這里以后還要派上更大的用場。
糧食進了場院,就該有個把門的。護青員老王頭搖身一變,成了眾人注目的看場人。在出口的西側,有一間低矮的幾平方米大的土屋,那是老王頭住的地方。說來這老王頭有些特別,他似乎一輩子都穿著青衣青褂,看起來讓人感到沉重,也令人生畏。老王頭對看場的差事一點也不馬虎,白天他就坐在土屋前的條凳上,像大偵探福爾摩斯般警惕地注視著出出進進的人們,防止有人把公家的糧食偷偷帶走。到了夜晚,特別是做活的人們離場后,老王頭提著一根酒盅口粗的木棒,不停地在場院門口轉悠,防止小偷或“階級敵人”搞破壞。這檔子事鄰村就發生過一回,不過不是“階級敵人”搞的鬼,而是一個根紅苗正的小伙子,和生產隊長的女兒談對象談崩了,便心生怨恨,一把火點到了場院。雖然只燒了了半個糧垛,損失不大,但罪名不小,據說被判了個無期。
秋末冬初是場院最忙碌、最喧鬧的時節,不論白天還是晚上,都有人影晃動,說是人聲鼎沸也不為過。到了夜晚,兩盞大燈泡將個場院照得燈火通明,一是便于人們夜戰,二是便于看場人明察秋毫,一發現蛛絲馬跡,就將壞人逮個正著。這時,閑置的場地中心地帶有了用武之地,幾個石磙在牲口的帶動下,骨碌骨碌周而復始地轉動著,碾軋著高粱穗、谷穗或大豆棵子,直到顆粒脫離了穗子。
接下去便是揚場了,數十個壯漢輪番上陣,將手中的木锨撮進糧堆,一撮撮地向空中揚去。當然這活計必須是在有風的天氣里做。在揚場的過程中,空中紛飛的糧食多少有點像天女散花。只是這活兒又臟又累,一不小心,碎屑就飛進了雙眼,給人臉上添上些許淚痕。糧食揚好了,就堆積成山,讓人看了滿心歡喜。
至于玉米棒子,就不好對付了。那時沒有脫粒機,得用手一穗一穗地剝,進展相當緩慢。這項工作多半在夜里進行,所謂“夜戰”是也。村里的勞動力坐在玉米堆的周圍一邊忙碌,一邊說笑。有道是男女混雜,干活不乏。不時有膽大的男人說幾句葷話,惹得大伙兒朗聲大笑,趕走睡意。就這樣,一囤一囤的玉米棒子,也在人們的調笑聲中剝完了。
打下了糧食,絕大部分要送到糧站。那糧站距離村子十來里地,五輛馬車,少說要來回跑上半個來月才能將糧食送完。當一麻袋一麻袋的糧食裝上了車,馬車朝向糧站撒歡地奔的時候,村里人就開始估摸今年的收成了,盤算著家里每口人可以分到多少口糧。通常年景,每人能分到四五百斤毛糧,足夠吃一整年。但遇上了災年就要少許多。公糧繳不上,還要吃返銷糧,讓一村人特別是生產隊長臉上很沒面子。沒面子的事還在后頭,到了青黃不接之時,家里的糧食吃完了,就得用野菜甚至樹皮充饑。所以,災年的場院更加令人牽掛。分糧的日子到來了,當人們大袋小袋地往家扛糧食的時候,就意味著場院今年的使命接近了尾聲。接下來便是年關了,村里人開始“貓冬”,殺豬宰雞,籌備過大年的事宜。
但場院還在,只是沒有了小山似的糧垛,土屋里沒有了偵探般老王頭的身影,全然沒有了往日的喧鬧。只有一個小角落里還堆積著孤零零的幾個谷垛,那該是牲口們的口糧吧。地面上散落著些許的糧食,不時有灰麻雀成群地飛過來,落在地上蹦蹦跳跳地啄食殘留的谷粒。進了臘月的門檻,鵝毛大雪一場場地下,偌大的場院一片銀白,便有調皮的男孩掃出一塊雪地,埋下鐵夾,捕幾只貪吃的麻雀帶回家燒烤。
我在1982年離開了東北農村的老家,自此之后再也沒有重返故里,更是無緣再去看看場院。聽前來看望我的父親講,那場院早已徹底廢棄了,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田野的一部分。土地承包到戶后,人們只在自家的院里或路邊開辟臨時打谷場。父親特意提到了老王頭,說他過世前抓住老伴的手,動情地說:“這輩子能做上護青員和看場人是我的福分。大家伙把人命關天的事兒讓我做,是對我多么大的信任!”出殯那天,全村的鄉親們為他送葬,有的甚至唏噓有聲……聽到這兒,我的雙眼也閃出了淚花。
盡管場院是那個特殊年代的產物,但它早已融進了一代人的情感里,不應被人遺忘。就像現在的我,昔日寬大氣派的場院在我的腦海中時常顯出身影:糧食在空中隨風飄落,石磙發出永不疲憊的音樂般的聲響。只是,沒有了場院,在寒冷的冬日,那些無家可歸的麻雀將到哪里覓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