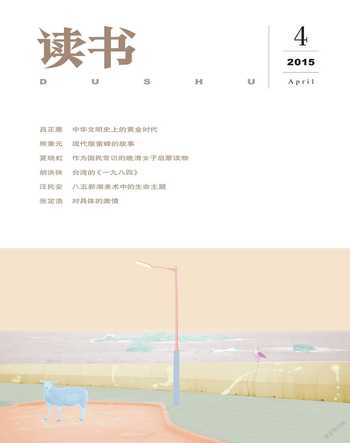消費社會的“奢侈”辯證法
任何時代為“奢侈”正名都會激起一片嘩然:顯然,在任何時代,奢侈總是與道德上的不光彩如影隨形,即便“奢侈”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某些技術革新、某些生產進步,但奢侈對道德規范的突破常常沖擊了人類的倫理底線,就像伯納德·曼德維爾《蜜蜂的寓言》那樣遭到同時代的一片罵名。盡管如此,十八世紀那位偉大的哲學家大衛·休謨還是寫下了為奢侈“正名”的文章,這“粗戾之音”吹響了消費社會的號角,讓那“物質匱乏”的時代充滿了創造的活力;一種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休謨那里業已成形。兩百多年以后,消費社會已千瘡百孔,奢侈之物成為符號、標簽,貼在各種社會秩序之上,讓這“物質豐裕”的社會顯得疲軟、乏力;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法國思想家鮑德里亞自成一體。在馬克思之前與之后,在工業社會誕生之際與所謂的“后工業社會”(其實都是消費社會),兩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相同的是“消費”這一人類行為,不同的是“消費”背后“人”的欲望的滿足,以及如何追求這種欲望的滿足。從休謨到鮑德里亞,奢侈在消費的歷史中變得有些無所適從、方向盡失。
一七五二年,休謨在他的《政治論文集》中拋出一篇《論奢侈》,其他各篇的見解立即引來了英法哲學家的好評,而唯獨這一篇,招來的是一片批評和譴責。雖然休謨后來將標題改為“論技藝的進步”,但正文卻一字未改,而其他篇幅都有或多或少的刪改,這也可以說明休謨對“奢侈”的態度沒有改變。那么,休謨是如何界定奢侈的呢?“通常說來,奢侈是指對各種感受享受的滿足有了極大的改進。”所謂的“感官享受”,自然是人們能夠得到更好的物質享受,甚至從中獲得更滿意的精神享受。這種享受可以是道德的,也可能是有損道德的,因而休謨才將“奢侈”一分為二:奢侈之于社會的利弊同時存在,若奢侈不再有害,它也將不再有利。一個文明社會,不是一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社會,而是一個物質相對豐裕的社會。美食華服、豪宅良馬,富人的奢華消費為窮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圣誕節餐桌上一碟豌豆所需要的操勞和辛苦,卻能維持一大家子六個月的生活”。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窮人也需要得到基本物質資料的滿足,人,才會感受到人之為人的“人性的尊嚴”。
然而,籠統地解釋這種“人性的尊嚴”是有失休謨本意的,因為這個術語在每個世紀的內涵可能都在不斷變化,即便今天也仍然在說“人要活得有尊嚴”;正確的做法是將其置于歷史背景之下,然后延續至今,再重新理解。很難說明,休謨所說的奢侈僅僅是人對基本生活資料等物質上的滿足,而沒有階層劃分、身份地位等符號消費的內涵,因為在消費過程中也包含了人的精神滿足,這種自我滿足本身就包含了社會學意義上的很多其他功能,比如炫耀性消費或莫斯所說的“夸富宴”式的消費等等。不過,休謨語境中的“奢侈”,更多與物的“有用性”或使用價值相關,而與抽象的符號較少聯系;換言之,休謨所獲的“奢侈”,似乎還只是技術革新及其解放人類自我的一種手段。
可以認為,休謨為“奢侈”的正名是對人類消費行為的肯定,是對技藝進步的提倡,是對人性自我解放的訴求(這與他主張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并不矛盾)。“奢侈”意味著需要人類技藝的進步,同時人的其他欲望也會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更多滿足。技藝的進步孕育文學藝術的成長,意味著人類各種能力的覺醒。“時代精神影響著一切技藝,人類的心靈一旦從昏睡中覺醒,就會孕育成長,并在各個方面展示自己的才能,提高各項技藝,提升各門科學。愚昧無知被徹底摒棄,人們享受著理性人的榮耀,享受著思考和勞動的樂趣,享受著培育心靈和肉體的樂趣。”十八世紀還是一個“喚醒心靈”的時代,思考、勞動、從身到心的解放,這些都會在“奢侈”的名義下突顯出來。盡管“惡”永遠不是“善”,“毒藥”永遠都有“毒”,但人類如若不是受到奢侈“這種毒藥”的侵蝕,便是受到懶惰、自私等“毒藥”的腐蝕,后者只會讓社會淪為一具僵尸、一潭死水,只會讓人性在愚昧與盲從的遮蔽之下失去光彩。因而,奢侈抑或技藝的進步,在休謨的政治經濟學中占有的位置,僅僅在“利益的激情”這一驅動力之后,和貪婪一樣推動著經濟社會的前進。這正是休謨《論奢侈》一文的主要觀點,它與盧梭截然相反,與亞當·斯密大相徑庭;這兩位與休謨交往甚密的學者,前者嚴厲抨擊敗德,連帶著一起譴責奢侈,后者雖然深知嫌貧愛富終能帶來社會財富的增加,但對此帶來的人類敗德行為則表示深深的憂慮。但是,兩者都沒有公然承認這種“毒藥”的作用;休謨承認了:因為,這本就是矛盾重重的人類本性之一。
即便如此,休謨也不會為奢侈唱起贊歌,他沒有像曼德維爾那樣鼓吹社會秩序是由“惡”、奢侈、貪婪等等建構而成;作為歷史學家的休謨,同樣看到信用在消費社會的脆弱性—而信用背后潛藏的正是對未來的消費,甚至是對未來的奢侈消費。雖然休謨對社會信用的認識更多是基于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時戰時和的局勢,但其觀點放在現代正當其時的信用社會卻一點兒也不過時。抵押國家收入,讓子孫后代還債,不正是當今社會非常流行的做法嗎?發行公債的確可以刺激經濟的發展,但也能讓一個國家陷入貧困虛弱的境地;而一旦人們疏于維護信用體系,信用便會像脆弱的瓷器一觸即潰,整個社會轟然坍塌,底下埋葬著累累白骨;人,終因其過度的欲望和貪婪而付出應有的代價。幾年前華爾街信用膨脹的災禍,正是最好的例證。故而休謨有言:不是國家毀滅信用,就是信用毀滅國家(休謨:《論社會信用》)。
社會信用脆弱難建,卻又能一再重建。一個信用體系崩潰,另一個信用體系又開始建立。這是因為人的欲望在時刻催促著重建信用以方便自己,而信用又反過來不斷馴化欲望。如果說在十八世紀信用消費還不太普遍,沒有馴養出人的消費習慣,那么從二十世紀一直到今,這樣一個看起來非常“豐裕”的消費社會,它所進行的是消費培訓以及面向消費社會的社會馴化。鮑德里亞簡單地提到信用在消費社會中的決定性角色。他說:“信用表面上是一種額外獎勵,是通向豐盛的捷徑,具有‘擺脫了儲蓄等老舊桎梏’的享樂主義品性。但實際上信用是對幾代消費者進行的面向強制儲蓄和經濟計算的社會經濟系統馴化,否則它們在生存中就可能避開需要的規劃而成為無法開發的消費力。信用是榨取儲蓄并調節需求的一種訓練程式—正如有償勞動是榨取勞動力并增加生產力的一種理性程式一樣。”(鮑德里亞:《消費社會》,二零零八年,63頁)消費社會向人的欲望大開方便之門:以你的信用購買你想要的任何東西,然后你會擁有你想要的豐盛,滿足你的各種欲望,最后,請付出你一生的勞動償還這筆債務。在不斷的抵押與還債的過程中,在對好幾代消費者進行馴化的過程中,信用終于成為后工業社會須臾不離的伴侶。個人可以抵押信用,機構或公司也能抵押信用,國家同樣抵押信用。試看如今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信用卡、房車按揭等等,充斥著企業和機構的風險投資與信用評估,乃至某個經濟體系中某個主權國家的信用體系,無不處于一臺無形的消費能力的“挖掘機”之下。
無可否認,信用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刺激作用;貪婪的欲望在信用的許諾下得到滿足,并且不斷向縱深之處開挖,同時獲得的是技術革新、物質豐盛。這是一種在“想象”和“幻象”的感召力之下形成的信用經濟體系。“當代人越來越少地將自己的生命用于勞動中的生產,而是越來越多地用于對自身需求及福利進行生產和持續的革新。”(《消費社會》,62頁)整個社會經濟系統馴化的不僅僅是個體的消費者,而且包括社團和群體的消費者,甚至反過來馴化了整個社會經濟系統本身。交換和消費在這種經濟系統的馴化與自我馴化中異化成各種各樣的符號、符碼。
現代社會就是一個信用社會,奢侈或消費正是在信用的承諾之下得以擴張。只是現代的奢侈或消費的內涵在經濟學意義上悄悄地改變了,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關于需求(最廣泛意義上的)、物品和滿足的理論,鮑德里亞認為傳統的理論已被符號政治經濟學替換,因為物品和需求都改變了。“在消費中物品朝著某種廣泛的范例進行變化,其中有另外某種語言在進行表達,有另外某種東西在發言”;“需求的客觀特點變得更加難以確定,因它貪得無厭、永遠無法滿足”(《消費社會》,59頁)。消費中的物品,比如冰箱,它可以是用于冷藏的儲物柜,可以是沒有發揮其功能的奢侈品,可以是標識使用者經濟能力的符號,它是什么不重要,它的意義在于“它與其他物的關系之中,存在于依照意義的符號的等級而具有的差異之中”(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二零零九年,45頁)。它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邏輯顯然無法以傳統政治經濟學解釋。同樣,服飾、美食、居所、代步工具、語言、文化、科學、宗教以及肉體本身,在消費理論中都需要以新的眼光看待。在資源稀缺性的條件下(所謂的豐裕社會只是相對的豐盛,而資源稀缺和匱乏卻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常態),“奢侈”并不等于你擁有了某個“物”,而是等于你擁有了某個符號。
藝術品拍賣市場體現了現代社會最典型的符號交換體系。在拍賣會上,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因被忽視、被否認而缺失,經濟意義上的交換價值和象征價值都失去了自身的地位,成為符號/價值的追隨者。藝術品進入拍賣市場,意味著一種“投資”,審美功能的重要性微乎其微,隱身于買賣的背后,作為奢侈的理性升華。在今天世界各個角落的藝術品拍賣市場,無不充斥著這種符號消費。傳統社會中高貴的藝術品依然帶著奢華的面孔,而真正的藝術欣賞卻成為一種“奢侈”。
同樣,開一輛梅賽德斯和開一輛捷達、穿香奈兒套裝和穿地攤上的便宜貨、住頂級海邊別墅和住鬧市區一間小公寓,完全代表著兩個不同的階層、不同的地位和身份。顯著的階層差別形成的意識形態,借助媒體將這種社會秩序傳達到世界的每個角落,激發亞當·斯密所說的人人都有的“改善自己境遇”(better one’s own condition)的欲望,調動人性中每一種可以達到此目的的激情,在“符號”的秩序中建構社會秩序,借此鞏固這種意識形態,進而再次鞏固這種社會秩序。電視、網絡、平面媒體的廣告每天都在“引誘”人的欲望:擁有“這個”,你便擁有了什么地位,成為什么人;必須擁有“那個”,因為它正在某某人群中流行,它就代表著時尚和潮流,否則你就過時了。不必在意“這個”或“那個”究竟有什么用處,你只需要擁有這個符號代表的意義即可。鮑德里亞稱之為對“符號”的崇拜,并以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重新闡釋了當今社會:“拜物教實際上與符號—物關聯了起來,物被掏空了,失去了它的實體存在和歷史,被還原為一種差異的標記,以及整個差異體系的縮影。”(《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80頁)如鮑德里亞所言,欲望的滿足不是建立在實體之物帶來的快樂的基礎之上,而建立在體系的基礎之上。
在所謂的后工業社會,欲望的滿足變得光怪陸離,因為欲望總在不斷變動、不斷消逝,又不斷生產和創新。人們被不斷提醒著“不要錯過這種享受”、“不要錯過那種體驗”,各種以美和快樂的名義命名的“設計”變換方式激發人體內的欲望,進而讓人為此付出各種各樣的代價。這對于經濟社會來說本不是錯—恰如那只“無形的手”的引導;錯的是人的欲望滿足已然找不到方向,遠離人的幸福大門。在久遠的十八世紀,休謨說人的幸福體現在三個方面,即“勞動、娛樂和閑暇”,三者以不同的比例混合,才會找到幸福的統一體,才不會破壞幸福的趣味。如今欲望的無限膨脹似乎完全破壞了這一趣味。欲望催促著人們不斷勞動,敦促人們享受勞動成果,在片刻歡愉之后投入下一次勞動之中。勞動的成就感在瞬間消失,娛樂變得索然寡味,閑暇則早就被欲望主宰。人,本在啟蒙時代就開始自我解放,卻在現代社會被束縛得越來越緊。鮑德里亞說:欲望不是在“自由”中得以滿足,而是在法則中—不是在價值的透明中,而是在價值符碼的不透明中。這就是欲望的符碼,這一欲望“需要”恢復游戲的規則—它需要這些規則—以滿足自身。正是欲望所帶來的規則,正是在欲望獲得滿足的視域下,社會秩序才得以建立。社會秩序為了能夠再生產自身而不斷被拜物教化了的顛覆秩序(欲望的滿足)結合在一起(《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211頁)。于是,人在滿足自我欲望的同時,也在毀滅欲望的滿足感;人本應在奢侈品的消費中獲得快樂和幸福,在技藝的進步中感受到人性的提升與解放,并在此過程中趨于人性的完美和完善;遺憾的是,人沒有在欲望的滿足中感受到自我的提升,反而感到越發的不滿足,人性也變得越發殘缺不全。何以至此?
十八世紀的休謨自然無法預料到后工業社會的消費主義,但他從人類本性出發的教誨放在今天還不算過時。貪婪本是人的天性,也是勤勉的刺鞭,若禁止“罪惡的”奢侈,而不醫治人性中的懶惰和冷漠,勤勉和進步將會與奢侈同時消失;人性自有惡的一面,唯有良好的教養才能讓人學會尊重、學著謹慎克制、學著成為一個“優雅之士”。休謨希望人能夠在善惡的權衡和比較中、在奢侈和消費的積極影響下自我解放;但這一任務到今天仍然沒有完成。二十世紀的鮑德里亞直接從消費出發,揭示從物到人的主人—奴隸的關系,進行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在休謨時代,盡管人性充滿矛盾,但人至少還沒有完全淪為物的奴隸—彼時,消費社會方興未艾;十九世紀以降,消費社會成為一個巨怪,吞噬一切人性、主宰所有的物和人。在這個巨怪的魔力之下,人性的全部內容淪為物的奴隸—此時,消費社會正當其時。的確,如今的批評領域缺乏對消費“異化”的批判,不過此前要做的功課,是應該探究一下“異化”之前的消費與奢侈究竟如何。消費社會的奢侈辯證法批判或許是一條路徑。
(《休謨論說文集(卷一):論政治與經濟》,大衛·休謨著,張正萍譯,浙江大學出版社二零一一年版。文中提到的休謨文章均出自該書。《消費社會》,讓·鮑德里亞著,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零八年版。《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讓·鮑德里亞著,夏瑩譯,南京大學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