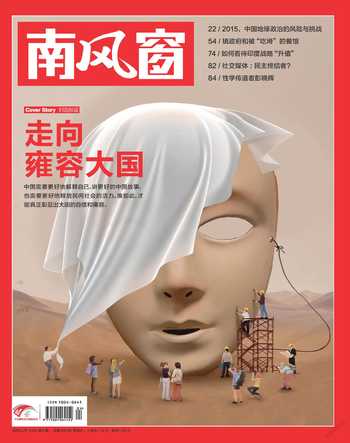破解權力和生存的糾葛
石勇
就像是慣例一樣,每到農歷過年前,在中國總會上演“農民工討薪”、“產業工人回家過年”的劇目,一年又一年。
它可以說明很多東西,至少是在提醒,中國社會仍然處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時段上,而且,無論是就產業工人的權利保障,還是就經濟結構對社會結構的支撐來說,我們遠沒有到達轉型基本完成的終點。
在以前,過了年之后,沿海發達地區,大城市,總會出現一輪“用工荒”。但在經濟結構早已發生很大變化的情況下,今年還可能嗎?相信很多人已經捕捉到了這個“問題意識”。
所以,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2月2日,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法律工作部部長郭軍在全總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指控”富士康等一些企業長期違法安排勞動者長時間加班,致使部分勞動者出現各種心理健康問題,導致過勞死或自殺現象時有發生。
全總要在產業工人的維權上發揮更大的“負責任作用”,無疑值得贊賞。然而,在經濟、社會背景發生了明顯不同于以往變化的情況下,它對富士康等的點名批評,在引起的可能反應上,會不同于以往的邏輯。
果然,富士康并不放低姿態默認批評,而是發布了一份聲明,起來“叫板”全總:“我們請郭軍先生在不斷點名批評的同時,能夠‘走到基層’,了解企業和員工的心聲。”它甚至還用了現在較為流行,符合“正能量”的語言范式:“不要忽視企業的成長和進步。”
富士康否認員工加班跟他們出現心理問題甚至自殺有因果關系。這確實是一個復雜的、無法簡單地建立邏輯聯系的問題。但它承認,“包括富士康在內的所有制造企業都面臨如何處理員工加班問題的困擾”。
輿論把富士康對全總的“叫板”,跟前段時間阿里巴巴對國家工商總局的“叫板”相提并論。這其實是一個誤會。阿里巴巴的“叫板”,跟富士康的“叫板”具有不同的背景,所擁有的籌碼也不一樣。
富士康的底氣,來自于它在貢獻的稅收上,以及解決就業問題上對于政府的強大吸引力。而這兩個吸引力,尤其是就業問題,正是在變化了的經濟和社會背景中,最可能被重點考慮的。畢竟,秩序的穩定對于中國來說是一種壓倒性的政治考量。
有這樣一個很現實主義的邏輯:假如經濟很困難,那么,能夠讓龐大的青壯年人口有活干已經不容易了,還在糾纏于“加班”、糾纏于“合法權益”是否不合時宜?在過去并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放在現在,是否有意義?我們都知道,功利的視角,在權力的運作中,很多時候要大于權利的視角。沒有吃飽的人好像是談不上吃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現實,還有可以想象的未來,確實構成了富士康對全總“叫板”的支持背景。
多年來,房地產不僅掏空了社會,而且嚴重侵蝕了實體經濟。進入2015年,大量的制造業已陷入困境。正如這個冬天一樣,企業老板跑路,甚至自殺的新聞,讓人感受到了經濟的寒意。
另外,外資也有不少在撤離。比如,去年12月17日,有消息稱微軟宣布將關閉位于北京及東莞的手機工廠,未來在亞洲將通過越南河內工廠來保證產能。微軟對此確認,稱此項調整將于2015年第一季度完成。
這意味著,中國不僅面臨經濟下行的挑戰,而且面臨著失業人口增長的威脅。畢竟,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這樣的實體經濟,不僅具有經濟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和社會功能,它們所創造的工作崗位,是解決龐大的農村青壯年人口就業的主要渠道,而這些人,很多已經不可能回到農村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呈現出了“不可逆”的特征。實體經濟不行,根本就不可能消除嵌于其中的社會政治風險。
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以及政策所給人的預期下,富士康所存在的意義,作為一種象征,事實上已不太一般。它已不僅僅是一家工廠,而是消化中國的社會政治風險的其中一個容器,盡管只是一個小容器。
員工加班的背后,無論是否自愿,背后無疑是一種經濟的強迫,馬克思早揭露了這一點。但現實讓人哭笑不得:當我們關注產業工人的合法權益是否被侵害時,不得不想一下:這個合法權益對于希望能得到高一點收入的他們來說是否必要?或者說,保障了這個合法權益,他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更高?而當上8小時的班可能都要搶時,富士康作為民間所稱的“血汗工廠”,又如何重新評價呢?
這是一個困境,權利和生存的糾葛。它已延續多年。2015年,很多東西和過去已不一樣,到了拿出勇氣去真正破解它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