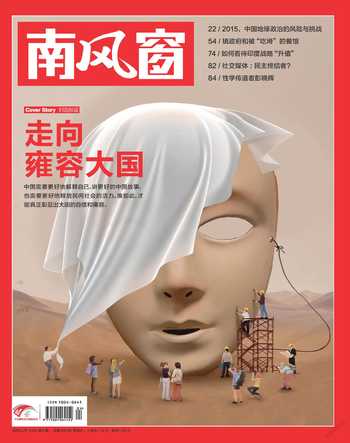企業家為什么停不下來?
甄靜慧
2013年馬云曾高調宣布退休—注意,他說的是真正的退休,而不僅僅是辭任阿里CEO—“48歲之前,工作是我的生活,明天開始生活將是我的工作”,甚至還具體到透露,未來將從事教育環保事業。可是,人們僅震驚了短短18日,他就耐不住寂寞復出,推出物流“菜鳥計劃”,你看看現在的他,又整天占據著商業版的頭條。
那么,馬云“退休”是想耍耍公眾玩嗎?我覺得也不是。其實他真的有個退隱江湖的夢想。證據就是:但凡阿里巴巴的員工,都知道他狂熱地熱愛金庸小說,常常幻想成為武林高手,而金庸小說人物里,他最喜歡的人是長年隱居華山、教導令狐沖獨孤九劍后就絕跡江湖的絕頂高手風清揚。
可惜,幻想終歸是幻想,不獨馬云,中國第一代創業的民營企業家,估計鮮能做到方當壯年就把自己的企業交給別個,從此西湖泛舟自在逍遙。
記得數年前,我和朋友在南京拜訪一位民營企業家,大家叫他Z總。他家就在當年的中國首富張近東家旁邊,同樣規格的3層別墅,還有個很大的地窖。大家約好了晚上9點,我們在客廳一直等到將近11點,毫無動靜,最后還是他的小女兒跑上樓看了一圈,說,“爸爸等你們的時候在椅子上睡著了”。
聊天的時候Z總告訴我們自己每天的作息:往往是早晨五六點,老婆孩子還沒起床就出門,凌晨回家時他要躡手躡腳進房間,免得吵醒熟睡的老婆。一周下來,跟親人說話的機會都很少。我們跟他開玩笑:你這棟豪華別墅每天只用來睡4個小時覺,日常都是保姆在享用。他苦笑。
中國老一代民營企業家不興放權給CEO,頭發都白了還總是有忙不完的事情,人人一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悲壯姿態。這固然跟職業經理人制度不健全等客觀因素有關,然而更重要的還是他們內心有一種很隱秘的“繼續忙下去”的需要。
每個人內在都有一股原始動力,需要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社會認可的個人價值就是財富與地位,這已是赤裸裸不需要掩飾的了。無數急于證明自身價值的年輕人扎進社會,努力按照金錢地位的標準打造自身。有的人成功了,成為精英;“失敗者”則從生活品質和精神心理上都淪為了“屌絲”。
然而成功者也不必沾沾自喜,此刻你以為財富可以帶來安全感和幸福感,殊不知附著在外部世界上的價值認同都是不安全的,一旦失去這些東西,人就一無是處;而它帶來的滿足感也有一定閾限,太有錢了,就只剩下“怕失去錢”的恐懼而無法從“賺更多錢”中獲得幸福。
如是,這個焦慮的物質追逐游戲不但永遠停不下來,一旦游戲玩得太成功,無意義感和虛無感還有可能殺上門來。
當然,企業家比普通財富精英又要好一些。家族企業對于創業者而言,并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創造財富的機器,那些優秀的民族企業血脈里,往往承載著一個家族的理想、夢想甚至使命。這些價值取向離真正的“不假外求”雖然還有相當距離,但比起單純的金錢游戲畢竟是更指向內在的—俗話就是“有內涵多了”。
所以,民營企業家即使已積累了“只剩下數字意義”的財富,仍然能從對家族企業的不斷付出和承擔中獲得價值感,這就注定了他們不會輕易把這份責任假手于人。
對大多數務實型的企業家來說,這沒有太大問題—老到真的干不動再說唄。但如果他們偏偏又有點浪漫情懷,時時幻想自己能當一把風清揚,那心理沖突就免不了。這么想,馬云的出爾反爾,不僅可以理解,甚至讓人有點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