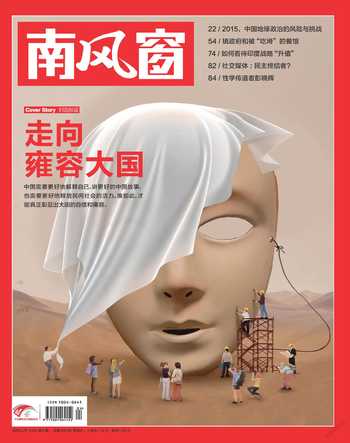評刊
劉韜 廣州新南社會發展中心理事長
“中產階層”并不是什么新鮮詞,盡管歷史淵源甚久(早在1745年James Bradshaw所著的小冊子里既已提過),并且含義紛繁蕪亂,似乎并不曾有人能夠清晰地定義出“中產階層”,更休提明確指出到底哪些人屬于中產階層。與其說中產階層是一個單純的社會階級分層法,不如說它是一個身份的構建,即:哪些人被看作中產階層、哪些人認為自己是中產階層。
但是,這種身份構建,連同“中產階層”這個概念本身,有可能在實際上忽略了許多極為重要的結構性不平等。
眾所周知,“中產階層”這個概念的大興,與國家福利體制的興起有關。然而按照秦暉的觀點,今天的中國實際上存在著“負福利”現象,體現在我們的經濟適用房實際是圈農民的地去給一些富人建廉價豪宅,以及某些與普通納稅人無緣的“公務員經適房”。因此,倘若我們迷戀于“中產階層”這個概念,就有可能意識不到這種結構性的“負福利”不公。舉個例子來說,大學同班的兩人,張三去了外資公司上班,李四去了政府當公務員,測算其各種指標和自我認同,很有可能都會將二人同時歸入“中產階層”的范疇,卻忽略了其背后的原因和差別。
更為重要的是 ,當我們不斷嘗試使用個案去完成“中產階層”的整體敘事的時候,我們實際上就在回避更為重要的問題:為什么是這些人?
我們今天所談的“中產階層”很多時候是與那套個人奮斗的個人成功學話語緊密相連的,從而忽視了階級本身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悉尼大學古德曼(David Goodman)教授的新書《當代中國的階級》中明確指出:那種好像任何人都能通過自己努力來贏取財富、地位和權力的中產階層神話,實際上缺少可靠的實證依據。古德曼教授的研究發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地方,有73%的財富和地位是世代相傳的,而在中國,這個數字更要高。當面對一個又一個精致的個體故事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忘記,這些個體故事并不是全然的“個體故事”,更多的,他們是一個結構性的批量生產的結果。那些精致的個體故事精心地將階級再生產的結構隱藏起來,仿佛具體的主人公之所以成為中產階層,全然是靠努力奮斗,結果將個人成功裝扮得溫情脈脈、美艷動人,卻回避了其中可能的不平等和不公義。
在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這個概念并未為我們理解當下社會的種種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洞見,反而,它使得許多重要、尖銳、深層的問題和困難更加曖昧模糊、難以改善。
年輕人對于“中產階層”的概念可能并不清楚,我們大致的生活路徑是從蝸居開始,然后是“房奴”、“孩奴”等的一系列過程。整個過程中焦慮而又疲憊,甚至還要拉著父母一起,這是中國的現實。我關注的并非“中產階層”這一階層的形成過程和劃分,而是現有社會經濟結構是否已經在做空間的、情感的、文化的、法律等方面的準備,如果當一個社會沒有這些積極的準備,如果一個社會僅僅是在探討一個西方的社會人群,如果一個社會的思考還僅僅是我們“這一代”的現狀,那么,“中產階層”的未來還是不能厘清。
—鄭明陽(讀第3期《這一代的中產,和他們的未來》)
房子、職場、子女教育,這3個詞可以說是大部分中國都市人要面臨的主要問題,只是在不同階層、群體,具體的表現形式不同而已。筆者以為,無論處于哪個年齡段,選擇哪種生活方式,都必將是對另一種未選擇方式的放棄,與其處于原地焦慮彷徨,不如帶著初心,踏實地走好選擇的路。筆者也曾認識如文中的女性,在40歲時感到被職場與家庭生活壓榨得身心俱疲,但通過積極的心態調整、運動,加之發展業余興趣,參加公益活動等調節,重新找回了自信與快樂。
—天天天藍(讀第3期《白領尋夢:回到生活本身》)
通篇讀罷,投射出的是教育問題。“航姐”58巴掌打向的是家庭與學校:家教的扭曲、校制的呆板。思隴中學7名打架的少女中,有6個是父母常年不在家,一位只有母親在家。當留守兒童、“00后”與商業化漸濃的學校疊加,荒誕的現象隨時都能找到注腳。人之初性本善被顛覆了嗎?否。成長環境形成習慣,長期習慣凝固為性格,人生因此定調。教育就是從小要調好不同年齡段的每根弦,這樣才能奏出美好的人生。
—沈治鵬(讀第3期《“航姐”們的世界》)
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相信影響過很多人,它被掛在或鐫刻在很多耀眼的場所,已經成為了很多人信念的一部分。現實中,這句話卻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和諷刺,人們對于知識的要求太過于功利,已經視知識為一種獲取物質利益的手段,使得知識就是力量變得庸俗化。真正的知識,即豐富內在心靈的力量。被人們忽視后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含義變得沒有了內核。這值得我們注意和深思。
—馬舉廣(讀第3期《知識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