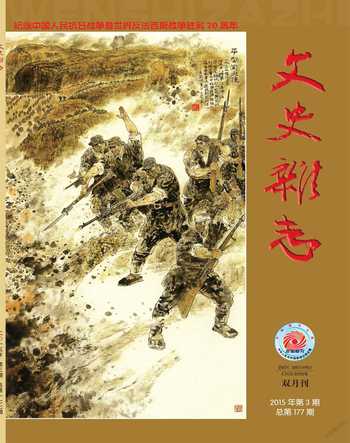屈原為什么要自沉汨羅江
肖燕
戰國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屈原在今湖南省的汨羅江自沉身亡,時年六十有二。關于屈原自沉汨羅江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其實是由探討角度的分歧所致,如思想道德的角度、心理傾向的角度、政治人格的角度等等。總括起來,主要有五說:
一、潔身說
此說以姜亮夫《楚辭今繹講錄》(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為代表。姜亮夫說:
屈原的個性是痛痛快快,有什么說什么,一點也不含糊,一點也不隱諱,雖然含糊隱諱,到最后也含糊隱諱不下去了,便跳水自殺。屈原為什么要跳水呢?屈原是清清白白的,“伏清白以死直兮”。“直”是道德的“德”字,即,我有這個德,先天得之于我的先祖高陽,我是楚國的宗族。我又有這樣的修養,既然“舉世皆濁我獨清”,我有什么辦法呢?他自己個人是光明磊落的,沒有一點含糊,他最看得起的道德是耿介,耿是光明的意思,介是大的意思,光而且大,這是屈原最高的理想。
潘嘯龍在《從漢人的記述看屈原的沉江真相》(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也指出:
屈原痛君不明,不忍見到楚國的前途敗送在“倒上以為下”,“變白以為黑”的舊貴族黨人手中;加之長期放逐,身心交瘁,再無重返朝廷、實施理想“美政”的一線希望。為了保持清白峻潔的操守,捍衛自己所畢生追索的理想,他因此莊嚴宣告:“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愿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終于帶著不盡的遺恨,懷石自投于汨羅江中——這就是詩人在絕命詞《懷沙》中,對于自己為何沉江所作的憤懣自白。熟悉屈原詩作的人們,耳邊不還至今震響著這位愛國詩人的錚錚遺言?
在該文里,潘嘯龍還強調說,至于屈原最終的自沉汨羅,雖然不是因為白起破郢而“殉國難”,但他是憤激于壅君佞臣的不識忠良,禍害國家,不忍心看到自己熱愛的祖國將再次遭遇比懷王失國還要危險的禍難,才憤然投江的。這樣的死,當然不是怯懦或逃避對祖國的責任。他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拼將一死,以期用“忿對沉江”的激烈舉動,震醒壅君的昏聵,震撼人心離散的楚人;同時表達對于黨人群小誤國殃民、迫害忠良的抗議。這樣的死,乃是出于對楚國前途和命運的關注和擔憂,出于對宗土、百姓的熱愛。當然,他的自沉之舉,也表明詩人在理想破滅后的無奈與絕望。
二、殉道說
此說以曲沐為代表。他在《紅樓“騷”影——試論林黛玉與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載《貴州大學學報》1993年第3期)里說:屈原是第一位自覺的也是自殺的詩人。曲沐又引李澤厚“死亡構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為‘驚采絕艷’的頭號主題”為證,接著曲沐寫道:
屈原的自殺無非兩個方面,一是社會政治的黑暗,一是性格的剛直,是生命在與現實的撞擊中而毀滅。林黛玉的自戕何嘗不是如此。屈原是出身于華族貴胄的政治家,其理想中的“明君”、“哲王”已不復存在。當著懷王、頃襄王這樣的昏君、庸主,其懷抱與志向無法實現,加之群小的讒害,“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言而齊怒”,因之憤懣不平,牢騷罹憂。……班固還批評他“憤懟忘身”,這說明屈原具有忘我的殉道精神。
胡學常在《“屈原與中國傳統文化”全國學術討論會綜述》(載《理論與現代化》1992年第2期)里轉述該學術討論會部分學者的觀點說,屈原的政治人格意義的影響決不亞于文學等方面,崇圣與忠君的沖突表現出了屈原的政治人格,他所孜孜追求的正是這種政治人格的完美和一貫。屈原的政治人格的偉大不在于功業與政治認識的超人,而在于他的行為邏輯的統一。正因為如此,他的政治人格釀成了他自殺的悲劇。屈原的死是他政治人格的升華,是追求理想決心的自我證明,是自我主體意識的壯烈表現。屈原是戰國時代應運而生的一位別具特色的“士”,他的人格力量在于他堅守“人道自任”的傳統信奉而對自身“內美”“修能”的不可動搖的認知,義無反顧地堅持理想(“志于道”)并重實踐的獻身精神以及視利祿功名如糞土,只求楚國強盛繼而統一天下的大志。
三、回歸說
前述胡學常《綜述》介紹了某些屈原研究者對屈原的心理頃向的研究,認為屈原的狂態表現在幻覺、幻視、幻聽、孤獨癥和易裝癖等五個方面,還分析了屈原充滿悲劇性的雙極血緣人格,并指出,屈原的人格精神促使他必然發狂,必然走向悲劇,他的自殺實現了他返本回歸血緣的愿望。有的學者還采用西方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屈原自戀的心理傾向,認為屈原總是將自我理想化而自贊自譽自我夸大,這使得他在現實生活中舉步維艱,最終導致失敗;屈原的求女也是他自大狂心理的體現,其潛在目的仍然在于自戀的滿足,而沒有多少真正追求異性的誠意;屈原以美人香花芳草而譽自我之高潔,毀世人異性戀之淫逸;屈原出國與留國的心靈沖突在于他去國的瞬間再現了“初度”時與母體分離的焦慮;屈原的投水自沉,實現了他回歸母體的愿望,意味著自我的再生。
四、尸諫說
此說以王之江《屈原之死芻論》(載《遼寧大學學報》1983年第6期)為代表。在該文里,王之江認為,楚國“黨人”橫行,搖搖欲墜。屈原被流放,不能生諫楚王。但他忠心未泯滅,沒有辦法使楚王覺悟,只好采取尸諫,投水而死。
楊劍宇也在《千古之謎》(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里轉述學術界的“尸諫說”觀點,稱屈原一直主張聯齊抗秦,而當時的頃襄王已經忘卻了疆土被蹂躪、父王被騙拘死于秦地的國恥父仇,反認秦為友,又“專淫逸侈靡”,“馳騁乎云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國內奸佞弄權,城池不修,百姓離心,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楚國已面臨亡國大禍。滿懷救國拯民之志的詩人卻受讒言而身遭黜逐,報國無門。在這種情況下,他還受到楚王的“逼逐”,被重新啟用的希望已經絕滅。身心交瘁的詩人不忍心眼見祖國和人民蒙難,也不愿在衰志不堪的晚年再忍受“逼逐”,于是,他在《懷沙》中斥責了楚王的昏聵,在《惜往日》中寫下了“寧溘死以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的詩句,決心以死諫來震醒昏聵無能的庸君,這才是屈原之所以忍受了兩次長時間放逐而依然等待,最后絕望而自沉的根本原因。
蔣建平亦在《千古之謎》中轉述了類似觀點,但稍有不同是增加了屈原效法彭咸一說。此說因屈原《離騷》中有“愿依彭咸之遺則”而生發,并引東漢王逸在《楚辭章句》中“彭咸,殷賢士大夫也,其諫君不聽,自投水而死”為證。此說認為屈原依彭咸的遺則,是指彭咸投江,屈原最后也選擇了投江的道路。《離騷》篇末,屈原說:“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對此,王逸特注:“我將自沉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所以,此說指出,屈原之尸諫,是向彭咸學習而來。
五、殉國說
此說在早以清初王夫之為代表。他在《楚辭通釋》中認為,屈原所以寫下著名的詩章《哀郢》是由于“哀郢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王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楚)亡可待也”。據此,現代的屈賦研究者大都認為,屈原投江是因為秦將白起攻破楚都郢,眼見國亡而殉國難之舉。
此說在現代則以郭沫若為代表。他在《屈原賦今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里如是寫道:
屈原既活到了六十多歲,他的流竄生活已經經過了很長久,然而他終竟自殺了。自殺的動機,單純用失意來說明,是無法說通的。屈原是一位理智很強的人,而又熱愛祖國,從這些來推測,他的自殺必然有更嚴肅的動機。頃襄王二十一年的國難,情形是很嚴重的。那時,不僅郢都破滅了,還失掉了洞庭、五渚、江南。頃襄王君臣朝東北逃難,在陳城勉強維持了下來。故在當年,楚國幾乎遭了滅亡。朝南方逃的屈原,接連受著壓迫,一定是看到國家的破碎已無可挽救,故才終于自殺了。
郭沫若還在《屈原考》中進一步發揮說:“就在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年,屈原寫了一篇《哀郢》……他看不過國破家亡,百姓流離顛沛的苦狀,才悲憤自殺的。”在《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中他認定:“屈原的自殺,事實上是殉國難。”
王夫之,郭沫若的“殉國說”,可謂深入人心,并特別為一般群眾所理解與接受。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