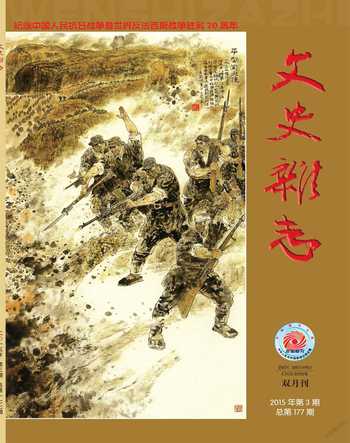讀楊銘《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一書
李仲良
楊銘先生的力作《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2012年由蘭州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06BZS009)的最終成果,其出版得到“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社規劃項目、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的資助。
一、主要觀點鮮明且深刻
楊銘先生《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一書認為:我國的西北地區有非常重要的戰略地位,東鄰華夏文明,西接中亞文化,北連塞外高原,歷來是多種文化相交沖突之地。漢、匈奴、氐、羌、鮮卑、敕勒、柔然、吐蕃、吐谷渾、回紇、突厥等民族相繼進入這塊寶地,在這里交往、沖突、調適。公元7世紀初,雅隆悉補野部落聯盟松贊干布承襲贊普,先后征服了蘇毗、羊同等部,建立吐蕃政權,統一青藏高原。吐蕃繼而向東北部、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擴展,不可避免地與多彌、白蘭、黨項、東女、西山、吐谷渾、大小勃律、突厥、突騎施、沙陀、回紇、鄯善、于闐、漢人、南山、嗢末、粟特等當地民族發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全方面的交往聯系。
楊銘先生提出: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形式主要有二,一是政治軍事交往,互派使節、締結婚姻、聯合行動、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二是經濟文化交往,物質、制度、文化、精神方面的交流。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三種類型:一是與青藏高原民族的關系類型,包括征服與被征服、融合與被融合;二是與河西走廊民族的關系類型,并未完全地、長期地占有,而僅是在某一個時期,對上述某個民族或一些民族實行過統治;三是與天山南北民族的關系類型,有交使、聯姻,也有聯合、對抗。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歷史作用有三:一是雅隆悉補野部的興起打破青藏高原小邦并立、強者爭雄的局面,逐步統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強大的吐蕃政權;二是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的交往,促進了一部分青藏高原民族“吐蕃化”,逐步融入了吐蕃乃至后來的藏族;三是居于今天山南北與河西走廊的民族,在與吐蕃的交往中,其語言文字、服飾習俗、文化藝術等受到了“吐蕃化”的影響。
作者在全書的結語中鮮明地指出: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歷史意義在于,吐蕃與西北諸族在相互借鑒、吸取對方先進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同時,自然就為促進本民族社會、經濟、文化的進步增添了新的元素,而這一歷史進程又揭示出一個不可辯駁的事實,那就是今天的藏族在其發展的初期——吐蕃時代,就已經將其演進的軌跡融入到了多源一體的中華民族之中來了。
二、引用文獻廣泛,考證深入精當
首先,該書在編撰過程中引用各種文獻十分廣泛。楊銘先生立足于基本的漢、藏文獻,并大量引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書及外文文獻,在充分掌握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較為深入系統地考述了吐蕃與西北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這是該書的一大特色。
為了編寫該書,作者除了引用已經刊布的史料以外,還從《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新疆出土古藏文寫本》中挑選出一部分以前尚未翻譯過的古藏文契約、書信等,與研究古藏文文獻的專家一起進行翻譯和注釋,并將這些新鮮的史料引用于本書之中。此外,作者還引用了近年才出土或問世的文物資料,如《大唐天竺使出銘》《巴爾蒂斯坦的古藏文石刻》等,為該書的諸種嶄新論點從史料的角度作了支撐。
該書還大量采納中外學者研究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的諸多觀點,使本書更具系統性、包容性。國外學者托馬斯、戴密微、山口瑞鳳、烏瑞,以及國內學者王堯、周偉洲、巴桑旺堆、張云、陸離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在作者的書中有所引述。從這一點看,該書可謂是一部博采眾家之長又不乏自主觀點的嚴謹之作。
其次,《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關系史研究》一書,對學術界尚存的一些爭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考據和分析,得出了新的觀點。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該書在討論唐代吐蕃及其他民族的名稱、地望時,凡屬于記載模糊、不全的,或當前學術界存有爭議的,皆一一列舉,詳細考辨。比如,對“羊同”地望的考據就列舉了伯希和、杜奇、張琨、佐藤長、山口瑞鳳、周偉洲、霍巍、黃勝璋、張云等學者所持的不同觀點,其后以《大唐天竺使出銘》《釋迦方志》《通典》等為據,分析考證,最后才得出自己的觀點,認為:小羊同國在大羊同國東南,而大羊同國東接吐蕃;8世紀中葉以后,由于吐蕃的擴展,小羊同被遷到大羊同之西。
又如,對于敦煌藏文文書中常見的“mthong khyab”一詞,自日本學者山口瑞鳳將其譯為“通頰”之后,學術界并未對其深入研究。楊銘先生依據《賢者喜宴》《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通鑒考異》以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簡牘考證,“通頰”早先實為一種駐守唐蕃邊界的斥候軍,而后又移植于吐蕃統治下的河西走廊和南疆地區,演變成一種包含有多民族成分的部落組織。作者通過考證文獻,梳理線索,考證出吐蕃在河西走廊的涼州、甘州、沙州、瓜州和南疆的鄯善等地創設了多個通頰部落,其中包含有吐蕃人、漢人、粟特人、突厥人等。
總之,該書堅持實事求是、論從史出的方法,從縱橫兩個方面,客觀、真實地論述了唐代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歷史進程,以及雙方在軍事、經濟、文化諸多方面相互交流的概貌,并專題分析了吐蕃與西北民族交往的類型、歷史作用等。這無疑對推動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作出了貢獻。而該書設計的吐蕃與某族關系的開放式篇章結構,為作者日后對該書的修訂,以及其他學者的跟進或商榷提供了足夠的空間。
作者:西南民族大學預科教育學院講師
中國少數民族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