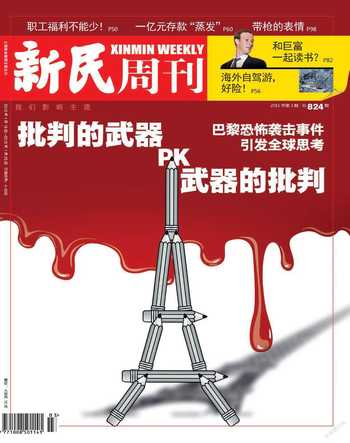關注7萬億投資效率
聶日明

據媒體報道,國務院于去年底已批準總投資額逾10萬億元的七大工程包基礎設施項目,其中今年將完成的投資超過7萬億元。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對此回應,“7萬億還是10萬億,是媒體自己推算的,具體投資額目前很難計算”,同時強調“這些投資并非強刺激,而是會引導社會資本積極參與投資”。
“7萬億”太容易讓人聯想了。2008年末,為了抵御經濟衰退風險,中央政府推出了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試圖挽救經濟,結果中央成功了。2009年投資對GDP的貢獻率高達87.6%,30年來最高,在1985年、1993年的高通脹年份,這一數值也不過80%和78%。而4萬億的后遺癥也是明顯的,眼下經濟處入“三期疊加”,其中“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正是2008年“4萬億”的遺產。
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上任以來,屢屢強調經濟轉型的重任在肩,政策以簡政放權、調整結構為要,甚至表態可以為經濟轉軌適當調低經濟增長預期。如今經濟增速下滑的壓力越來越大,決策者或許也意識到經濟增長的重要性,GDP的底線須臾不可放棄,自2014年年中,保增長的文件頻出,讓人看到了經濟政策有調頭轉向的可能。
目前看來,7萬億投資還不會重復4萬億的老路。首先,這7萬億并非額外新增的投資,額度在每年例行的新增固定資產投資總量之內,或許2015年的增速可能會高一些,但很難超越2009年高達30%的增幅。我們還要考慮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兩個重鎮(房地產與制造業)都面臨投資放緩的陰影,前者受困于樓市低迷,難現2009年、2013年的輝煌,后者背負著過剩產能的重壓,減杠桿都來不及,哪敢新增投資?
其次,“4萬億”的核心并非政府投資,而是寬松的貨幣政策。2009年的貨幣供應量增速高達28%,高增速的貨幣供應才是30%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的根源。雖然2015年的貨幣趨于寬松是大概率事件,但央行再怎么放水,也不太可能重現2009年的盛況。
與此相反,以《預算法》修訂案通過為標志,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央政府連下文件,清理整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規范融資渠道,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大部分業務不僅難以獲得過去政府信用的擔保,還要化解存量債務,逐步地置換、清理。這意味著以前地方政府借銀行、債市大舉融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也是發改委、財政部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參與7萬億投資的原因。
據發改委此前披露的消息,7萬億涉及到的“七大工程包”,指的是糧食水利、交通、生態環保、健康養老服務、信息電網油氣等重大網絡工程、清潔能源、油氣及礦產資源保障工程等。這些投資雖然不再局限于“鐵公基”等傳統基建項目,但仍然偏重于基建,針對生產性設施的投資偏少,投資回報率令人擔憂。
基礎設施與生產設施的投資存在最優比例,如果比例不當則會產生效率損失。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中國政府制定了一攬子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不僅幫助中國免受亞洲金融危機傳導效應的影響,進一步還加速了中國在接下來10年里的經濟增長(平均12.8%的人均GDP增長率)。但多年的基建投資已經讓中國的基建投資相對生產設施投資過剩,2009年因兩者錯配導致的GDP增速損失已經上升到1.05%。在這種情況下,更多基建投資的效率無疑更為低下。
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仍然很高。哪怕不增加資本與勞動力等要素,僅僅改善資本錯配與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可以保持可觀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前提是政府不應該再直接或者主導投資,避免把資金投向無效的領域。只是現實不容樂觀,雖然發改委、財政部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公私合營(PPP),以促進社會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或公用事業,但如果國有股掌控關鍵性、基礎性行業不改變,政府仍對企業投資行為有種種審批、限制,那么社會資本在投資活動中起到的只能是點綴作用,無法改進投資效率。
(作者為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