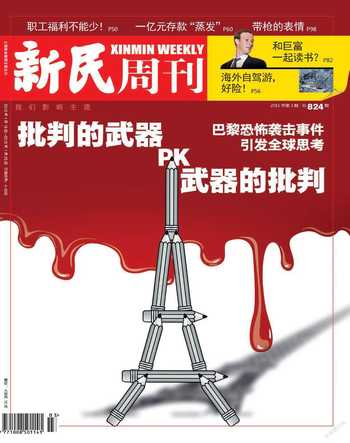遲子建:黑土地上的心靈史
何映宇


“寫到結尾那句‘一世界的鵝毛大雪,誰又能聽見誰的呼喚’,我的心是顫抖的。”她說。
素雅的封面,仿佛遠山淡影般的墨跡流過,一如她低調的為人。
從她的文字,就能讓你聞到濃濃的土地的氣息。
茅盾文學獎得主遲子建的長篇小說新作《群山之巔》亮相北京2015年全國圖書訂貨會。本書出版,距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額爾古納河右岸》已過去十年,距上一部廣受好評的《白雪烏鴉》也已有四年多。這次,遲子建再度將深情悲憫的目光投向中國北方蒼茫的“群山之巔”,講述在那里發生的勾人心魄的人間故事。
現在擔任黑龍江省作協主席的遲子建從小就生活在這片黑土地上。1964年的元宵節,她出生于中國最北端的漠河。之后,到大興安嶺師范學校學習,再入黑龍江作家協會工作至今,除了1987年在北京師范大學和魯迅文學院聯辦的研究生班讀書有過3年出省生活的經歷,她近半個世紀的人生,都與那片高緯度的山川平原合為一體。
高緯度地域的特征——寒冷、蒼茫、堅韌、厚實——已經深深地刻入了她的文本文體中,有女性的柔美細膩,更有蕭紅生死場般的近身搏殺的一擊即中,讓你感動。
自1985年發表作品開始,她已經完成了500多萬字的小說,包括5部長篇,其中,《額爾古納河右岸》為她贏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殊榮,也讓她成為中國不可忽視的作家之一。
在童年,北極村星星照耀的夜晚,她的外祖母會給她講的故事,往往也就是十多分鐘一個。這短暫的故事常常在她的腦海中翻騰不休。也許就是在那時候起,她開始夢想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吧。
最新的這部《群山之巔》,在《收獲》發表后就引起了廣泛關注,它比《額爾古納河右岸》更蒼茫雄渾,比《白雪烏鴉》更跌宕有致。在北方龍山之翼的龍盞鎮上,屠夫辛七雜、“小仙”安雪兒、執行死刑的法警安平、殯儀館理容師李素貞,以及繡娘、金素袖等一個個身世不同、性情迥異的小人物,在群山之巔的滾滾紅塵中浮沉,在詭異與未知的命運中尋找出路。“生活不是上帝的詩篇,而是凡人的歡笑和眼淚。”《群山之巔》中的眾多卑微的小人物,他們“懷揣著各自不同的傷殘的心,卻要努力活出人的樣子”。
這一首黑土地上飄揚的長短歌是遲子建人生的點滴感悟、片段悲喜,是大河中的一簇浪花、天河中一片漣漪,是這土地上的心靈史,在等待著你去發現與感動。
童年影響一生
《新民周刊》:1964年,你出生于中國最北的漠河,又長期在黑龍江省生活,念念不忘的是黑土地,是否有意地要用文字的方式來記錄這片土地上的人的生活史和心靈史?
遲子建:小說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作家心靈的折射。我生長在黑土地,熱愛它,所以我的筆觸更多地伸向了它。我還記得二十多年前在京求學時,每到寒暑假回家,列車穿過山海關,到了關外,你會感覺吹過來的風都是那么與眾不同,異常親切。
《新民周刊》:童年是否影響了你的一生?
遲子建:沒錯。我生長在大興安嶺,17歲以前,我都沒有坐過火車。除了在北極村,就是在森林深處的一個叫“永安”的小山村。壯闊的大自然,古樸的民風,以及那片凍土地發生的生與死的故事,對我影響很大。
《新民周刊》:蕭紅對你是否產生過特別大的影響?
遲子建:最初寫作時,我對蕭紅的作品讀得并不多,那時我更喜歡屠格涅夫和川端康成等作家,他們對我影響比較大。系統地讀了蕭紅作品后,覺得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她的《呼蘭河傳》、《商市街》、《牛車上》、《手》等作品,已是文學經典,我非常喜歡。她是我們黑土地上誕生的偉大作家。
《新民周刊》:謝冕在第二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獎”頒獎會上,對你的小說《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授獎詞:“向后退,退到最底層的人群中去,退向背負悲劇的邊緣者;向內轉,轉向人物最憂傷最脆弱的內心,甚至命運的背后。然后從那兒出發傾訴并控訴,這大概是遲子建近年來寫作的一種新的精神高度。”是否可以概括你近些年來的文學方向?
遲子建:其實從一開始,我的筆觸伸向的就是我熟悉的領地,而我熟悉的領地本來就在“底層”。只不過我早期的作品雖然伸向了“底層”,由于年輕,看問題不很深刻,呈現的風貌也就不那么大氣。而隨著閱歷的增長,寫作的深入,看到了人性的多面,寫作自然而然發生了變化。
《群山之巔》:用我的生命寫成
《新民周刊》:你最近出版了長篇小說《群山之巔》,據說寫作此書歷時兩年,其間兩度因劇烈眩暈而中斷。家人擔心你的健康,曾不許你再寫下去?
遲子建:是的,作為我來講,確實寫得很不容易,寫了兩年,這兩年身體不大好,確實有點嘔心瀝血的味道。《額爾古納河右岸》調動了我的才情和我多年生活的積累,《群山之巔》同樣如此。
《群山之巔》對我來說太重要了,這種重要性體現在哪里呢?我想讀者看過以后可能會有體會。一個寫當下生活與歷史有千絲萬縷糾葛的作品是一個挑戰,所幸我把它完成了。如果說它有什么優點?我想這里的每一個字,都用我的生命寫成。如果說它們是雪花,你們接到手里的立刻會化成一滴水,而你們感受到這一滴水其實都是一個作者用他的生活經歷,用他的藝術積累,點點滴滴擠出來的,也是流淌出來的,這里的甘苦不是三言兩語能夠說得清楚。
《新民周刊》:身體出現問題的話,會不會擔心有一天會寫不動?
遲子建:那倒不會。有的作家會擔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則沒有。因為到了《群山之巔》,進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納入筆下的生活,依然豐饒。雖說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別我而去,給我留下越來越多的白發,和越來越深的皺紋,但文學的春色,一直與我水乳交融。
《新民周刊》:你的小說,以文字優美、充滿詩意著稱,你覺得這是否與你的女性性別有關?這種文字之美,很大程度上來自漢語的文字之美,在翻譯文學和中國文學之間,你偏愛哪一類?
遲子建:也許與女性身份有關吧,女性更加感性一些。在翻譯文學和中國文學之間,我更偏愛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的古典文學,我至今依然喜歡讀古詩詞。《紅樓夢》、《聊齋志異》,也是常讀常新。翻譯小說看得也比較多,其中也有許多我喜歡的作家。也許因為我生長的地方與俄羅斯接壤的緣故吧,我更喜愛俄羅斯文學。那片深沉博大的土地上,誕生了一批文學巨匠。
《新民周刊》:很多讀者驚奇于你小說中的魔幻成分。
遲子建:因為都市人遠離了大自然,遠離了鄉村,對于那兒發生的人與自然的故事,一些人以為那是我虛構的,其實不然。我留意到有讀者認為我小說里的故事是虛構的,不相信有那么一個部落的存在,實際那是客觀存在,我還實地做了采訪。比如《額爾古納河右岸》里面寫到的薩滿給人治病體現出的那種神力,確實曾發生過,我幾乎沒用虛構,把他們放入了小說。我們看到的現實世界多姿多彩,我們看不到的鬼神世界光怪陸離,這兩個世界交織著,對我的寫作同等重要。
黑土地上短歌行
《新民周刊》:除了長篇,你在短篇小說方面也卓有建樹,之前你出版了4部短篇小說編年集,這是否涵蓋了你所有的短篇小說作品?選擇的標準是怎么樣的?
遲子建:我至今一共發表了大約百篇短篇小說,收入了69篇,還是篩掉了一些我個人覺得在藝術上比較幼稚和粗糙的作品。我一年大約寫兩三個短篇。我覺得好短篇,一年有一兩個足夠了。我選擇的標準是,在藝術上比較靠得住的作品。
《新民周刊》:你在這套編年的前言中列了很多短篇小說名家的名字,這些名家是否都是你特別喜歡的作家?
遲子建:我提到的那些短篇小說名家,確實都是我喜歡的作家。這些短篇名家風格不太一樣,帶給我的是不同的營養。契訶夫的深邃、川端康成的優美、普寧的憂郁,魯迅的犀利、杰克·倫敦的蒼茫,蒲松齡的詭譎,汪曾祺的閑適,總之,他們太不一樣了,但我都喜歡。
《新民周刊》:在中國當代文壇,愛寫短篇的小說家也不在少數,蘇童、余華、格非、莫言、張承志、史鐵生等等作家都寫過不少的中短篇,你對他們的中短篇小說怎么評價?
遲子建:你提到的這些作家,確實都寫過優秀的短篇。不過像莫言和張承志,他們的華彩篇章還是在中篇和長篇上。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命若琴弦》,我非常喜歡。你提到的蘇童、余華、格非,與我都是60年代生人,他們的短篇寫得確實很好,尤其是蘇童,他寫了許多經典的短篇。中國當代文壇還有一些短篇高手,而且直到現在每年都有好的短篇讓人眼前一亮,像王安憶、韓少功、畢飛宇、劉慶邦、葉彌等。
《新民周刊》:寫長篇要醞釀很多時間,那么寫中短篇的話,是不是就比較輕松自由?
遲子建:相對來說,寫長篇壓力更大,因為寫作時間漫長,對作家的心智也是一種考驗。但它也更具魅力,因為它提供給作家的空間很大。而寫短篇,慢的話,通常十天左右就完成了,你可以盡快地品嘗自己的勞動成果,確實讓人愉悅。但這并不是說,短篇給人的空間不大,其實它更鍛煉人,就是逼迫你做個好裁縫,懂得裁剪,不容許你說廢話。所以好的短篇,張力大,氣場足。
《新民周刊》:在這樣一個喧囂的時代,如何保持內心的寧靜?
遲子建:堅持自己的東西,不畏浮云遮望眼!還有,故鄉是我的精神根據地,我在黑龍江漠河出生長大,即使在哈爾濱生活,每年至少回去兩次。從童年到現在,我眼里裝的都是大自然的四時風景,而且我們那里,每年有半年是冬天,特別寒冷,那片土地給我的精神世界注入了一種強大的東西,我被大自然的風雪鞭打快半個世紀了,所以遭遇文學的寒流時,筋骨會強健。我對文學的追求,這種堅定,以及內心的寧靜,與這種成長環境也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