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偏“中西醫結合”
張墨寧
在尋找中醫的前途這條道路上,產生了很多口號。“中西醫結合”,“中醫現代化、國際化”,以及現在已經不太被強調的“中醫科學化”。總體來說,就是要使這一古老的醫療體系在今天仍然發揮價值,相關的產業具備國際競爭優勢。在各種構想和戰略并沒有取得共識的情況下,中醫與現代科學的拼湊關系發展了幾十年,問題也在不斷積累。今天,我們應該如何反思中西醫結合以及中醫現代化?本刊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陳其廣,2004年他開始擔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中醫典籍研究及英譯工程”秘書長,觸及中醫藥領域。2008年任中醫藥國情調研組執行組長,對中醫藥戰略多有研究。
《南風窗》:“中西醫結合”提出了半個多世紀,為什么很多人認為它在實踐中并不成功,“中西醫結合”的本意是什么?
陳其廣:這個問題是目前中醫藥發展方向一個關鍵性、根本性的問題。關于中西醫結合,其實有一個重大誤區,很多人包括中醫藥界人士在內,都認為這是黨和政府關于中醫藥工作的一個大政方針,這個認識其實是不正確的。如果說黨和國家關于中醫藥或者說整個國家的醫藥有一個最基本的大政方針的話,那應該是中西醫并重。中西醫并重是憲法早就規定了的,黨的十七大、十八大又反復強調。
那么中西醫結合究竟是怎么來的呢?新中國成立以前,一些領袖人物主要是出于統一戰線的考慮,從團結中西醫這個角度來講的。當時的“中西醫結合”,主要是說中西醫互相之間要有一個平等交往的局面,講的是一個政治上的問題。 這個口號到后來尤其是建國初期有一個轉變,從團結中西醫人員轉移到了中醫西醫在醫術上互相學習。
現在很多人尤其一些對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科技比較重視的人士持批評意見,首先是因為結合是一個模糊概念。從詞義學上來講,它可以有多種解釋,可以是聯合、配合、混合,也可以是融合。含義不清,各方理解不同,造成了今天對于中西醫結合有很多不同看法。現在一些權威人士也主張中西醫融合,但思想界是不認可的,專門研究醫學哲學的專家認為中醫藥和西醫藥的哲學基礎完全不同。因為哲學基礎不同,從而對生命健康疾病的本質認識,對疾病治療和養生防病的技術路線就有了不同的選擇。包括世界衛生組織、美國FDA也認為這是兩種醫學體系,他們認為現代醫學是對抗醫學,而把傳統醫藥尤其是中國和印度這樣一些有悠久歷史的傳統醫藥,稱之為整體醫學,或者叫完整醫學。所以說,思想界對融合也是反對的,從哲學上講,一個是對抗,一個是調和,沒有中間道路可走,不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比較權威的醫藥界人士包括一些院士都在反思,從100年以前有人提出來中西匯通,到建國初期放棄中西匯通提出中西醫結合的口號,直到現在,這個領域沒有獲得任何重大的理論成果。所謂的一些成果,多數都是在臨床應用層面,就是方法技能的配合。所以,他們認為結合是走不通的,如果要強調結合的話,今后的方向也應該是理論融合,包括把中醫藥的天地人理論和現代醫藥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式融合起來。我覺得這里面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到底誰是體,誰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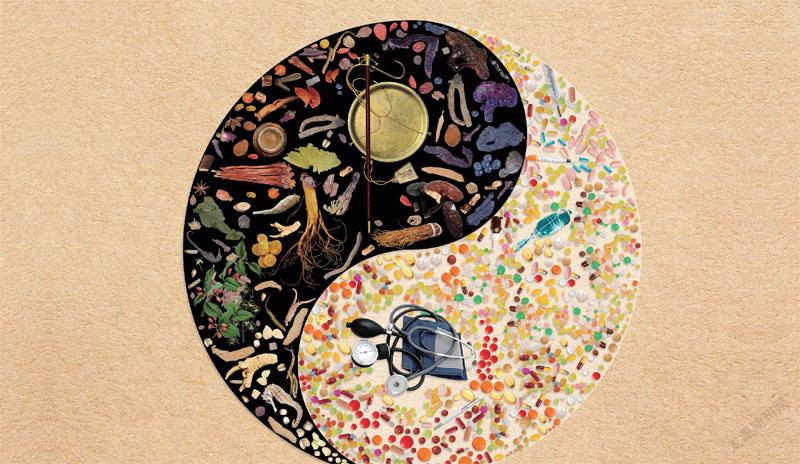
《南風窗》:反映在臨床、科研和教育模式上,“中西醫結合”指導思想構成了怎樣的中醫醫療現實?
陳其廣:近些年來的中西醫結合之所以不成功,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醫藥衛生服務一線的一些從業人員,并不是真正試圖從思想理論、方法技能上去努力探索結合特別是融合的可能性,而是把中西醫結合當成一個口號來掩飾醫藥界追求名利的實質。現在,國家的一些獎勵制度、技術職稱評定制度、科技成果認定制度都是偏向于用西醫西藥的思想和方法來做標準。這就是為什么搞中醫藥的人要費很大勁去做西醫藥的研究,中醫藥的碩士博士研究生要做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的研究,以顯示科研水平,這是制度上的一種引導。前不久還有中醫藥專家提出要搞轉基因中藥,中藥講的是溫熱寒涼,講的是性和味,科學沒有禁區,愿意試驗轉基因中藥也未嘗不可,但是從現實的角度來講,生產出一個轉基因中藥放到中藥材市場上去流通的時候,你相信會有人選擇轉基因中藥嗎?如果轉基因中藥改變了中藥的性味,它還能不能作為中藥來使用?
在臨床上,中醫講不清楚了就講西醫。現在有一個最大的誤區叫西醫檢查,中醫治病。有人認為這是中西醫結合的最好方式。我覺得這就錯了,所謂的西醫檢查,不是醫學手段,它是化學物理學和生物學手段。
所以,歸根結底還是我們沒有把中醫藥的特色優勢發揮放到醫藥衛生工作的重點上去,為什么世界上多數對醫藥管理比較規范的國家,對傳統醫藥和現代醫藥都是實行嚴格的分業管理?到底是失敗教訓還是成功經驗,我們應該去研究、參考。現在一講分業管理,很多公立醫藥衛生機構的朋友就來找我,說你千萬別再提這個事了,真要分業了,很多公立中醫院都活不下來。一家大型醫藥企業的領導也曾經跟我表示很擔心分業管理,西醫如果不能使用中藥處方藥的話,中醫藥的市場份額會受很大影響。一個利益格局已經形成了,要改變是很難的。
《南風窗》:中醫的存在也是比較尷尬的,民間派和中醫學院的學生是不是都很難找到一個足以讓他們發揮的從業環境?
陳其廣:民間沒有取得合法行醫資格但是確實能夠用中醫藥傳統方法來治病的,這樣的人數應該是不少于25萬人。幾乎一半的人被攔在合法行醫的大門外了。就是因為《職業醫師法》和《藥品管理法》,這兩個法規都是在現代化、科學化這個口號下制定的。
正規中醫院校的畢業生現在的處境也比較堪憂。一個中醫藥大學的畢業生沒有5年以上的單獨門診出診臨床應用經歷,不可能沉淀為基本合格的醫生。而西醫院校畢業的學生,兩年左右就可以獨立應診了。所以,中醫學院的學生更愿意中西醫結合,這樣他們的個人利益才有保障。中醫名家王新陸在山東中醫藥大學當校長的時候,曾經辦了全國第一個傳統中醫班,七年制本碩連讀。結果學生畢業的時候找工作,都不敢說自己是傳統中醫班畢業的。我在山西見過鄧鐵濤先生的一個博士生,他先是分到地區中醫院,工作兩年后,他覺得公立中醫院不是中醫藥人才成長的地方,選擇了辭職,自己出來辦一個小診所,靠自己的醫術口碑也生存下來了。
《南風窗》:拋開學術和文化爭論,中醫還應該被當作醫療體系中重要部分的現實原因是什么?
陳其廣:為什么現在醫改問題成為世界難題,就是因為現代西方醫藥是以最先進的現代物理學、化學、生物學作為支撐和基礎來發展的。當醫藥領域大量使用先進成果的時候,它也帶來了一個高成本的問題。醫改難題的本質就是大幅度增長的醫藥費用支撐不了了。無論采用何種支付方式,只要無法有效控制醫藥費用吹氣泡式的膨脹,現有醫保體系的各類支付主體都將難以承受持續增長的醫藥費用負擔。以美國為典型,用尖端的理化檢查設備、巨資研發的各類新藥和層出不窮的手術新方法作為技術支撐高成本“現代先進醫藥模式”,絕非當前乃至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所能承受的。美國也快支撐不了了,他們的人均醫療費是中國的40倍,大約8000美元左右。醫學本來應該是以人的健康為中心,世界衛生組織很明確這一點,但是為什么這么多年下來,包括國外也沒有很熱烈地響應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相應的轉變,要做重大的產業結構調整,要做重大的利益分配格局調整,它是有阻力的。
在中國,要建立持續穩固的醫藥衛生體系與國民健康保障體系,中醫藥必須是這兩個體系的戰略基石。國家統計部門的數據表明,中醫藥的人均費用比西藥至少低20%,住院也是低20%。有人就強調這個不可比,住院可能不可比,但是門診應該沒有大的區別。所以,甘肅衛計委提出了一個明確的口號,要走中醫特色的醫改道路,用最簡單的方法解決群眾最基本的問題,甘肅人均醫療費用只是全國平均水平的50%。這對我們今天的醫改是一個啟發。
另外,從國際制造業競爭力來看,醫藥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而中國現在臨床使用的西藥,95%都是發達國家醫藥企業專利保護過期的仿制藥物,70%左右的醫療器械知識產權也不在我們手里。所以,只有更好地利用中醫藥,我們的國民健康保障體、醫藥衛生服務體系,才有可能比較持續、穩定地運行下去。

《南風窗》:對中藥現代化戰略的批評現在也比較多,眾多部門、行業,尤其是植化、化工、生物技術、西藥等,都在大搞中藥現代化,這種風潮的形成是怎么形成的,中藥的現代化研究中,是不是也出現了方向偏差?
陳其廣:西藥的主流是人工化學合成藥物,在臨床使用過程當中,西藥界的人士越來越認識到它的局限性。比如說耐藥性、毒副作用。所以,世界醫藥行業有兩個重大轉向,一個是更加關注植物化學藥的研發,另一個就是從一般意義上的藥物治療轉向所謂的高科技比如干細胞、基因技術。但是后者在國外的應用非常謹慎,比較明顯的轉折就是植物化學藥。現在世界上幾個領先的醫藥跨國企業,在中國都有研發中心。就是要利用中醫中藥的豐富歷史積累,在研究植物化學藥上盡快取得成果。
屠呦呦得獎之后,一些人說這個也是中藥,醫藥界之外的人像方舟子認為這跟中藥沒有任何關系。我覺得這兩種觀點都有它的問題,青蒿素離開中藥的積累是不可能產生的,否則怎么能在12000多種植物藥材中關注到青蒿呢?但是她用的方法是植物化學藥的方法,非要說是中藥也就不客觀了。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中藥藥材都可以按照西藥的這個方法來研發,結論肯定是否定的。不是每一種藥材都可以用化學方法提取某種單體物質,然后明確肯定它對治療某種病有直接作用。另外,現在世界公認的是,研究一個能夠治療全球范圍內重大疾病的藥物需要3個“十”,10億美元,10年時間,10%的成功概率。青蒿素之所以能躋身于這個行列,就是因為它利用了中醫藥的豐厚歷史積累,走了一條捷徑。即便如此,青蒿素的研發當時也是舉國之力。
從人工化學合成藥物向植物化學藥、生物制劑、細胞基因醫學發展是當前世界醫藥范圍內一種技術路線和方向的變化。中醫藥界的人反應最強烈,但事實上這種變化挑戰的不僅僅是中醫藥,更是我們整個國家的醫藥界。
《南風窗》:中藥界對屠呦呦的獲獎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認為這是對傳統中醫的傷害,這種說法是不是極端?現在的中醫藥研發方向,對傳統中醫的存亡是否構成威脅?
陳其廣:我覺得如果過分強調中醫藥研發的成功意義和價值,特別是如果管理部門把它作為一種標準模式來要求整個中醫藥行業的話,是會造成傷害的。在繼承與創新之間,我們必須擺正一個關系,沒有繼承就沒有創新。現在對中醫藥界來講,更大的危機不是在創新,而是在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