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為誰而生?
孫偉鋒
《錢商》
阿瑟·黑利 (Arthur Hailey) 著
陸谷孫、張增健、翟象俊 譯
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6月版
阿瑟·黑利創作的小說《錢商》雖以上世紀70年代的美國銀行業為背景,但其中不少橋段,諸如濫發信用卡、信用卡詐騙、大銀行的勢利、銀行規避社會責任、銀行高管的貪腐,對于40年后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頗具鏡鑒意義。
作為行業小說,阿瑟·黑利在《錢商》創作上下的苦功絲毫不遜于現代作家茅盾創作的《子夜》—前者在銀行作了艱辛的蹲點調研,后者對證券交易所的運作作了深入研究。區別在于編劇出身的阿瑟·黑利過于強調緊湊、密集的戲劇沖突,這阻礙了《錢商》無法具有史詩性力作理應具備的宏大格局。這既是阿瑟·黑利行業小說的暢銷書定位使然,也揭示了其無法躋身偉大小說的根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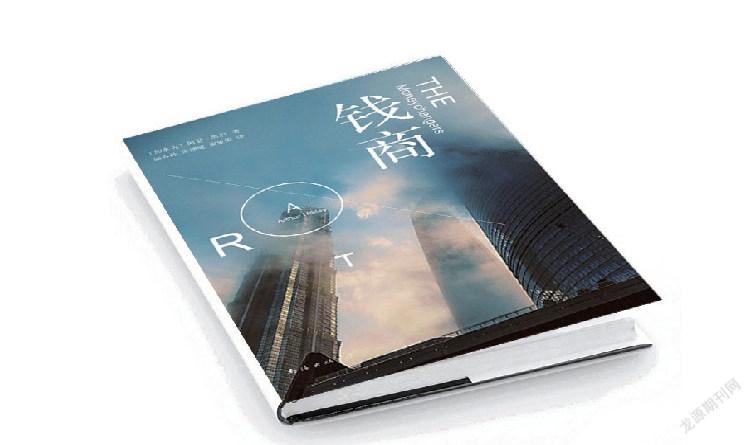
作為一家上市的家族企業,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遭遇的危機不啻當下中國銀行業的注腳,由此也衍生出了更具根本性的問題:銀行為誰而生?
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創始人的孫子、現任總裁班·羅塞利已是肺癌晚期,其子在二戰中喪生,孫子死于越戰,這讓現任總裁繼承人的課題提上了議事日程。總裁在經營戰略上的價值取向直接影響銀行的運營理念,這也正是小說中人物性格沖突乃至小說戲劇性的來源—在總裁候選人、副總經理羅斯科·海沃德看來,銀行為利潤而生。為實現利潤最大化,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應該著力于服務超國公司(作者在公司取名上煞費苦心)這類的大客戶,至于小微企業、東城新區改造項目這類利潤微薄甚至帶有公益性質的業務應該避之唯恐不及。在另一位總裁候選人、副總經理亞歷克斯·范德沃特看來,銀行不應對超國公司這樣的財閥趨之若鶩,小微企業乃至舊城改造貸款才是銀行理應關注的利潤源泉。一言以蔽之,羅斯科和亞歷克斯作為下一任總裁的競爭對手,庶幾代表了金融資本在價值取向上的分歧:前者重視上層,后者注重草根。
羅斯科在以財閥企業為代表的大客戶爭取上體現出的目光短淺、急功近利和唯利是圖,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當前的國內銀行業—一方面,具備創新理念的小微企業融資無門以至于求助地下錢莊;另一方面,大財閥視銀行風控制度如無物,在貸款申請上所向披靡。更可怕的是,財閥之所以成為財閥,是因為其可以成功操控各種社會資源為其作信用背書。
從小說中看來,不僅是羅斯科這樣的金融巨子,還是美國副總統這樣的政界強人,都成為超國公司總裁夸特梅因的座上賓。為實現和金融資本的聯姻,夸特梅因不惜向羅斯科贈送超國子公司的股權甚至情婦,將羅斯科從好友晉級為利益攸關者,進而借此綁架銀行貸款。可以預料的是,如果副總統旨在救助超國公司的提案在國會通過,會有更多的股民為“大到不能倒”的上市財閥買單,遑論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橫跨金融資本、政界人脈的既得利益財閥集團就是這么形成的(正如艾森豪威爾提及的“軍事-工業聯合體”),這也是對于當下中國最具有警示意義的所在。
與之相對的是亞歷克斯為代表的銀行改革派。在今天看來,被70年代的美國視為銀行創新的自動柜員機不啻明日黃花,但有些橋段可謂日久彌新:為履行社會責任,亞歷克斯主張銀行積極參與東城新區抵押貸款的民生項目;為整治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的“大企業病”,亞歷克斯將分行下沉至社區;為創造穩定且可持續的利潤增長點,亞歷克斯號召銀行為小微企業雪中送炭。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馬克思看來,資本無疑是原罪的,銀行作為金融資本亦不例外。但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制度安排,本身也在不斷進化,這使得金融資本從原始積累階段的叢林人屬性(譬如《威尼斯商人》中的高利貸者夏洛克)不斷向成熟階段的社會人屬性轉變,正如小說中美利堅第一商業銀行創始人的那句名言—“要真正賺錢,我們必須不僅要有所得,而且還要有所失”,這句金玉良言同樣適用于中國的銀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