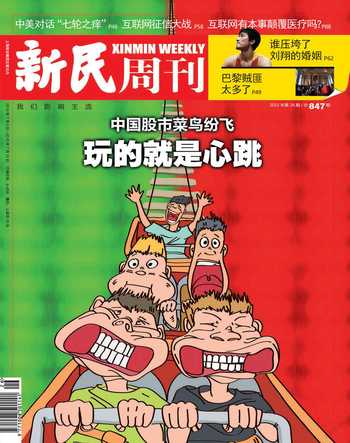美國同性婚姻合法: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
陳晟
這幾天,估計大家的朋友圈都被各種彩虹色的新聞刷屏了吧?雖然美國不是第一個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國家,但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卻讓這個超級大國邁出了巨大一步,對于各國彩虹人群的意義都非常重要。毫無疑問,它將會和聯邦法院諸多著名的判決一樣被載入史冊,為后世的歷史、法律研究者所津津樂道。
然而,同樣是這個判決,又多少顯得有些無奈:5:4的投票結果,意味著只要5位大法官中僅需一人改變主意,判決就會截然不同。而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閣下的異議意見,也表明了至少有一部分美國人是反對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因此,一個問題就值得拿來思考一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裁決,究竟是歷史的必然呢,還是幾位大法官一時興起的偶然選擇?
何為婚姻?
要討論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婚姻是什么”。而這一問題,也正是這次爭議的焦點。
在這次判決書中,大法官們以相當詩性的語言給出了定義:“沒有一種結合比婚姻更加深刻,因為婚姻象征了對愛情忠貞、奉獻、犧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通過組建婚姻關系,兩人都比曾經的自己更加偉大,就像本案中的一些請愿者所證明的一樣,婚姻象征著一份甚至超越死亡的永恒的愛。婚姻的本質是,通過雙方持久的紐帶,兩個人能夠一起找到其他類型的自由,比如表達,親密還有精神上的。無論他們的性取向如何,這些對于所有的人都是合適的。說這些男人和女人們不尊重婚姻的意義,將是一種誤解。相反,他們的情緣表示了他們不僅真的尊重婚姻,更尊重到渴望尋求婚姻來獲得自身的圓滿。他們的愿望不應該被責難,而使他們孤獨終老,或被人類文明最古老的制度排斥在外。他們向法律尋求平等的尊嚴,而憲法也賦予他們這份權利。”

相反,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對于“婚姻”則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抨擊說,“最高院宣布超過半數州的婚姻法無效,強制性地改變了一個數百萬年來形成人類社會基礎的社會制度,一個南非布須曼人,中國漢人,迦太基人,阿茲特克人通行的社會制度。我們到底把自己當成誰了?”
那么,讓我們回溯歷史長河,看看婚姻之于人類社會,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流變?
通說認為,在上古時期普遍存在著一種“搶婚”的傳統,或者用更直白的話說就是強奸和綁架:青年男子帶上幾個伙伴,將其他部族的漂亮女子用暴力擄走,然后強迫其成為自己的妻子。這種傳統,在今天的絕大多數地區已經蕩然無存,但在希臘神話中還能見到其遺跡(比如冥王哈迪斯搶走了普洛塞庇娜);而在罕見的情況下,比如“伊斯蘭國”(IS)控制下的地區,依然有將異族女子搶來作為戰利品分配的惡習。
隨著歷史的發展,婚姻變得稍微文明了一些,但實質依然是不需要獲得婚姻當事人(特別是女方)的同意,僅需要其父母、監護人點頭,婚姻即可成立——或者說更像是談成了一樁買賣。無論是我國古代的“三書六禮”還是歐洲古代的“保護人”制度,看似繁瑣嚴密的婚姻制度所掩蓋的不過是雙方對于物質條件的考量,以及對于婚姻當事人情感、權益的漠視。即便今日,這種狀況還存在于一些落后地區,比如印度的婚姻,就受到了種姓制度的干擾,討取高額嫁妝的習俗也讓婚姻沾染了濃厚的銅臭味。

2015年6月26日,美國好萊塢,支持者慶祝同性伴侶有權在全美50個州結婚。
此外,歷史上有許多地區的婚姻在伴侶人數上是不平等的:男子可以和多名女子同時締結婚約(如我國古代的妻妾制度),而女子則無一例外被規定只能對一名男子忠誠,如果稍有出軌行為則會遭到殘酷的懲罰,甚至為了避免這種風險,人為的限制其日常活動的范圍(如裹小腳、戴面紗等等);一些地區甚至認為女子可以被作為遺產而在兄弟間進行繼承,認為丈夫死后女子有殉葬的道德義務,徹底的物化了女性。
不僅結婚如此,離婚也經歷了各種奇怪的歷程。在歐洲的一些地區,曾經明確禁止離婚,因為按照宗教上的解釋,“神作之和,人不得離之”,所以不得不搞出了“分居”這種變通的模式。而在中國,離婚的權力僅限于男方所有,所謂的“七出”賦予了男性相當大的特權,即便是以“三不去”加以抗衡,也改變不了婚姻中女性一方的實質性弱勢地位。
直到進入了20世紀,這些不合理的規定才在世界各國的法律中漸漸消除,當事男女雙方被賦予了婚姻自主權,只需要聽從自己內心的召喚,無需再獲得其他人的認可就能決定結婚和離婚,讓婚姻復歸于人性的范疇,剝離了附麗其上的宗教、宗族和階層的內容。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壓根就不存在著一種跨越了時空、伴隨著人類文明史而歷久不衰的婚姻制度。相反,正是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人類不斷地摸索著最適合自身、最能體現個人主體意志的婚姻制度,讓婚姻服務于人,而非讓人類充當婚姻制度的演員。
從這個意義上說,羅伯茨大法官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人類的婚姻制度一直沒有停止過演進。即便是聯邦最高法院,實際上也充當了這種演進中的助推器,如著名的“弗吉尼亞州訴洛文案”(當時弗吉尼亞州的法律禁止黑人和白人結婚,否則視為犯罪行為;聯邦最高法院于1958年做出裁決,認定該法律無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此,當現有的法律并不能符合民眾的期待,不再體現民眾的意志時,完全應該對其做出修訂,比如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問題;而本次聯邦最高法院的裁決,正是回應了民眾的呼吁,所謂正當其時,并非5位大法官個人意志專斷的結果。
實際上,美國的同性婚姻合法化運動,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經過了漫長的爭取,包括一系列的訴訟與裁決。更重要的是,許許多多公眾人物的表態,對于同性婚姻的正當性、合理性有了極大的幫助。曾幾何時,同性性行為被視為一種犯罪,或是一種精神上的疾病,即便是將其非罪化之后,它依然被視為是一種不名譽的、見不得光的行為,至少聽起來沒有異性性行為那么順理成章、理所應當。
但是,隨著一個個公眾人物的出柜,社會輿論也開始了潛移默化的轉變,漸漸地發現了同性性行為并沒有那么罕見,不那么古怪,更沒有必要將其妖魔化。比如社交媒體“臉譜”的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CNN名嘴安德森·庫珀、“甘道夫”的扮演者伊恩以及蘋果公司的現任老大庫克,他們公開了自己的性取向,不僅獲得了公眾的尊重與支持,也一次次地抨擊著“同性婚姻不受祝福”的堅冰,給彩虹群體做出了榜樣,讓更多的同志坦白自己的取向,使得美國社會也開始正視這個并不算很小眾群體的合理訴求,最終形成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洪流。
回想一下,從圖靈到勞倫斯,無論最終的判決是否有利于彩虹人群,對于公眾而言都是一個討論與思考的契機,漸漸地產生了從“同性性行為并不應該為法律譴責”到“同性婚姻也應該得到法律的保護”的躍遷,為今日的法律裁決打下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對于同性婚姻的合理認識也是如此。當美國的同志群體在興奮的揮舞彩虹旗時,似乎不應該忘記這些為了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付出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說,聯邦法院的判決也不像是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水到渠成、順應民意的結果。
該不該管?
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反對該判決的另一個理由,是此事根本不該由最高法院接手,而應該由立法者——也就是美國國會,通過修改、制定法律的做法加以解決,這個判決實質上是越權了。
在美國的法制史上,“馬伯里訴麥迪遜案”家喻戶曉,從中不難看出聯邦最高法院對于自身權力的謹慎和謙虛,輕易不愿代替國會和總統作出裁決。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美國的立法程序相當冗長,往往還受制于兩黨意見的分歧而久拖不決,一個法案從醞釀到總統簽署,花個幾年時間是相當正常的事情。


2015年6月28日,美國舊金山,民眾參加年度同性戀大游行。
但是,美國同性婚姻合法性的問題卻已經是迫在眉睫,沒時間再等下去了。美國已經出現過同性伴侶因為不能繼承遺產而入稟法院的案例,更多的彩虹團體還在遭遇著人身、財產上的歧視待遇(如不能以配偶身份獲得綠卡,不能在繳稅時以家庭為單位計算扣除等等),讓他們繼續等待遙遙無期的國會立法,似乎太過殘忍。“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從這一點上說,美國聯邦法院擔負起修正法律規定的重任是最佳的選擇。
再者,聯邦最高法院在歷史上多次舉起社會變革的大旗,在諸如消除種族隔離、保護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權、保護爆料者的身份安全等等重大事件上,都起到了鳴笛的作用并且得到了歷史的肯定與贊許。盡管的確有超越立法機關權力的可能,但總體效果依然是非常正面的。
所謂當仁不讓,讓聯邦最高法院來充當改革的破冰船,并無不妥。
從媒體的反饋上看,目前美國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民眾,對于這個判決都是相當贊賞的,無論是同性戀群體還是異性戀群體。
但是,這一判決也還是遭到了一些批評的聲音,不僅來自認為“同性婚姻有違傳統價值觀”的保守派群體,也來自觀念更為超前的新興人類們。
具體而言,在本判決書中,多數派的大法官們的論證邏輯是:婚姻是具有各種美好的價值的;同性婚姻并不會妨礙這些價值實現;彩虹人群也有權利獲得同等的婚姻價值,所以同性婚姻應當合法化。這種邏輯本身并無漏洞,從理論的角度論證了改判決的依據與價值觀。
然而,這樣一來,實質上就隱含的否定了另一個小眾的群體:單身者和不婚人士。
正如“和誰結婚”是雙方當事人自由選擇的結果一樣,“要不要結婚”當然也是每個社會成員得自主決定的事情,他人無權干涉。但是,在這個判決書中,用華麗而熱情的語言謳歌了婚姻的價值,全然不提婚姻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家庭內吵架甚至家庭暴力、個人時間碎片化與職業機會的損失、個人生活習慣的被迫改變等等),實際上還是將價值觀強加于人,只不過是從“一男一女才能結婚”變成了“無論是男是女,都應該結婚”,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實際上,隨著時代的進步,婚姻的社會職能一直在被弱化。比如,我們不再認為男女雙方應當承擔不同的家庭職能(男主外女主內),不再認為婚姻就應該產生下一代,也不再把不婚人士視為怪物。但是,不知不覺中,社會輿論對于他們依然存在著深深的敵意,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有一種隱藏的自卑——恰好就像是當年的彩虹人群所遭遇的歧視。“女漢子”、“剩女”和自嘲時的“單身狗”,這些稱謂都反映了這種價值取向。在本次判決書公布之后,似乎更會為這種歧視暗暗添上一段背書,這是一種很不好的暗示。
從整體上看,聯邦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順應了民眾的呼聲,也代表了歷史發展的一種必然趨勢,并非僅是機緣巧合的產物。當然,它背后的說理邏輯未必那么嚴密和完美,但這一步對于彩虹群體、對于公民權利的平等都有著相當積極的作用,更是讓“人”的自主選擇成為了婚姻最重要的基石,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
展望未來,相信會有更多的國家對同性婚姻問題展開嚴肅的討論,基于本國的社會發展實際而做出解答,讓婚姻的價值復歸于人性和感情,讓每一位民眾的正當權益都得到法律的保護與祝福,讓彩虹旗更加驕傲地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