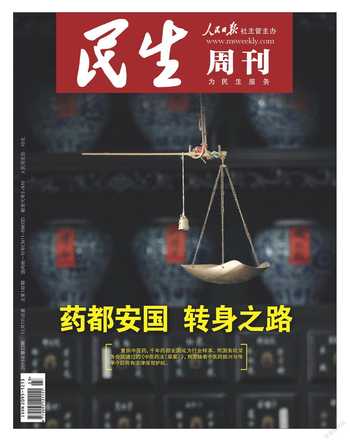合作辦學:平均3天誕生一個項目
李劍平
一些人故意混淆政策界線,把涉外辦學活動換成“中外合作辦學”旗號進行招生。有關方面再也不能用撒胡椒面的策略,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路。
既不屬公辦大學,又不是民辦高校,中外合作辦學在國內面臨尷尬,但這并不影響其迅速成長為國內第三支辦學大軍。
1995年,全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項目只有71家,20年后的今天已達到2371家,在校生總數約56萬人。其中,中外合作辦學機構200個,本科及本科以上法人設置的10個、非法人設置的57個(含籌建的天津茱莉亞學院),高職高專近30個,高等教育階段在校生約46萬人、畢業生總數超過160萬人。
“20年間,平均3天就誕生一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廈門大學中外合作辦學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輝在第六屆中外合作辦學年會上追問,穩定規模增長的機制、質量保障的體制去哪兒了?
連鎖店化趨勢
很多人誤認為,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就是外國大學的在華分校。美國肯恩大學常務副校長菲利普·康納利明確表示,這些學校并不是在中國的分校,而是一個自我運行的機構。
外國教育資質的有效性,跨境教育機構頒發證書的合法性,學生的檔案、注冊情況等都關乎學生的切身利益。教育部學位中心評估處處長林夢泉深刻感受到,國內在這些方面應該做更多、更細致的信息披露。
有關方面在對中外教育政策、體系不了解的情況下,合作辦學的積極性非常高。有關人士向記者透露,2010年以前,國家對中外合作辦學每年集中審批一次;從2011年開始分上半年、下半年各審批一次。每次獲得批準的數量約為受理數量的36%~50%,且很多是申報相同、相近的學科專業。
以本科及本科以上57個非法人設置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為例,大部分為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工商管理、會計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等辦學成本低、市場效益好的專業;有的高校為解決財政困難,盲目聯姻,一哄而上開設專業。
某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向教育行政部門申報環境資源、經濟學、法律、數學、大氣等5個不相關的專業,根本不符合審批標準被退回。中方校長向教育行政部門解釋,他們引進外方資源是要培養“復合型大氣人才”,最后獲得批準。
這令中外合作辦學的一些準入原則與要求形同虛設,很多報上去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都在打“擦邊球”。某科技大學校長只與外方校長禮節性地對接了一下,教務、財務、人事等部門都沒有對接,該校國際處就弄了一個中外合作辦學方案報給教育部門審批。甚至,出現過不同省份、學校、專業的中外合作辦學協議雷同問題。
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成為中外合作辦學的“前三強”教育輸出國。有關人士說,澳大利亞有所學校在中國境內辦了40多個合作項目,美國某大學在我國有10多個合作項目,中外合作辦學出現連鎖店化的趨勢。
南方一所大學國際學院院長說出了其中的奧秘,每名學生每年收費7萬元,1000多名學生規模,合作辦學初始階段,外方拿70%,中方只有30%;正常運轉后,中外雙方各拿50%,還有一些業務費與提成歸學院支配。
由于有著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另一所具有5000多人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的副校長表示,他們每年都往物價部門跑,要求上漲學費,今年總算如愿以償對每名學生的收費上漲到8萬元/年。這還算低的,有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對學生的收費達到10萬元/年,甚至40萬元~60萬元/年。
西部一所本科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主要以專科生為主,就是用中外合作辦學的牌子同獨立學院、民辦本科高校爭搶生源。東部一所師范大學的副校長透露,地方政府投資10億元,與該校舉辦一所以商科與創意設計為主題的國際學院。
那么,中外合作辦學在現有的規模與體量上,還有沒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林金輝表示,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這個指標在2014年就達到了37.5%,預計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45%。多出的5%主要用在高職高專的擴張與中外合作辦學。
現實的情況是,一些高職高專院校生源不足,很大一部分都會跑到中外合作辦學一邊。同時,還有一批高校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正在盤活存量,騰籠換鳥。
江蘇省的有關調查顯示,40%有出國留學愿意的學生會選擇留在國內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林金輝說,“中外合作辦學規模擴張上去了,要在陽光底下運作,不能盲人摸象,創新質量、提升內涵才是關鍵。”
人才培養成空洞口號
浙江師范大學副校長樓世洲表示,浙江省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從整體上看基礎還不夠,學科分布不能滿足現代教育發展的需要。浙江有寧波諾丁漢大學、溫州肯恩大學等兩所中外合作大學,對國內中外合作辦學的探索有一定影響,不過在滿足和服務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山東某大學國際處工作人員介紹,教育部對中外合作辦學要求,引進的外方課程和專業核心課程應當占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全部課程和核心課程的1/3以上,外國教育機構教師擔負的專業核心課程的門數和教學時數,應當占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全部課程和全部教學時數的1/3以上等指標,在實踐過程中大部分機構、項目都達不到。為在數字上做文章、湊課時,他們把外方教師教學的64學時會計課一分為二地變成“會計1”、“會計2”。
現在,中外合作辦學招收學生的高考分數一降再降,有一些課程講到一半時學生根本聽不懂,老師講下去沒什么作用與意義。部分在中外合作辦學一線工作的教授表示,他們很難自始至終主持某一門專業課的教學。
中外合作辦學項目有的高校歸教務處管,有的由國際處領導,還有的專設國際學院。來自吉林大學人文學院的一位教授說,澳洲的本科一般為3年,北美的本科是4年,有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英語課時就好幾千個學時,有的英語課、國際課加起來有50門課程,遠遠超過國內普通本科高校學生的學習能力與課時;有的頒發境外大學證書、學位,有的只能取得中方高校畢業證與學位證,還有的是拿中外雙證書。有關方面應該盡快把分類引導、分類管理等落到實處。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負責人表示,第一種是獲頒國(境)外學歷證書學生注冊,第二種是中外合作辦學學歷學位認證。國家的新政策要求是,所有境外證書的學生在當年入學之初,對學生相關信息進行注冊,畢業后其學歷學位才能認證通過。現在國家與地方教育行政部門的一部分精力是在維護和保障2012年前后一些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沒有經過審批招生的學生權益。
據權威專家透露,實際上,很多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的精力是在維護學生權益,確保他們不在學校鬧事;防止二級學院不能對學費收入截留與抽成,至于質量保障則是排在最末位考慮的事,使人才培養目標成為一句空洞的口號。
“阿聯酋、中國,正成為全球最大的教育輸入國之一。”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跨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金賽·凱文說,這種模式正在受到一些質疑與挑戰。首先,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沒有納入外方校本部的管理體系,在教育輸出國沒有相應的法律保護地位,更多的是從商業角度考慮。
其次,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所招收學生的素質不如在教育輸出國招收學生的素質高,再加上是當地人管理為主,體系不健全,沒有足夠的監控,容易形成各種誤解,難以達到輸出國校本部畢業生的學術造詣與水準。
再次,把國外的模式作為舶來品強加給本地,其合作的地位存在不確定性。
防止政績工程、面子工程
作為第六屆中外合作辦學年會的主持人,林金輝說,國內中外合作辦學有師資、教學、質量、規模、效益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需要解決,2003年公布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一些規定,已經不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需要。一些人故意混淆政策界線,把涉外辦學活動換成“中外合作辦學”旗號進行招生。有關方面再也不能用撒胡椒面的策略,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老路,必須把工作重點直面火熱的中外合作辦學,把質量建設提到綜合改革的高度加以推進,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也要及時跟上。
上海紐約大學成立3年多來,經常面臨“為什么要辦這所大學”的問題,校長俞立中說,中外合作辦學不是復制一種商業模式,多了一個合作伙伴,用了國外大學的名字與學位,而是借鑒一種辦學模式,立足教育與人才培養,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如果這個目的失去了,中外合作辦學就會走形,很難辦出高水平大學;如果不在辦學模式、特色與質量方面下功夫,也辜負了國家的期待。
教育部原副部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會長章新勝介紹,美國紐約州引進教育資源的3個原則為,第一必須是紐約州缺乏的,第二必須為優質的教育資源,第三是通過審核。歐盟28個成員國中,軍事防衛權都可以共享,教育權絕對不讓。“現在大學成為各個國家競爭的工具。”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白杰瑞認為,這些值得我們在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深入思考。
廣東省教育廳交流合作處處長馮興雷表示,10多年來,國際經濟社會發生很大變化,我們對中外合作辦學沒有進行很好的總結與反思,體制、機制是否有利于中外合作辦學,政策上還缺少什么,能否適應這個發展趨勢。
關于這個問題,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副主任車偉民也表達了憂慮。他說,我們現存的中外合作辦學的立法、法律法規能不能應對國際跨境教育迅猛發展帶來的一些沖擊,我們的執法和審批流程是不是科學合理,能否滿足中外院校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的愿意。中外合作辦學者是不是做到依法辦學,保證質量,培養出高質量的國際化人才。
教育部國際合作與交流司有關負責人回應相關問題時說,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個別地方和機構辦學目的不端正,一些中介機構參與、包辦,嚴重影響了中外合作辦學的社會形象,一些長期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在新時期沒有根本解決,中外合作辦學過程中還出現一系列新問題。
據了解,教育部將嚴把教育資源入口關,嚴格控制舉辦中外合作大學,依法從嚴審核;要求舉辦中外合作大學要納入省級人民政府高等學校設置規劃,堅決防止出現政績工程、面子工程;要強強聯合,典型示范,貫徹“管辦評分離”原則,真正引進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