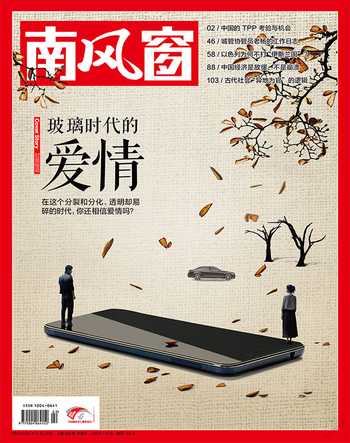5小時,“重啟”廣州
李少威
對于廣州人而言,臺風向來不是壞事。這座超級城市位于珠三角北部,臺風抵達的時候,風力早已衰弱,剩下的就是一陣雨中的清涼。
這次不一樣。
10月4日下午5點左右,臺風“彩虹”抵達,但送來的不是七彩的心情,而是一次廣州23年來最大規模的停電。番禺、海珠等區域,40.9萬戶用電戶斷電,超過100萬人受影響。
電量仍然充足的手機,開始向微信朋友圈散發抱怨與期待。5個小時后,電來了,“彩虹”才在人的情緒里回歸。
人們不知道的是,這5個小時里,廣州供電人,展開了一場摸黑進行的戰斗,經受了影響廣州人生活的一次歷史考驗。
“彩虹”在10月4日下午17時左右抵達廣州,首先與它邂逅的,是南部的番禺、海珠。
它在行進過程中發生了一點凌厲的變化。臺風外圍冷熱空氣對沖,形成了小范圍的龍卷風。龍卷風改變了力的作用方式,意味著“彩虹”將不似以往的臺風那般溫柔。
真正的問題在于,這股小范圍的龍卷風,經過了一個最不應該經過的地方—廣南變電站—這是一個500千伏的變電站。
發電廠發出來的電送到廣州,先要把電壓提高,變為高壓電,抵達用戶附近,再按需要把電壓逐級降低。
500千伏是超高壓電,廣州地區一共只有6個500千伏的超高壓變電站,其中中心城區有4個。一個500千伏變電站,就是一張蛛網的中心,如果它出現故障,那么整張蛛網都會停電。
現在龍卷風向其中的一個撲了過去。
龍卷風是個不友好的大力神,它能把什么都舉到空中去。這次它舉著的有七八米長的鐵皮,還有一床床濕漉漉的棉被,還有一些衣服、塑料制品。
鐵皮、棉被、衣服、塑料,都掛在了高壓線上,有的同時掛上兩條高壓線,于是,強大的電流沖擊下導致短路。
廣州供電局局長甘霖說:“最高的沖擊電流我看了記錄,幾乎達到4萬安培。”
可以這樣迂回理解“4萬安培”這一數字:一般臺式電腦電流大約1.5安培。
一瞬間,保護開關跳閘,廣南變電站全站失壓,波及供電區域內5個220千伏站失壓,14個110千伏變電站失壓。
40.9萬戶用電戶失去了色彩。夜色跟著上來,做飯、看電視、逛街、煮咖啡……都停止了。
災難降臨的聲音是這樣的:“突然聽到一陣很大聲音,就像是火車呼呼地開過。”
這是廣南站站長詹鐘濤的描述,這讓人想起詩人艾略特的句子:“世界轟然倒塌,不是砰的一聲,而是噓的一聲……”。
隨后他的電話就響了。“廣南站全站失壓!”
這個久經戰陣的電力行家吃了一驚,全站失壓是此前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電話馬上響起來的遠不止詹鐘濤一個,一名深知500千伏變電站全站失壓老員工說,聽到消息時電話幾乎掉在地上。
大面積的停電導致了什么結果?番禺、海珠區大批街道社區同時停水,交通燈失靈,停車場擁堵,“爆炸”謠言滋生。還可能導致什么結果?恐慌情緒進一步蔓延,人們的生命財產面臨危險,社會不確定因素積聚……
普通人可以很容易理解的一個例子是,停電區域內有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孫逸仙醫院,搶救、手術以及各種機器的運轉,備用電力所能堅持的時間有限。
所以,時間最為寶貴。
甘霖局長一邊趕赴廣南變電站,一邊打電話聽取南方電網公司董事長趙建國、總經理曹志安、副總經理王良友的指示。當他6點鐘抵達廣南變電站現場時,立即成立現場指揮部,很快決定啟動Ⅰ級應急響應—這在廣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這本是一個愉快的假期,但職工們放下了飯碗、結束了旅行,通過各種交通方式輾轉回到了他們的崗位。正在桂林度假的羅同春,當晚就趕回了搶修現場。“剛進入變電站的時候,感覺到一陣別樣的寂靜,平常所有機械的細微聲響,電線之間的噼里啪啦聲,主變運行時候的嗡嗡聲全部不見了。”
“工作20多年,還從沒遇到過這樣的情況,當時廣南站一片狼藉,剛開始真有一種無從下手的感覺。”廣州供電局變電三所的老員工蔡楚榮說。
他接報后6點多就趕到了站里,當時風雨交加,站內也停電了,現場一片漆黑。工人們冒著暴雨、拿著手電筒或者應急燈,在現場摸查受損情況。衣服很快就濕透了,雨水順著褲管往下流。由于臨時從家里趕來,很多人甚至連雨衣都沒有準備。
情況空前緊急,但專業素養讓人們保持著冷靜的頭腦。之后幾天在廣州媒體與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熱圖,準確地描述了當時的場景:大雨傾盆的廣南站現場,一名變電站工作人員正在沉著得查看手中的工單。
更多的專業人員、資深老員工不斷抵達,焦慮被逐漸驅散。番禺供電局的一輛發電車迅速開過來,讓廣南站搶修現場有了光亮。
首批進入廣南站的492名“先頭部隊”摸清了受災情況,并連夜做好了施工方案。當夜有4200余人、車輛600余臺投入搶修。
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南方電網公司董事長趙建國、國家能源局南方監管局局長郭智、廣州市副市長周亞偉等親臨廣南站現場慰問,靠前指揮、穩定軍心、鼓舞士氣。
事發后4個小時,區域內95%的用戶用電恢復,5個小時,全部恢復。居民的生活一切如常了,但這并不意味著廣南站已經修好,而僅僅是一個開始。
供電恢復,是通過將廣南站失去的負荷,轉到了木棉站—去年建成的一個500千伏變電站。
“廣南站失壓后,就靠木棉站頂上來,丟掉的負荷由木棉站轉供,短時間恢復供電,這是最關鍵的一點。”廣州供電局副局長劉育權說。
木棉站的建成和投產,是“以化解電網風險為導向的電網規劃建設”戰略思維的結果。這一次,新生的木棉站立下了赫赫功勛。
如果沒有木棉站,廣南站下面帶動的9個220千伏變電站也將無法運轉,這9個變電站是對廣州中心城區天河、越秀、荔灣、海珠供電的主力電源,那么中心城區80%的供電將會丟失。
想想,8成中心城區停電,這是怎樣一種景象?而且這種景象將持續5天,直到10月9日,廣南站恢復送電。
一座木棉站,此時成了廣州整座城市的命門,而其中的出線木碧線,是在搶修期內維系供電所剩的唯一生命線,如果再遭遇不測,或被人為破壞,后果不堪設想。
當天,廣州市長陳建華聽取了甘霖的匯報之后,馬上決定由黃埔區、白云區兩個公安分局派出警力,陪同電力工作人員到木碧線沿線去嚴密巡查看守,不允許任何人接近。
故障出現總是很突然的,就像電流本身一樣,電光石火。
第一步的應對,非人力所能為,必須依靠智能化設備—繼電保護裝置。它就像人體的神經一樣,能夠即時做出反應。比如,手指觸摸到燙手的水壺,馬上就會條件反射地抽離,不需要經過思考。
繼電保護的目的,行話叫“切除故障”。通過電網上地連接開關自動跳閘,把電網的故障區域隔離出整個供電網絡。廣州供電局運行方式科的技術人員打了一個貼切的比方:“這就像傷口受感染了,如果不盡管將腐肉剔除,那么感染就會擴散。”
這時就看設備的質量了。廣南站在遭受襲擊后短短30秒,繼電保護不斷動作,開關動作309次,這些保護動作無一錯誤。
如果發生一次錯誤,比如一個開關壞了,沒有反應,或者不該它跳閘的時候它卻瞎積極地跳了,結果會怎樣?
技術人員做了一番理論推演:事故從廣南變電站蔓延到番禺、亞村變電站,從而影響到番禺全境,緊接著威脅到北方的芳村變電站,停電繼續影響到荔灣、越秀、天河……由于廣州是南方電網在廣東受端電網的核心,事故會威脅到廣東整網;甚至,由于南方電網西電東輸是通過直流輸電,電流無處安放,將進一步影響到整個南方電網。
2003年美加大停電,就是因為有的開關拒動、誤動,由一個小故障演變成美國、加拿大兩個國家的大停電,損失數百億美元。
電網的“神經”反應完成以后,“頭腦”也迅速做出反應,調度人員上場了。在轉供電的戰役中,500千伏木棉變電站的出線木碧甲乙線成為“生命線”,調度們需要避免線路過載,通過各種方式將這條“生命線”上的負荷轉走。
這要求他們根據各線路的電流、電壓、頻率等復雜的實時數據,準確地做出判斷,同樣地,一次判斷失誤,也可能造成更大故障。
他們采用的是遠程遙控操作,廣州中調當值調度長張堯說:“就像玩電子游戲,但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游戲。”
6個人,全部是年輕人,資歷最老的張堯也只工作了5年。他們在3個多小時進行了379次遠程操作,無一失誤。事后局領導給予了“了不起”的評價,這并無過譽,因為大部分在供電行業工作的人,一輩子也不會碰到如此規模的故障事件,操作者面臨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
遠程遙控,是技術設備立功的另一個側面。以往,線路故障出現后,需要派人力前往現場操作開關予以恢復,調度下達指令后,最近的工作人員奔赴現場,完成操作至少需要10分鐘。在惡劣天氣條件下,如果道路、橋梁損毀或者嚴重擁堵,則時間難以預計。而因為新技術的使用,現在可以由調度統一指揮進行遠程遙控操作,每個開關操作完成縮短到1分鐘。
供電恢復之后,廣州供電局系統內那些失去了假期的人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他們至少內心安定了。
1天半內,500千伏廣南變電站恢復220千伏帶電送電,應急響應由一級降為三級響應,電網運行風險由三級降為四級。
5天內,500千伏變電站500千伏線路送電,標志著廣南站全站恢復正常運行,比之前預計提前兩天。
在廣南站搶修過程中,人們徒手從高壓電線上清理出了“彩虹”贈送的“禮物”:鐵皮等垃圾一共超過3噸,裝了十幾車,僅從電線上取下來的棉被就有幾十床。
同時,人們還清理出了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廣州歷史上第一次500千伏變電站全站失壓;第一次多類型、多重故障集中在30秒內出現;第一次短時間內309開關保護動作并且百分之百正確;第一次在一次故障中出動電力搶修人員1.4萬人次;第一次在幾個小時之內調度人員成功遙控操作379次;第一次5個小時快速恢復40萬戶用戶供電。
這創造了極端嚴重的50萬伏變電站全停后的“廣州速度”。據稱,當這些事實披露以后,有的國內專業人士都感覺難以置信。
每一步都似乎充滿了偶然性,比如開關全部聽話,比如木棉站在去年投產,似乎都是值得慶幸的因素,“是老天爺幫了忙”。
劉育權列舉了幾個值得“慶幸”的事實。
“在2013年我們就演練過廣南站兩條母線同時失壓的情況。在當時我們在演練的時候發現一部應急發電車接口對不上,后來趕快完善了接口,接上并試驗了發電車。如果沒有當時那次,這次為變電站工作生活供電的變壓器將無法使用,現場指揮只能摸黑進行。”
“我們的電網建設從2011年開始明顯加快了速度,當時的出發點是面對廣州電網建設歷史欠賬比較多這個情況,我們在12年提出了一個觀點,我們的電網規劃建設要以化解電網風險為出發點來進行規劃和建設,直接成果就是500千伏木棉站在去年投產。”
以前,主網調度、配網調度、客服調度分開辦公,而現在已經實現合署辦公,信息快速流轉。“客戶服務調度就能第一時間知道故障在哪里,這個時候客戶甚至沒有打電話過來,我們就可以通知客戶,避免了大范圍抱怨與恐慌。”
張堯在紙上又畫又寫,解釋他所熟悉的集中調控模式所起的作用。“你看這個環節,如果沒有集中調控的模式,恢復220千伏主網架這個環節起碼要從1小時20分鐘變為2個小時,那么相應的,40.9萬戶全部恢復供電最快也要8個小時。”
每一種幸運,都是基礎扎實的日常工作的必然結果。
正因為存在“是偶然還是必然”的因果思考,廣州的供電人才可以從這一次大事件之中總結出有益的經驗:此次抗風復電,實質上體現了廣州供電局在硬件、軟件和企業管理等各方面的水平,這是一個集中的檢驗。
電停了,電又來了。對于城市居民,只是一個時間段的煩惱,而一暗一亮之間,是一股密切配合的力量在爭分奪秒,“重啟”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