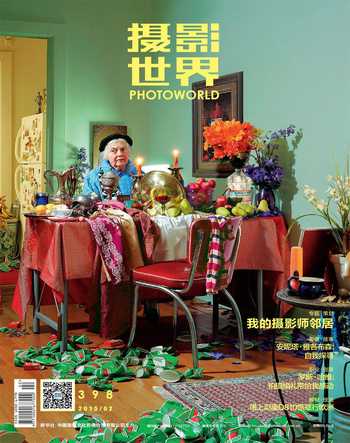林柏樑:見證中的個人情懷
傅爾得





“就像很多現代人無鄉可歸一樣,我也是一個沒有家鄉可以回的人。”說這句話時,林柏樑換了一副他極少顯露的嚴肅面孔。
林柏樑不是一個能輕易嚴肅起來的人。說話時,他總是帶著微微的笑意,眼睛瞇成一條線,藏在那副橢圓眼鏡框后面,嘴唇下那一撮花白的胡須,讓他顯得更好靠近。他說話雖然緩慢,但聲音洪亮,中氣十足;交談中,他往往會出其不意地哈哈大笑起來。我更愿意把他看成是一個樂觀、隨性的人。
1978年,臺灣畫家席德進給26歲的林柏樑畫了一幅素描。我們站在位于臺南的海馬迴畫廊展廳內,在那幅棱角分明的素描面前,林柏樑說:“我年輕的時候,就是個憤青。”他好像輕易戳中了自己的笑點,瞬間開始放聲大笑,笑聲直沖云霄,還在空中打了好幾個轉;但是,他能做到情緒收放自如,笑聲收得也快,接著說:“年輕人沒有憤怒就不是年輕人。”
1952年出生的林柏樑,已然過了憤青的年紀,“我現在的表達方式不一樣,會很溫和。”
當62歲的林柏樑,站在自己26歲時的畫像面前時,我感覺時間被微縮成了簡單的數字,順序一調,便跳躍了幾十年,一股強大的時空力量將我席卷,時間風云變幻般地在眼前流逝,過去與現在,急速對比起來。
作為攝影師的林柏樑,正是在時間的流逝中,才找到自己拍照的意義:“我的照片好像都在憑吊一些正在消逝的東西,好像是未來的遺照。”
林柏樑有一種敏銳的歷史感,他站在當下,為了未來拍照。正如他感嘆自己出生地高雄,“我小時候住的地方,變得跟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實質上已經不存在了。”
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沒有家鄉可以回的人”,以這種邏輯推而廣之,他所謂的“現代人沒有家鄉可以回”,并非是他對過去簡單的懷念,而是對于社會發展過程中傳統人文價值逐漸流失的惋惜。這種人文情懷,正是他的攝影動機所在。
把握攝影的命題
林柏樑看重攝影的紀實天性。他所拍攝的主題,如古跡風景、庶民生活、傳統節慶、文人肖像、社會弱勢群體,等等,無不關涉在社會快速發展變化中,傳統文化的變遷和沒落。“我拍鹿港的龍山寺,其實并不是在拍古跡,而是在感慨臺灣的變遷和落寞。”
在訪談中,林柏樑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在他照片表層之下的精神價值,比如,“我實際上是在講臺灣的命運”、“我實際上是在講臺灣原住民的命運”、“我實際上是在講社會的價值判斷”,等等。他總是會認真地解釋點什么,想要給自己的影像找到更重要的存在價值。
或許,林柏樑是刻意要解釋給我聽,對于一個出生年代與生活環境和他完全不同的大陸到訪者,他下意識地想要在一開始糾正理解中必然會出現的些許歧義,達到對影像的表里認同。
林柏樑擅長記錄不可挽回的時光,他興奮于在社會發展中,探尋傳統的價值。而他25歲時對傳統帶有覺醒意味的理解,來自于一位在臺灣藝術領域占有一定分量的畫家——席德進。
席德進出生、成長于四川省,受教于林風眠,25歲到臺灣,又先后在美國、巴黎游歷過幾年,受西畫的影響深刻。
“他在巴黎的博物館看到很多東方藝術作品,受到很大沖擊,在西方的世界,他想要進入抽象表達的世界,但進不去;結果,他在東方傳統藝術里面找到了根。”在林柏樑看來,席德進是臺灣藝術現代化的先覺者,“他1966年從巴黎回來時,買了一臺照相機,那時候他就開始記錄臺灣的廟宇、古跡、民間藝人,有系統地在雜志發表文章,并寫了一本《臺灣藝術》。回過頭來看,他很用心地觀察民間文化、藝術、建筑,用水彩畫臺灣的古厝、風景,他把握到了臺灣的氣息。”
受到西方藝術的刺激、影響后,轉而向自身的文化根基尋求藝術源頭的席德進,影響了他當時的學生林柏樑。
現在看來,林柏樑向席德進拜師的行為,仍然具有相當的勇氣,也不失叛逆的意味。高二時,他在《今日世界》雜志上看到席德進的畫后,便寫信過去,并收到席德進的回信。一來二去,席德進答應教他畫畫。
高中沒畢業,要從高雄去臺北,跟席德進學習畫畫,是林柏樑自己的決定,但在他家,這似乎引發了一場風暴,“他們就是不同意,后來,我媽媽去跟爸爸說情,他才同意。”
“但席德進沒有教我,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畫畫上,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夠用,那時他在大學教書,上的課也很少。”似乎席德進并沒有兌現當初的諾言,林柏樑形容自己為“畫家的書童”,他更多的工作,是協助席德進料理家務。
即便如此,席德進仍然在林柏樑的藝術生涯里,有意無意間扮演了啟蒙導師的角色。
“我給席德進當助手的那一年是1975年,那年他到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教書,假日學生都會來找他。在那時,我認識了后來在臺灣很有名的一些畫家。雖然我沒有受過藝術教育,但耳濡目染,也能跟他們談論美術了。”
“同時,也因為跟席德進在四天內從北到南游覽臺灣,打開了我的眼界。”
那四天里,席德進對著臺灣老街、民宅、古老寺廟和鄉下景致記錄、畫畫,林柏樑一旁觀看。對年輕的林柏樑來講,通過席德進了解傳統文化,雖然間接,但也讓林柏樑在此基礎上,逐漸把握到他日后用攝影表達的命題。
走上攝影之路
林柏樑開始攝影,也是因為席德進。
“那時,剛好有人找他要照片,他說可以找我去拍,便介紹我去給雜志拍照。這樣,我就開始給《宇宙光》雜志拍照,也開始給《雄獅美術》拍臺北故宮的文物。”
將攝影作為職業,也是林柏樑自己的決定。
一方面,在于他面對現實尋找出路的緊迫感,“我在席德進身邊呆了一年之后,已經25歲了,只是在當一個畫家的書童,他也沒有意識要教我畫畫。”另一方面,或許在席德進身邊呆久了,耳濡目染間,他逐漸認清畫畫是一條很難成功的道路,“我如果要成為一個畫家,靠畫畫維生,至少要十年以上,但十年不保證我可以成功。”
當然,務實的考量之外,最重要的在于他對影像的敏感,“我第一次被照片震撼到是看到自己拍的照片,一個小孩臉部的特寫,他扮演家將(臺灣的一種民俗活動,原指神將權名,通常
八位。家將為陣頭之一,負責提拿鬼怪妖邪)。因為小孩很容易夭折,父母就把小孩給神明當棄子,來保佑他成長。他的臉被顏料涂得亂七八糟,露出無辜的神情,那無形的壓力,讓我想到自己,我的心好像被針刺到一樣。從那之后,我感受到攝影的強大力量,而且能在瞬間迸發。思考三個月后,我發現似乎可以往這個方面發展。” 之后,林柏樑陸續為臺灣的報紙雜志拍攝,如《皇冠》《中國時報》《大自然》《人間》等。其中,高信疆負責的《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和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志,是當時對紀實攝影比較重視的媒體,而且這些刊物的人文關懷風格,對當時的臺灣攝影產生了一定影響。這些雜志倡導攝影并非是膚淺記錄,而重在冷靜觀察。這多少對林柏樑攝影的風格,以及對社會的理解產生過影響。
“我從攝影上得到無窮盡的財富,見證了臺灣1970、1980、1990年代的變化,一般人接觸不到這么廣泛的人、事、物。這給我很多體悟。”攝影帶給林柏樑的豐富閱歷,“是金錢買不來的”,對于攝影帶來的精神回報,無疑他很享受。
1983年,林柏樑加入臺灣視覺藝術團體,“V-10視覺藝術群”。“‘V-10’強調個人創作,我就是想表達自己的感受,我的作品有一點紀實和抽象。” 1986年和2003年,他都陸續參加了“V-10”的群展,參展照片的主題,有人物、風景,還有民俗。
一番簡要的介紹后,他依然沒有忘記要解釋幾句:“我的照片不能只從表面來看。”
1996年,林柏樑接受徠卡相機委托拍攝廣告,到蘭嶼(臺灣的一個島)拍攝臺灣原住民達悟族,“到目前為止,那是我這一生最好的照片”,在這張林柏樑自認為最好的照片里,兩位著正式傳統服裝的原住民,面朝大海背對鏡頭,標題為“面對不可知的未來”。
拍攝臺北“公娼”
林柏樑擅長運用影像思考群體命運。他更廣為人知的紀實作品《臺灣公娼運動》,便是對臺灣政府廢除“公娼”政策下“公娼”命運的記錄與思考。
1997年,臺北市議會通過廢除《臺北市娼妓管理辦法》,廢除自日據時代開始的合法“公娼”制度。當時,部分“公娼”走向街頭抗議。1999年,支持“公娼”運動的學者、社會人士成立了民間團體“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持續推動“性工作除罪化”。林柏樑正是應了在協會工作的一位朋友請求,開始拍攝臺北的“公娼”。
“我前后大概拍攝了三年,很難拍,幾乎沒有辦法,都只能拍背影和局部。開始只有一個愿意被拍,但后來她們都接納我了。”
唯一一個愿意被拍的,是林柏樑稱之為官姐的官秀琴。
“官姐父親是礦工,肺纖維化后,人到中年,就沒有辦法工作了。她是長女,便犧牲自己把弟弟妹妹帶大,甚至她哥哥的卡車都是她買的。即使這樣,她哥哥還是看不起她。她離開正常社會久了,連衣服也需要讓別人幫忙買。她沒有容身之地,生活空間只在娼館附近。”
林柏樑愿意理解她們的困境,為這群社會邊緣人尋求幫助,“開攝影展時,去了很多媒體,報道對她們的幫助很大。很多人來看展,包括以前的嫖客,有一個后來就自動跑來幫忙。”
即便如此,這個群體依然躲不過命運。2001年3月29日后,“公娼”正式列入不合法范圍。而沒有其他謀生能力的官秀琴,因付不出卡債,跳海自盡。
“那些‘公娼’的年紀都比較大了,沒有其他謀生能力。有人曾幫忙其中一位弄了個檳榔攤,可是她不會加減乘除,因此酗酒,兩三天之后,她被發現在家中暈倒。現在,是‘日日春協會’在照顧她。”
“社會給她們的污名太大,她們不僅是社會邊緣人,更是站在崖邊的女人,再一步就掉下去了。”
對著自己拍過的照片,林柏樑愿意用人道主義的善良,去理解這個社會。比如,1980年在臺北南昌街拍的一張照片里,一位雙手手肘全斷的老兵,在街頭賣東西以自食其力,遇到了一位收廢紙的同鄉,同鄉停下來,點燃一根香煙,放到老兵的口中,“這一幕,看得我感觸良深,既溫馨,又殘酷。”
拍攝文學容顏
攝影使林柏樑練就了一雙善于發現的敏感眼睛,當然,這并不表示他有溫和的個性。2013年8月,由臺灣青年攝影師陳伯義發起,臺南的海馬迴畫廊為林柏樑舉辦了名為“私人備忘“的個展,展示他30多年攝影生涯的重要作品。陳伯義稱林柏樑為“老師”,在一場對談中,陳伯義說:“老師私底下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對不爽的事情就像怒目金剛一樣。但我覺得老師的照片卻非常柔軟,他不會把自己的批判強加在照片里。這是老師創作和個性之間的反差。”
對于被總結出來的“反差”,林柏樑甚為贊同,“我是典型的天秤座,隨時在追求一種平衡。我平時對社會有自己的看法,也會罵,但照相機一拿起來,心就靜下來了,不會過于火爆,很多事情不能輕易下判斷。”
1998年,林柏樑受托拍攝了臺灣一系列文學作家的肖像,例如陳火泉、巫永福、周夢蝶、葉石濤、東方白、七等生、楊牧、李昂等人的,該系列被稱為“文學容顏:臺灣作家群像攝影”。
林柏樑稱那次拍攝為“挑戰”,“每位作家年紀都很大,不但生活閱歷豐富,想法也很多,我必須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每個人大多只能花一到兩天拍攝,但準備工作卻非常細致,花了很長時間,“東方白有一套三本的著作,一百多萬字,我要在很短的時間內看完,但是看得很愉快。他寫得非常精彩,把臺灣的近代史透過小說活靈活現地講了出來。”
拍詩人周夢蝶前,林柏樑已看過他的傳記和著作,對這樣一位臺灣社會中眾所周知的清苦詩人,他的鏡頭表現也甚為獨特,“他話很少,人很安靜。我一問他一答,有時候,話是接不下去的。其實,他是一個內心很熱情的人,我跟他握手,他很用力,能感覺到他的真誠。”
這些在臺灣土壤下成長、成熟的文人,都曾在某一個層面上為臺灣社會的發展認真“把過脈”,用各種方式刻畫著臺灣的陰郁與浪漫、荒謬與真實,他們出現在林柏樑的鏡頭前,展示出一種莊重的尊嚴感,時代的風骨與自我的個性并存。
“我拍照其實時間很短,我把所有的精力都凝聚到那個點上,精神高度集中,但全身都是汗,拍完人就垮掉了。”
拍作家葉石濤的時候,林柏樑跟著葉石濤去了一些他小時候生活的地方,“葉老以前在白色恐怖時期被抓過,他說獄房小小的,擠了幾十個人,不能完全躺平,得輪流睡覺。每天都有人被帶出去就回不來了,這段經歷差點毀了他的一生。”在臺南的武廟后院里,林柏樑發現斑駁墻面前的一把竹椅,讓葉石濤坐在上面,“我既興奮又緊張,那個天色已經暗了,光線詭異,我仿佛看到那次恐怖經歷仍未在他身上消散。為什么我會激動呢?因為我知道,那神情只有一剎那。”
見證中的個人情懷
正如林柏樑自己所說,“如果要簡單設想一下我以后的回顧展,會是幾十年來,我見證了什么。”
陳達是臺灣民間藝人中很有名的一位,有不少臺灣攝影師拍過他。“陳達死的時候,是一個貧民,他的聲音很動人,如果讓他在美國的卡內基音樂廳表演,我相信外國人同樣可以欣賞他。”
“陳達這張照片是我在1982年拍的,那年他74歲。大年初三,我和幾位朋友去屏東看他,帶了個大西瓜和兩條長壽煙,他很高興,唱了一首歌給我們聽。他的聲音很有魅力,人生的滄桑都融化在歌聲里,很感人。他唱完歌,把我們忘得一干二凈,陷入自己的思緒里,開始抽煙。我3月1號去看他,他4月中旬就因車禍走了,這應該是他最后的一張照片。”照片是現實的副本,在現實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它為消亡佐證。林柏樑的記錄是零碎的,帶有強烈主觀意味的,是一種帶有個人情懷的檔案般的見證。林柏樑作品的意義,在于他給我們可供凝視的瞬間定格,并感受與思考承載在這些人身上的時光。
林柏樑那碎片式的記錄,并沒有要刻意反映整個社會的企圖心,如他所說:“我是很散漫的,接觸到就去拍,比較隨性,使命感放在心里。只要還能從攝影上獲得精神收獲,我就會繼續走下去。”
之后,林柏樑打算記錄一些臺南的老工匠或者賣五谷雜糧的店,“老一輩臺南人堅守傳統,面貌氣質很不一樣。”
林柏樑肯定堅守,大概是出于一種對當下和未來的擔憂,正如他說,“我們都是無家可歸的人”。大抵也因如此,他要繼續記錄已經消逝的文化。
臺北市的幾條主干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有秩序地彰顯著社會的文化價值。林柏樑的攝影動機出于擔憂,想要從傳統的人文價值中,找到立足的根基和文化自信,這一點,在這個飛速發展的社會中顯得有一定意義。
一切擔憂,都很難跟得上社會的飛速發展,如此,照片的意義又有多大?我們無法精準估算。起碼,行動的意義大于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