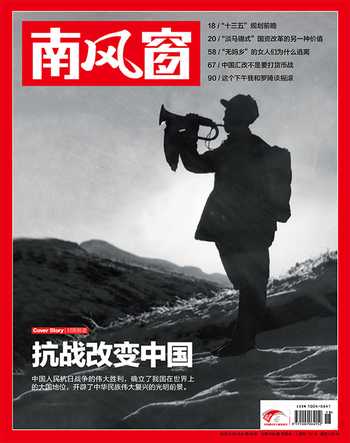中日和解繞不開歷史這道坎
雷墨
“歷史不會死亡,甚至永遠不會結束”。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重溫美國著名文學家威廉·福克納的這句名言,意義尤為特別。中日之間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但有關歷史認識的“戰爭”仍未結束。美國學者加納·費爾德曼去年4月在《外交政策》雜志上一篇題為《和解意味著你必須說對不起》的文章中寫道:和解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它沒有終點。
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首相安倍晉三8月14日發表的戰后70周年講話中,雖有以回顧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間接提及“反省”、“道歉”,但其宣稱戰后出生的日本人不應背負“謝罪的宿命”,傳遞出的“不再道歉”的訊息,既是對“歷史”的誤解,也是對“和解”的誤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回應指出,正確認識和對待過去那段歷史,是銘記歷史、捍衛正義的要求,是日本與亞洲鄰國改善關系的重要基礎,也是開創未來的前提。
9月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將舉行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閱兵,以及一系列相關的大規模紀念活動,某種程度上說是中國對歷史正義缺失的一種回應。英國牛津大學的中國問題學者拉納·米特在其2013年出版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寫道:數十年來,西方人眼中的二戰始終是一場美英蘇領銜抗擊法西斯的血腥戰爭,亞洲戰場上英勇抗擊日本的中國卻因種種原因被遺忘。西方遺忘的不僅僅是中國這個盟友,還有歷史正義。
歷史認識之所以重要,首先體現它事關歷史正義。
冷戰結束后,國際社會出現過一段被學術界稱為“道歉時代”的時期。比如法國對殖民統治阿爾及利亞時期制造的大屠殺道歉,美國克林頓政府對未能阻止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道歉等。日本的“村山談話”與“河野談話”也正是出現在那個時期。但國家在國際層面主動追求歷史正義,在世界歷史上幾乎還是空白。今年7月9日,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七次峰會期間,借助這一國際平臺呼吁“堅決反對否認、歪曲、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圖謀和行徑”。在日本右翼歪曲歷史的背景下,中國有必要將歷史正義引入國際議程,并打造自身的話語權。
歷史認識不僅是對過去的記憶,也會塑造國家的未來。對歷史的集體記憶,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國家之間的關系。眾所周知,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起初是不支持德國統一的。當時她的顧問曾對她說過這樣一番話:“西德現在值得信任,所以應該鼓勵其與東德統一。主要原因就是它在面對德國暴行歷史上的‘模范表現’。”可以想見,當初撒切爾夫人主要的擔憂在于,統一的德國是否會構成安全威脅。美國達特茅斯學院學者珍妮弗·林德在一篇關于歷史認識爭議的文章中指出,歷史記憶對國家安全問題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能塑造威脅認知以及國家間的信任水平。
德國當初能順利實現國家的重新統一,日本如今的實現“國家正常化”的努力為何得不到鄰國的理解和支持?林德關于歷史記憶與威脅認知之間邏輯關系的觀點都具有解釋力。某種程度上說,日本向曾遭受其侵略的亞洲鄰國展現何種歷史認識,就會在這些國家中建構何種威脅認知。日本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野晃一也認為,有關歷史記憶的政治是塑造如今東亞國際關系的一個關鍵因素。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日本那些堅定主張修改和平憲法、推行強硬安全政策的政治人物,正是那些極力否認日本侵略歷史的人。安倍正是這類政治人物中的典型代表與堅定實踐者。
據說西德總理阿登納在世時每晚都閱讀《圣經》,他對宗教的虔誠也被用來解釋他主動向德國侵略戰爭受害國伸出和解之手的原因之一。但歷史的另一面是,當時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和法國總統戴高樂對阿登納政府施加了強大的壓力,敦促其采取更多緩和關系的措施。美國的施壓當然是出于地緣政治考慮的需要,就如同它沒有在戰后清算日本的戰爭罪行一樣。但阿登納政府的和解外交也表明,戰爭加害國的歷史認識以及與受害國的和解,離不開外部壓力。虔誠如阿登納的政治人物尚且如此,鮮有宗教情結的日本領導人沒有理由不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承受更大的外部壓力。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以憲法的形式放棄國家發動戰爭權力的國家。和平主義一直是戰后日本政府推銷國際形象時的一大賣點,有學者甚至論證日本出現了“和平民族主義”,并演變成“日本例外論”。這種“例外論”也賦予了日本作為國際社會一員的優越感。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曾經說過:“日本對和平的愿望,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堅定和強烈。”正因為如此,致力于修改和平憲法的安倍也不愿放棄“和平主義”的論述,提出“積極和平主義”。日本社會的確存在自戰后延續至今的反戰、反軍國主義聲音,但將和平主義上升到日本國家身份的高度,卻值得商榷。

2015年5月3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出席紀念達豪集中營解放70周年紀念儀式。
日本戰后首任首相吉田茂是和平主義的提出者,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日本問題學者邁克爾·格林對此的評價是這樣的:吉田茂以及日本保守派精英把和平主義視為最大限度地爭取國家獨立直至復興的手段,其后的繼任者都把制度化的憲法第九條作為防止日本被迫卷入美國冷戰戰略的防護網。也就是說,日本和平主義的緣起是國家利益考慮,與國家身份塑造無關。瑞典國際事務研究所日本問題專家里努斯·哈格斯特朗甚至認為,日本戰后的“和平身份”,并非由對和平主義標準的堅持或反軍國主義文化催生的。正因為如此,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絕不意味著他對和平的追求更積極。
德國國際與安全事務研究所學者漢斯·茂爾曾表示,盡管可以說實力是政治的核心,但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在德國卻是一個禁忌。日本則完全不一樣,其對和平主義的論述,從來沒有脫離實力政治的范疇,“和平身份”也沒有德國那么“正宗”。戰后日本的和平主義,并不意味著否認軍事實力在維護國家安全上的重要性,日本只不過是把這個任務“外包”給了美國。如今意識到美國的保護不那么可靠了,日本就開始考慮“自己動手”了。在哈格斯特朗看來,和平依賴于威懾的邏輯,使日本安全政策的大幅轉變成為可能,這也是安倍“積極和平主義”的精髓。
和平主義論述“參照對象”的變化,也折射出日本正在邁向實力政治。戰后相當長一段時間直至冷戰結束前,日本在描述自身“和平身份”時,參照的“非和平”對象更多的是“帝國日本”。比如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1972年的一次講話中說:“我們的經濟實力已經大幅增強,但我們絕不會再次成為軍事大國。”而且每當日本政府增加軍費,總有反對黨議員指責其開歷史倒車。但冷戰結束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的“非和平”參照對象逐步轉向“崛起中國”。安倍政府對“積極和平主義”的推銷,總以“中國威脅”作為鋪墊。
盡管日本再次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可能性不大,但日本政治的變化卻不得不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日本問題專家希拉·史密斯認為,日本右翼在戰后政治中一直是引人注目的勢力,但如今他們的某些曾經非常邊緣化的理念,已經變得更主流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這樣評價日本:日本認為他們的社會非常獨特,能夠在適應任何變化的同時,保留民族的精髓。所以日本人能夠做到突然的巨變,他們可以在兩三年內從封建主義轉向天皇崇拜,又能夠在3個月內從天皇崇拜轉向民主政治。如果基辛格的判斷成立,那么日本的和平主義就更難以讓人放心的。
安倍在戰后70周年的講話中表示,不能讓與戰爭沒有任何關系的子孫后代不斷背負謝罪的宿命。美國波士頓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托馬斯·博格,把日本的道歉稱為“不完美道歉”。他在對比德國時指出,盡管德法在1960年代就實現了有限的和解,但如果沒有德國對其侵略歷史持續不斷的謝罪,那樣的和解注定將是非常脆弱的。英國利茲大學日本問題教授卡洛琳·羅斯也表示,日本在“道歉”上的種種努力,沒有“強化道歉”的行為作支撐,反而還伴隨著來自政府的含糊言辭、適得其反的聲明和行為。
與安倍關系較為親近的日本前外交官岡崎久彥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只要日本與英國或美國結盟,日本總能表現出色”。但岡崎久彥卻沒有看到事實的另一面:與西方國家同盟關系搞得不錯的日本,在亞洲卻向來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盟友。漢斯·茂爾在比較德日和解外交差異時指出,日本很大程度上放棄和解時,德國卻利用其政策占領了道德高地,成了可以信賴的國家。“正是來自鄰國的信任,使得德國的重新統一成為可能。”反觀日本,仍在與曾遭受其侵略的鄰國進行“歷史戰爭”,似乎真誠的道歉就意味著戰敗。
亞洲國際格局正在發生的變化,使日本未來能否繼續“表現出色”,更多地不再取決于其對同盟關系的經營。對于日本來說,無須實現歷史和解就能繼續保持繁榮發展的外交操作空間,正在日益縮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日本問題學者杰拉德·柯蒂斯注意到,從安倍最近的言行來看,他不僅意識到了日本沒有能力遏制中國,即便日本想這樣做,而且日本未來的福祉也取決于與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之間更緊密的經濟聯系。但要做到這一點,正視歷史并主動伸出和解之手,是日本回避不了的外交課題。
包括安倍在內的日本政治人物,有的是時間建設“美麗國家”,但留給他們實現與東亞鄰國和解的最佳時機已經不多了。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亞洲問題學者望月,在題為《歷史記憶、現實主義以及東北亞和解》的文章中寫道:朝鮮半島的統一以及中國的崛起,給東北亞戰略調整帶來的挑戰,將比德國統一之于歐洲來說大得多。推進歷史和解在東北亞將更加關鍵。望月教授所說的“挑戰”,日本應更有緊迫感。如果在歷史問題上沒有實現和解,無論是崛起的中國還是統一的朝鮮半島,都不會讓日本的戰略調整更容易。日本需要擔憂的是,別在建成“美麗國家”的過程中,成了東亞的“邊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