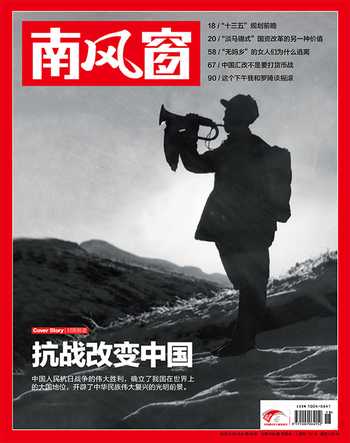讓人“回到自我”的廣州
何蘊琪
“我家就在美術館附近,每次在這個地方,就在想,如果晚上從這里的窗戶看出去,看到月亮慢慢升起來,會是什么感覺。”F在我組織的故事會活動里面分享她對于夏天的感覺。她有一張質樸單純的臉,從穿衣打扮到氣質,形象和一般意義上的文藝青年有著本質區別,可能因為這樣,這句話從她口中說出有一種不同尋常的真實感。她描述的時候眼睛里閃爍著光芒,我感覺自己也好像沉浸在那個詩意的意象里。
就在這次聚會不久前,我約F在一個餐廳見面,請她談談對自己身份的理解。和上次走訪的楊箕村村民一樣,F也有著一個稍顯特殊的“地主”身份,她所在的村子在白云區,雖然不大,但也因著城市新移民的涌入而共享著“城中村”發展的紅利。家里一棟房子在出租,她其實不太為柴米油鹽憂心,因而也有了更多時間可以發展自己。和所有人一樣,她經歷著城市變革帶來的得到與失去。如果說舞獅隊、龍舟隊的參與者,那些陽光下黝黑的肌肉、汗水,似乎是男性氣質和宗族儀式在城市里更新的象征,那么F所投入很多的活動則似乎更有女性的特質,她對藝術、教育有超出一般的理解。
F個子嬌小,打扮既不時尚也不文藝,更接近家庭主婦,頭發常常用發卡梳到腦后,眼神清澈,說話語速挺快。你很難想象她比那些留長發、穿長裙、手里拿著煙,三五成群討論藝術的藝術家、準藝術家,或是文藝青年們更加鐵桿,至少在我眼中是這樣。
我們最早結識是在民眾戲劇圈子,具體在哪一次相遇已經忘記。也曾一起演出過,當時我給一位朋友的短劇做音效,而她獨自做了另一個演出,結束后,一桌人笑說她劇中的幾個BUG,但她不以為忤,純真的笑容依舊。幾年來,就是這樣偶爾在活動或工作坊中碰到,交談不多。
一次我們一起看香港導演鄧樹榮的戲,在正佳廣場,舞臺在某一層,她已經第二次看了,提早在再上一層的咖啡店占好位置,招呼我們過去:“這里是最好的位子!”演出后拉著導演探討藝術問題,那份單純執著讓我們都佩服。

我問,你眼中的藝術是什么。她托腮想了一會,“藝術是將人打回原形,修煉成妖。”我被這句話驚到了,她接著解釋,我們日常的生活,“常常是把垃圾當食物”,而藝術就起到了“吸塵器”的作用。聊天中我幾次被這樣深度的話所觸動,看得出來,這是從F心里發出的聲音,是直覺而不是思考或分析,也不是知識學習的結果。
是的,這番談話常常將我帶回頭腦或確切說是心靈中一個很少被觸及的地方。那時在北京,十多年前,校園外面就是最負盛名的書店雕刻時光,在最初的認識里面,不單藝術是風格化的,連藝術愛好者也是—咖啡館裝修得很有文藝情調,墻上書架堆著一些令人敬仰的作者的書和各種小眾音樂唱片,燈光昏暗,角落有貓,里面坐的人連面相都是那么藝術。他們抽煙、喝酒,這里仿佛是另一個法國左岸。是的,藝術一直給我這種感覺,它必須是小眾的,必須是美的,必須是與眾不同的。它甚至是一種不被察覺的暗含著中產元素的時尚,影響到一群人的談吐、衣著、舉止、修辭。而假如一個人的標識不夠藝術,那么他/她似乎也不被認為和藝術有所關聯。
回到廣州很多年,我自己也很少參與藝術圈子的活動,這當然和性格,但其實也和廣州的氛圍息息相關。這是一個關心食物的烹制多于關心餐館裝修風格的城市,一個人們談論柴米油鹽多于談論文化活動的城市,簡而言之,這似乎是一個關心物質多于精神的城市。
一個也愛好藝術、同樣在北京上過大學的中學同學和我說過這樣的話:“在北京,你感覺就算一無所有也可以很快樂,但是回到廣州就不可能。”這種觀察有它的道理。但是,真的是這樣嗎,廣州就是一個那么物質的城市嗎?
F的思維很發散,一會會專注回答問題,一會又和我探討起馬克思的“沖突”論。“沖突到底是怎樣產生的,不同的哲學家怎樣論述這個問題?”這是她現在修讀的社工本科課程要做的作業,看得出這個問題激起了她特別大的興趣。我想起了很多年前讀大學的時候,在我們這些傲嬌而不知所謂的大學生中間,有時候會夾雜了那么兩三個旁聽課程的社會人士,他們職業各異、神色各異,但同樣擁有我們都比不上的對藝術、知識和真理的超乎想象的渴慕。
這可能是F的情況,幾年前,她是一名專業會計,一邊上班,一邊拿上班賺的錢來上心理課和戲劇課。曾經是工作狂,后來因為機緣巧合,參與公益圈的許多藝術和教育培訓課程,一度成為某個著名公益組織的兼職財務人員。現在她已經徹底自由身,變成我們羨慕的悠閑人士,同時修讀社工課程。她特別強調,自己很幸運,當年一開始認識到的都是廣州公益圈子最優秀的人。
我問以前和現在,這兩種生活狀態有什么區別,她說,“以前感覺有點分裂,現在更加像一個整體,可以沉下心,解剖自己,面對沖突。”我意識到沖突是一個在F的生活和思緒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關鍵詞,在后來的聊天里,我了解到F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她有小孩子,非常關注教育問題。盡管F自己沒有提到,但我發現,無論是學習和關注藝術、社會工作,她其實都有一個核心的關注。其實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回到廣州生活多年,開始參加當年在北京只會旁觀而沒有參與的劇場,是因為它的角色(或是我自己的角色?)已然轉變。
在當年我所觀察的大學生群體里面,和詩歌、音樂、電影一樣,劇場有著自己的語言—藝術更多是一種需要由展覽-觀賞-評論這個過程來完成的小圈子游戲。在林少華、孟京輝積極探索先鋒劇場的1990年代,大學生趨之若鶩,劇場是知識分子表達的工具,它在趣味上是精英的,內容上是充滿人文關懷的,而形式上卻是先鋒的。年輕人迅速而積極地沿襲了這些語言,就如同1980年代全國年輕人都在修習現代詩一樣。但到后面,當形式超越了內容,展覽的意義勝過了表達時,我開始不再走進學校內外的小劇場。
但工作多年以后,劇場又突然成為我釋放工作壓力,從更多角度理解社群、文化、人性—這是新聞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的渠道。我雖然沒有特別關注的議題,卻確確實實是從自己的需要、自己成長出發去再次接近藝術,這和F有著本質的相似之處。
這個也是我們所認識的廣州—它可能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一個非常風格化和符號化的藝術氛圍,直到現在,從事文化事業的朋友聚在一起,偶爾還是會說到,工作機會在北京、上海、甚至深圳都要更多、更好,文化活動也要更多一些。但大家還是選擇留下來,廣州確實有它的吸引力—如同F所說,藝術可以“將人打回原形”,廣州也有這樣一個氛圍,它可以將人打回原形,將最本質的一些東西留下,因為它有一種務實的風格。這種務實不單體現在商業中,也滲入在藝術中。所以在廣州,真正喜歡文藝的人,可以很多年隱忍地僅僅因為藝術的回報而做,而不是為了一些附加的價值,我身邊的不少朋友就是這樣的典型。他們是律師、教師、醫生、銀行職員、工程師,他們表面上一點都不文藝青年,有時候穿著也很土,他們也很少去咖啡館對藝術和人生侃侃而談,但他們默默地學習、演出,然后繼續上班、下班。
回到“將人打回原形”的藝術觀念,我理解F所說的,是她在藝術中發現一種對身心靈的凈化功能,這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藝術觀念和美學觀念。在這種觀念里,美,或者藝術,是有功能性的,而不是為了藝術而藝術。如同F一樣,她參加很多戲劇工作坊,看戲,聽大導演的講座,最本質地,她其實在探求人的成長。
“最想做的,其實是教育,但是現在覺得自己還沒有這個能力。我不想自己也像其他老師一樣,把小朋友培養成機器人。在中國,見到一個是人的老師,已經很難得。”她話一出,我又一驚。F有自己的許多觀察,說出來常常讓人驚訝,但細思之下又有她的道理。
我們還談論了其他話題,我發現,F非常關注社會問題,她對社會的關注,甚至不比我這個媒體從業人員要低。究其原因,可能還真的不能和她的自由身脫去干系—但是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她的關心是從一個切身的角度出發,而非傳統知識分子的憂國憂民的宏觀角度。
無論如何,我在這次對話里發現了一些以前從來沒有留意的東西,是F身上,和我自己身上的,也是許許多多這個城市生活著的普通人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