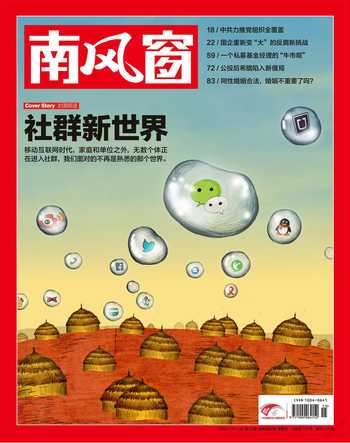應(yīng)該給農(nóng)村集體制度一個機(jī)會
李北方
今年年初,盧暉臨老師出了一本書,題為《通向集體之路》。書的主體是作者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安徽一個叫作汪家村的村莊走向集體制度的過程。書中還附了另外兩篇作者關(guān)于農(nóng)村的論文,其中一篇是關(guān)于河北的周家莊合作社的研究,周家莊恐怕是全國唯一仍按人民公社制度運(yùn)行的地方。兩個關(guān)于集體化的研究相隔十多年,思路上有明顯的差異,這與其說是內(nèi)在的矛盾,不如說如實(shí)反映了作者思想發(fā)展的軌跡。這次關(guān)于集體化的對話就從作者思想的發(fā)展開始。
《南風(fēng)窗》:讀你的這本書,我覺得最有意思的一點(diǎn)是,其中有你自己跟自己的辯論,自己對自己的批評,不同時期的文章對待集體化的態(tài)度是不同的。你的博士論文雖然沒有直接批評集體化實(shí)踐,但字里行間流露出負(fù)面的情緒。當(dāng)時為什么會持那樣的態(tài)度?

盧暉臨:其實(shí)我年輕的時候沒有太多所謂立場的考慮,因?yàn)槭菍懖┦空撐模械氖撬^純學(xué)術(shù)的立場,至少自己當(dāng)時感覺是這樣,就是想探討集體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探討集體制度和舊有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我當(dāng)時想要追求學(xué)術(shù)性,今天回過頭看,當(dāng)時對研究對象的生活狀況關(guān)注是不夠的,無論是搜集的資料、關(guān)心的問題,都有一定的盲區(qū)。
《南風(fēng)窗》:但我作為一個讀者還是感覺到了傾向性,大體上是與對集體化的主流表述很接近的那種態(tài)度。當(dāng)時集體化已經(jīng)被瓦解了,對集體化的主流闡釋基本上就是論證集體化失敗的必然性,你的研究其實(shí)呼應(yīng)了這種論調(diào)。
盧暉臨:我覺得你的這個觀察是對的。每個人進(jìn)入研究議題的時候,都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狀態(tài),我也不例外,我相信一些潛在的,哪怕我沒有意識到的一些聲音對我是有影響的。當(dāng)時講到集體就是會講到?jīng)]有效率、大鍋飯、平均主義等等,報(bào)紙、雜志以及我平常看的一些作品都是如此。這反過來說明,純學(xué)術(shù)的角度本身有它的問題,純學(xué)術(shù)的角度強(qiáng)調(diào)不帶立場、不帶判斷,可是實(shí)際上不存在這個東西。你自己平常的閱讀,從方方面面獲得的知識、信息都會影響你的判斷,只是你沒有清醒地去反思而已。
《南風(fēng)窗》:你寫的周家莊的那篇文章,對集體化是持同情和支持的態(tài)度的,在思想上是非常明顯的變化。能否結(jié)合自身的經(jīng)歷,談一下這樣的認(rèn)識轉(zhuǎn)變是如何發(fā)生的?
盧暉臨:我是農(nóng)村出來的,1969年出生,集體化時期還小,長大一點(diǎn)了就在學(xué)校里讀書了,對那個時代的是是非非,我個人的切身體驗(yàn)不多。改革開放之后也是一直在學(xué)校度過,和農(nóng)村的接觸也不夠。后來我在做田野調(diào)查的時候,已經(jīng)看到了很多農(nóng)村的問題,但我把自己設(shè)定在探討集體制度是怎么產(chǎn)生的這個問題上,所以只寫到70年代。今天回過頭去看80年代、90年代農(nóng)村的問題,是可以看到它們與集體消亡之間隱秘的聯(lián)系的,但是當(dāng)時還沒有這樣一個清醒的認(rèn)識。
對集體化問題的認(rèn)識轉(zhuǎn)變和我后來做農(nóng)民工研究有關(guān)。在做建筑工人、制造業(yè)工人的研究時,我看到了農(nóng)民工的生活和工作狀況。我開始做農(nóng)民工研究是在2000年之后,在90年代“三農(nóng)”問題已經(jīng)比較明顯了,到了做農(nóng)民工研究,我意識到他們之所以到城市里打工跟集體制度的消亡有關(guān)。聯(lián)系起來看之后,我開始對原來的看法進(jìn)行了校正。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多了歷史的角度。之前對于集體化的研究,我覺得歷史的角度是不夠的,而且很多研究太過局限于村莊層面。當(dāng)有了一個更大的視野,對問題的看法就慢慢發(fā)生了改變。比如說農(nóng)民的生活水平問題主要反映在有多少糧食吃,很多研究都講農(nóng)民在集體化時期的吃糧水平?jīng)]有明顯的提高,可是當(dāng)我們對國際環(huán)境和歷史背景有了更清醒的認(rèn)識后就會追問,為什么會這樣?就是因?yàn)槌源箦侊垺]有效率,所以生產(chǎn)發(fā)展不起來?不是的,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平均主義,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還是發(fā)展了,只不過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發(fā)展成果并沒有完全留在農(nóng)村。而且農(nóng)村的發(fā)展是多層面多維度的,不能僅僅從吃糧食上面去講,以我研究的汪家村來說,這個村的發(fā)展算不上好,但到了70年代,一套基本的保障體系已經(jīng)建立起來,生計(jì)安全、教育、醫(yī)療等基本需求大致可以保障。
《南風(fēng)窗》:你談到了“窩工”的問題,集體化沒能充分吸納勞動力,后來這些人成了農(nóng)民工,被“大進(jìn)大出”式的國際加工貿(mào)易模式消化了。這往往被論證集體化解體合理性的那些人當(dāng)作證據(jù)。根據(jù)你做田野調(diào)查時的了解,在集體制度被解散之前,農(nóng)村集體在解決“窩工”問題上有沒有開始有一些進(jìn)展?
盧暉臨:在集體化時期,“窩工”現(xiàn)象是事實(shí),有一些地區(qū)還是蠻嚴(yán)重的。這和發(fā)展戰(zhàn)略有直接的關(guān)系,當(dāng)時國家的工業(yè)體系基礎(chǔ)還沒有建成,還沒有從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yè)轉(zhuǎn)向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yè)。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產(chǎn)業(yè)會永遠(yuǎn)陷于那樣一個處境,不會完成升級。比如70年代末,蘇南地區(qū)的“窩工”現(xiàn)象基本上得到解決,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興起讓蘇南農(nóng)村慢慢走出了黃宗智先生說的“內(nèi)卷化”困境。
在當(dāng)時的城鄉(xiāng)二元體制下,農(nóng)村為了國家的重工業(yè)化和國民經(jīng)濟(jì)體系建設(shè)做出了貢獻(xiàn),也可以說是付出了代價。按照當(dāng)時的邏輯,在國民經(jīng)濟(jì)體系的基礎(chǔ)打好之后,無論是農(nóng)村內(nèi)部生長的企業(yè)還是城市輕工業(yè),是可以逐漸吸收過剩的農(nóng)業(yè)人口的。但80年代之后,我們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外資進(jìn)入中國,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進(jìn)入工廠,當(dāng)然是以非常單純的勞動力形式進(jìn)入的。這就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不一樣,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他們既是勞動力,長遠(yuǎn)看也是企業(yè)發(fā)展的受惠者。
《南風(fēng)窗》:也是所有者。
盧暉臨:是的。如果按之前的邏輯,他進(jìn)入城市就成為城市集體企業(yè)的工人,或者是國有企業(yè)的工人,而不是簡單的勞動力。
《南風(fēng)窗》:其實(shí)現(xiàn)在回過頭看,農(nóng)村集體制度被強(qiáng)行解散那個時候,恰好是這個制度經(jīng)過痛苦的形成、發(fā)展和逐步穩(wěn)定,正要破繭而出的時刻。
盧暉臨:我覺得挺可惜的。集體制度的發(fā)展時期是最困難的,經(jīng)濟(jì)基礎(chǔ)很差,全社會剛剛從舊制度里過來,人的頭腦中完全是小生產(chǎn)者意識,這與新的制度之間是有矛盾和抵觸的。農(nóng)民一開始不適應(yīng),但干了一二十年后,有一些地區(qū)的生產(chǎn)和生活水平實(shí)現(xiàn)了增長,大家嘗到了一些甜頭。在最嚴(yán)苛的環(huán)境中誕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到了70年代,無論是內(nèi)部還是外部,集體制度都到了一個逐漸向好的時期。
《南風(fēng)窗》:有一些地方的增長不能說太慢,在辦起了自己的工業(yè)之后,日子就發(fā)生了比較顯著的變化,這是個人單干達(dá)不到的。
盧暉臨:現(xiàn)實(shí)情況差別比較大,大概1/3的農(nóng)村集體在生活水平和福利方面的發(fā)展勢頭不錯,1/3處于中間狀態(tài),還有1/3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發(fā)展不是太好。應(yīng)該說,一些地方農(nóng)村集體在70年代已經(jīng)到了要開花結(jié)果的時候,在外部,工業(yè)體系已經(jīng)比較健全,拖拉機(jī)產(chǎn)量大幅度提高,可以支持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生產(chǎn)方式,農(nóng)業(yè)科技也得到了發(fā)展,大型的化肥廠建成,城市反哺農(nóng)村、工業(yè)支援農(nóng)業(yè)的態(tài)勢形成了。
《南風(fēng)窗》:確實(shí)也有很多地方的農(nóng)村集體發(fā)展得不好,小崗村當(dāng)年無疑屬于較差的那部分。
盧暉臨:集體制度的消亡有多種原因,來自于農(nóng)民的對抗性力量是有的,這個力量怎么看?我在書中講到了人性和制度的沖突。在一些地方,農(nóng)民開始能夠抑制小生產(chǎn)者意識和自私的一面,逐漸發(fā)展出可以和集體制度配合的行為方式和習(xí)性,不敢講成為了社會主義新人,但是有了巨大的改進(jìn)。有些地區(qū)就做得不好,這里面可能有自然條件和其他因素的影響,在這樣的地區(qū),農(nóng)民的小生產(chǎn)者自私意識在70年代末就成了瓦解集體制度的因素,小崗就是這樣的代表,老百姓鬧著要分。這里面當(dāng)然也有集體制度本身的問題,比如干群關(guān)系,老百姓可能把對干部的怨氣發(fā)泄到集體制度上。
集體制度的改革,本來是說不要一刀切,讓農(nóng)民自愿選擇,可是到最后反而變成“一包就靈”的一刀切了。在集體制度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確實(sh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然而,如果這些代價不能通向任何一個有意義的目標(biāo),它們還可以被稱為“代價”嗎?
實(shí)際上即使集體制度發(fā)展得好的地區(qū)也一定有自己的問題,但要給他機(jī)會進(jìn)一步完善。如果不一刀切,這些地區(qū)完全可能和另一部分地區(qū)形成發(fā)展模式的競爭。
《南風(fēng)窗》:你把農(nóng)民工稱為一種制度安排,當(dāng)時解散了農(nóng)村集體,把釋放出來的勞動力逼到沿海,為外部需求而生產(chǎn)。聯(lián)系你對集體的看法,如何理解這種情況?
盧暉臨: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實(shí)際上為世界工廠提供了勞動力,農(nóng)村土地到了90年代變成了城市發(fā)展的資源,這里面有內(nèi)在的邏輯。但我相信是一步步走上這種發(fā)展方向的,當(dāng)時的舉措看起來是簡單的技術(shù)性的決策。
《南風(fēng)窗》:鄧小平晚年講過農(nóng)村發(fā)展的二次飛躍,還要走發(fā)展集體經(jīng)濟(jì)的路。現(xiàn)在的政策也有一些帶有集體化色彩的舉措,比如鼓勵合作社的發(fā)展。就協(xié)調(diào)解決農(nóng)民工問題的潛力而言,你能否對比一下集體化和現(xiàn)在的合作社及其他舉措的效力?
盧暉臨:當(dāng)年的制度設(shè)計(jì)有兩個方向,農(nóng)村的集體制度和城市的國有企業(yè),配合在一起構(gòu)成社會主義制度,它有系統(tǒng)的設(shè)計(jì),有一套系統(tǒng)的方法解決城市和農(nóng)村的公平發(fā)展問題。今天的合作社當(dāng)然是針對集體消亡之后農(nóng)村出現(xiàn)的問題,主要是小農(nóng)在面臨劇烈變化、具有破壞性的市場時的脆弱和無力,無論在銷售農(nóng)產(chǎn)品還是購買生產(chǎn)資料方面,農(nóng)民要在市場上有議價權(quán)。合作社是一個技術(shù)性的補(bǔ)救。如果真正能按照合作社的章程去做,那當(dāng)然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但是在現(xiàn)實(shí)中大量的合作社名不副實(shí),目標(biāo)沒有達(dá)成,變成農(nóng)村大戶利用制度設(shè)計(jì)獲取國家的投入的手段。合作社的目標(biāo)就算充分落實(shí),在解決農(nóng)民和農(nóng)村的問題方面,也是沒有辦法和集體制度比較的,潛在的空間比較小。
《南風(fēng)窗》:李昌平講過,90%的合作社都是假合作社。
盧暉臨:沒有準(zhǔn)確的百分比,但大部分是假的。這有一定的必然性,當(dāng)原有的實(shí)現(xiàn)共同發(fā)展的制度被瓦解之后,分散的小農(nóng)沒有辦法來保護(hù)自己的利益,沒有辦法阻止利益集團(tuán)和占有優(yōu)勢的大戶去扭曲國家保護(hù)小農(nóng)的政策。
《南風(fēng)窗》:可是問題總得解決,我們也知道真正重走集體化道路在現(xiàn)實(shí)層面是不可能的,但僅從理論層面來說,要通盤解決城鄉(xiāng)問題、農(nóng)民工問題、“三農(nóng)”問題,集體化是不是也是一種選擇?
盧暉臨:這個問題必須立足今天的現(xiàn)實(shí)來考慮,簡單地說回到集體制度,各種條件可能也不具備。可能首先要解決的是城鄉(xiāng)關(guān)系問題,怎么樣把“剝奪性的城鄉(xiāng)關(guān)系”建設(shè)成為“城鄉(xiāng)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模式,這比起農(nóng)村內(nèi)部制度更加重要。
《南風(fēng)窗》:一些堅(jiān)持了集體制度的農(nóng)村現(xiàn)在發(fā)展得挺好。根據(jù)你對河北的周家莊公社做的研究,周家莊的集體制度能堅(jiān)持下來并且得到了好的發(fā)展,從制度的角度做對了哪些事情?
盧暉臨:農(nóng)村的發(fā)展需要團(tuán)結(jié),從經(jīng)濟(jì)學(xué)上來講,團(tuán)結(jié)就有規(guī)模效應(yīng),能提高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效率,然后進(jìn)一步實(shí)現(xiàn)農(nóng)業(yè)之外的發(fā)展可能性。有一句話叫“無農(nóng)不穩(wěn)、無工不富、無商不活”,如果單純靠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可能吃飽肚子,但實(shí)現(xiàn)富裕的可能性很小。沒有集體的組織框架,農(nóng)村不大可能實(shí)現(xiàn)工業(yè)化,集體的組織方式為農(nóng)村提供了從農(nóng)業(yè)走向工業(yè),從生存到發(fā)展的可能性。為什么過去一些農(nóng)村在協(xié)作之后反而出來更大的問題?是因?yàn)楣芾硭讲桓撸蓡T的習(xí)性和制度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如果把這些問題解決好,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提高就比較快,這會為工業(yè)的發(fā)展打下基礎(chǔ)。傳統(tǒng)的小農(nóng)再能干,他不過是變成富農(nóng),不可能從整體實(shí)現(xiàn)對發(fā)展瓶頸的突破。
周家莊給我們的啟發(fā)就在這些方面,但是它現(xiàn)在面臨的危機(jī)也蠻大。今天的集體和過去不一樣,過去集體的外部環(huán)境是友好型的、支持性的,而現(xiàn)在是身處于市場經(jīng)濟(jì)的汪洋大海中間的孤島。
《南風(fēng)窗》:集體的邏輯也跟市場經(jīng)濟(jì)不同,在形勢緊張的時候,其他企業(yè)會壓成本,裁人,降薪,但集體不能這么做。
盧暉臨:沒錯。一些被我們視為集體制度的優(yōu)點(diǎn)的東西,到了市場經(jīng)濟(jì)的環(huán)境中就成了負(fù)擔(dān),比如要實(shí)現(xiàn)全部就業(yè),要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等。所以他們的生存是蠻不容易的。
《南風(fēng)窗》:你談到人性問題,在你的書里看到這個詞的時候,我是有點(diǎn)吃驚的,因?yàn)閷W(xué)術(shù)界仿佛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禁忌的。人性對制度而言有多重要?
盧暉臨:人性的問題其實(shí)蠻難討論,不存在抽象的人性。那種小生產(chǎn)者意識,每個人為自己、為家庭謀劃,追求家庭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的意識,今天好像是天經(jīng)地義的東西。但人性是歷史的產(chǎn)物,我們不應(yīng)該認(rèn)為理性人是一切制度的前提,這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假設(shè)。可是在集體制度誕生的時候,這就是作為小生產(chǎn)者的農(nóng)民的追求,集體制度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一批人和他們的行為傾向,這是歷史的產(chǎn)物,沒辦法。集體時期有一首歌,“公社就是常青藤,社員就是藤上的瓜,藤兒連著瓜,瓜兒連著藤,藤兒越壯瓜兒越大”。我覺得這個歌謠非常好,把集體和個人之間關(guān)系的理想設(shè)計(jì)非常形象地講出來了,我們應(yīng)該施肥,讓藤越長越壯,然后收獲更大更甜的瓜。然而,歷史形成的小生產(chǎn)者為自己謀劃為家庭謀劃的動力強(qiáng)過為全盤考慮,這是很普遍的現(xiàn)象。我只能說,任何理想的制度設(shè)計(jì)都必須面對歷史形成的人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