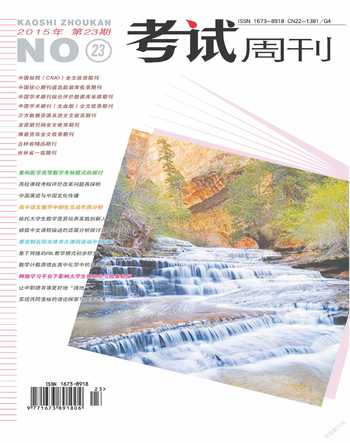以“災異”喻易代
李兵兵

陳壽(233—297年),字承祚,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北)人。少好學,師事譙周,在蜀漢曾任觀閣令史。公元268年,入晉為官,歷任著作郎、治書侍御史等職。280年,晉滅東吳,天下歸一,開始撰寫《三國志》,297年,陳壽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說:“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①于是晉惠帝令人到陳壽家中抄寫其書,藏之宮內,乃魏晉時期重要的史著之一。
對于陳壽著史的評價一直是中國史學史中不斷被討論的話題,諸多對陳壽的非議主要有三個理由:“毀諸葛亮之名”、“索米作佳傳”、“替司馬氏作曲筆”,對于前兩者學者多為之辯誣,但最后一條卻怎么也是抹不掉的②。陳壽的《三國志》在關系西晉統治者易代之事上多有曲筆,此舉多遭非議,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三國志多迴護》中列舉了很多,有兩個代表性例證:
司馬師廢齊王芳,《魏略》是這樣記載的:(司馬)師遣郭芝入宮,太后方與帝對弈,芝奏曰:‘大將軍欲廢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大將軍意已定,太后但當順旨。’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芝曰:‘大將軍何可見邪。’太后乃付以璽緩。’”是齊王之廢全出于司馬師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陳壽《魏紀》反載太后之命,極言齊王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其誣齊王而黨司馬氏亦太甚關。高貴鄉公曹髦被司馬昭黨羽成濟所殺,但《三國志·高貴鄉公紀》中只記載:“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③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到陳壽對司馬氏篡權的行為是極為迴護的,但筆者認為雖然陳壽在關于司馬氏篡權的記載表面上看起來曲筆嚴重,但通過對讖緯、災異的書寫隱晦地指出了這一事件。筆者發現《三國志·魏書·明帝紀》,尤其是《三少帝紀》中有大量關于“龍困井中”之象的記載,茲列列表如下:
從上表來看,整個《三國志》在《魏紀》中對“龍困井中”的異象記載多達9次之多,在二十五史中也是屬于最多的。那么,他究竟要說明什么呢?有什么蘊意呢?東晉時有著“鬼之董狐”⑦之稱的干寶,給我們道出了真相,他說:“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也,而不勝于金,黃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⑧之所以有如此多的此種異象,乃是“上者逼制”,隱晦地指出了上被下制。《三國志》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亦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⑨又《漢書·五行志》對此異象的直接解釋是:“劉向以為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⑩“幽執”乃囚禁遭難之意,所以,對司馬氏的迴護不攻自破。
王夫之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陳壽的著史面臨著在專制時代當朝人修當朝史的問題,陳壽作為降臣不得不小心翼翼。但我們看到,其實陳壽通過“龍困井中”這一“災異”之象,隱喻了易代之事,也是一位“鬼之董狐”。
注釋:
①房玄齡等.晉書·陳壽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②對于“因私怨毀諸葛”,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晉書》謂:“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被髡,故壽為《亮傳》,謂將略非所長。此真無識之論也。亮之不可及處,原不必以用兵見長。觀壽校訂《諸葛集》,表言亮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勵。至今梁、益之民,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過也。又《亮傳》后評曰:亮之為治也,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其頌孔明可謂獨見其大矣。”而“索米作佳傳”,此事最早記載蓋東晉裴啟的《語林》:“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又《晉書·陳壽傳》記載:“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借變成了索。又《三國志·曹植傳》記載“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陶懋炳先生說:“丁儀之子不存,陳壽米將誰求?索米之說,不攻自倒。”(參看陶懋炳.陳壽曲筆說辨誣[J].史學史研究.1981,3.),但“并其男口”的記載太模糊、不準確,《昭明文選》中唐李善注引《丁儀妻寡婦賦》曰:“含慘悴其何訴,抱弱子以自慰。”“弱子”尚存。此外,還有一些記載對陳壽的品行有懷疑。《晉書·陳壽傳》載“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沈滯者累年”;《晉書·陳壽傳》載“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但東晉常璩所著《華陽國志·陳壽傳》對此事的記載是:“(陳壽)遵繼母遺令,不附葬,以是見譏。”并非陳壽生母而只是繼母,并且是“遵繼母遺令”;又《華陽國志》記載:“王化與壽良、李宓、陳壽、李驤、杜烈同入京洛,為二州標俊。五子情好未能終。”蓋陳壽的為人不太拘小節,易遭人非議,當然也有可能是陳壽成書太倉促了。
③參看趙翼.廿二史札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4.
④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
⑤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三少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
⑥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三少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
⑦參看房玄齡等.晉書·干寶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4.
⑧沈約.宋書·五行志[M].北京:中華書局,1974.
⑨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三少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59.
⑩班固.漢書·五行志下之上[M].北京:中華書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