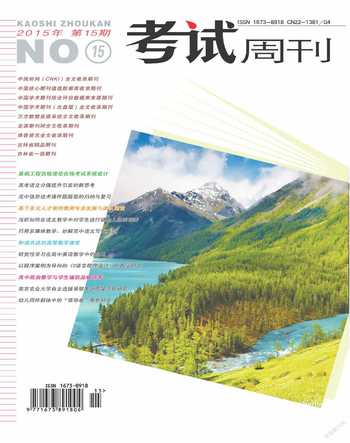“風流人物”花落誰家
錢忠福
摘 要: 文章從“去泛政治化”、“知人論世”、“還原本位”三個維度對《沁園春·雪》中的“風流人物”進行了解讀,這既是對教材教參“能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注解的一種質疑,又是對詞作者的一場“翻案”,希望通過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還毛澤東一個“風流人物”的偉人形象。
關鍵詞: 風流人物 文本解讀 《沁園春·雪》
自從教改以來,語文課堂的重心在不斷轉移,由最初的關注學生,以學生為主體逐漸向文本轉移,深挖文本,鉆研教材就成了時髦的專業術語。但是,對于文本的解讀,究竟要秉承一種什么樣的思想宗旨呢?我認為要尊重文學本身,還文本、還作者一個清白。筆者以《沁園春·雪》為例談文學作品的主旨解讀,有不當之處,還望有識者斧正。
筆者在講授《沁園春·雪》時,將“風流人物”解讀為毛澤東本人,遭到質疑,質疑者認為“風流人物”應該是“廣大人民群眾”,應該是“能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如果解讀為毛澤東本人,未免有損偉人形象(1945年本作發表后蔣介石就說毛澤東有“帝王思想”)。人教版語文九年級上冊教材也是這么注釋的,對此,我存有疑慮。
首先,對于文本的解讀,不宜落入“政治化”的俗套,用“政治”的眼光審視文學作品。1945年10月,重慶談判結束之后,毛澤東的這篇詞見諸報端。蔣介石看到后非常生氣,認為“毛澤東野心勃勃,想當帝王稱王稱霸”,遂命幕僚陳布雷組織國民黨御用文人對毛澤東的這種“帝王思想”展開批評。于是山城上下,引發了一場持續月余的《沁園春》“填詞大戰”。據不完全統計,毛澤東的詞刊發后不長時間里,國民黨控制的《中央日報》、《和平日報》《文化先鋒》、《益世報》等報刊,刊出以唱和為名,以相罵、歪曲為實的《沁園春》近30首[1],而發表在重慶各報的唱和之作就有300多首[2]。作為政治敵手,蔣介石的眼光是犀利而獨到的,但我們不是蔣介石,更不應該只看到作者的“帝王思想”,更何況,這首詞創作于1936年2月,離發表之時已有九年之隔。
其次,知人論世也許是了解作者情懷的有效途徑之一,更是有效解讀文本的重要途徑之一。《左轉·襄公二十七年》所記趙文子對叔向所說的“詩以言志”大概是最早提出的關于詩與詩人情懷的關系論述,《尚書·堯典》中堯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也就是說,“詩是言詩人之志的”,這個“志”的含義側重于指思想、抱負、志向。毛澤東是非常認可這個觀點的,他也是這么做的,他寫的“詩言志”的書法作品可以佐證。
毛澤東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深知底層百姓的疾苦。他讀了很多史書,深諳中國歷史上成王敗寇的“因果游戲規則”,更善于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他又較早地接受西方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故以拯救天下蒼生于水深火熱為己任,自然就成了他的理想。毛澤東青年時期的思想對其一生都有巨大的影響,或者說毛澤東一生都在為實現青年時期的理想而奮斗。這種歷史責任感和時代使命感決定毛澤東的一生是不平凡的。早在少年時期,毛澤東就有過“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的詩句。如果說當時的毛澤東借鑒了清末安徽名士程正鵠的詩句的話,那么他青年時期所做《沁園春·長沙》則一定是發自肺腑的。時年32歲的毛澤東去廣州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面對反動勢力的瘋狂鎮壓,工農革命運動卻在蓬勃發展,體現出“萬類霜天競自由”的態勢,毛澤東感慨萬千,中華民族的命運將走向何方,誰將成為主宰發展方向的力量?于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流瀉于胸。十年后,瓦窯堡會議的召開,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次年,毛澤東帶領紅一方面軍東渡黃河,取道山西,奔赴河北抗日前線。東征前夕,毛澤東在陜西清澗縣袁家溝視察地形,籌劃渡河時,眺望茫茫北方的大雪一口氣寫成這首氣吞山河的壯麗詩篇。十年前,還在“萬類霜天競自由”,十年后已是“欲與天公試比高”。可以這樣說,《沁園春·長沙》和《沁園春·雪》有著天然的互證關系,“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也許是“問蒼茫大地,誰主浮沉?”最藝術的回答[3]。
再次,對于文本解讀,應該遵從文本,尊重作者,從文本出發,又回歸文本。詞的下闋中抒懷對歷史英雄的惋惜。雖然作者對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這五位帝王的褒貶不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作者看來他們都是不完整的英雄,“惜”、“略輸”、“稍遜”、“只”等字可以佐證。“惜”肯定了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的英雄,又委婉地提出這些英雄的不足,批評他們短于“文治”。試問,作者的這種“批評”的力量源自何處?我想這與他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具有的豪邁氣概和堅定的信心是分不開的。但作者為什么偏偏選取這五位帝王?歷史上可以稱得上“英雄人物”的可謂數不勝數,他們之間有什么樣的內在關聯呢?筆者認為原因有三:其一,這些人物都是“草根英雄”,都是從社會的底層發展起來的,這些人物都有很好的“群眾基礎”;其二,這些“草根英雄”都曾稱雄于宏大的空間,是宏大空間的主宰者,都是歷史的創造者,都是某個朝代的開創者;其三,這些英雄都是一代代相繼崛起的,他們的崛起是建立在對前任的徹底推翻,他們是眾“英雄”中的一個個體。在個體的作用下發揮群體的效應,這個群體的價值才能得以體現。下文的“俱往矣”又不動聲色地對那些英雄個體予以全盤的否定,因為歷史的將永遠成為歷史,我們要著眼于當下,當今的“英雄”應該是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偉大的人,不僅有“武功”,還有“文治”,所以把這樣的人物稱為“風流人物”。當然,這個風流人物群體也是需要一個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這樣的一個個體來領導的,而此時的毛澤東正好具備這個條件。因為此時此刻的毛澤東,已經今時不同往日,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作為黨內領導人,此“風流人物”非他莫屬。在特定的創作瞬間,激情成就了一個傲視一切的“不可一世”的毛澤東。我們在閱讀時,讀出了毛澤東豪邁的氣概和強烈的自信。
最后,文本解讀在很大程度上受歷史階段、主流文化及文藝思潮的影響,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解讀。《沁園春·雪》主要經歷了三個解讀時期。1945年至1949年期間,國共雙方及進步人士圍繞著“風流人物”是否是“帝王思想”展開辯論,這是政治的需要。1949年至1978年,又將“風流人物”普遍理解為“無產階級”。1978年至2010年開始進入本體化的解讀,語文界更趨向于把“風流人物”理解為“毛澤東本人”。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錢理群先生在《名作重讀》中對《沁園春·雪》的全新闡釋,他認為“今朝”的“風流人物”當是“毛澤東自況”,詞作抒發的是作者早年立下的“集豪杰與圣賢于一身”的大志[4]。《語文教學通訊》刊有數篇文章,對人教社課下注釋“風流人物”的質疑,認為此處的“風流人物”應該是作者自況。
千言萬語,只想說“詩言志”應該還詩人一份自然。
參考文獻:
[1]鐘聲.毛澤東的詞《沁園春·雪》賞析[J].閱讀與作文,2008(03).
[2]黃小平,謝智香.《沁園春·雪》的互文性分析[J].時代文學,2012(03).
[3][4]林中港.文本解讀的六個層次——以《沁園春·雪》為例[J].語文教學通訊,2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