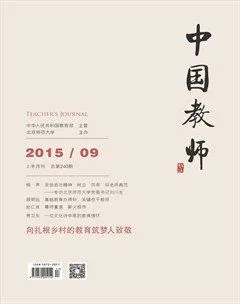尊師重道 薪火相傳
趙仁珪

我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小學生,當時在北京師范大學第一附小讀書。1978年國家恢復研究生學歷制度后,我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下文簡稱北師大)中文系的研究生,1981年畢業后便留校任教,從此便與北師大結下了不解的情緣,也和教育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我的父親是一名教師,我從小就覺得教師是一個很崇高的職業,別人小時候的理想都是當科學家、當醫生、當作家,我那時候就想當一名教師。我對教師的感情一直都很深,從小學、初中再到大學,我求學的過程中有幸遇到了許多位優秀的老師,他們對我的一生都有著很大的影響,因此,我對教師職業始終懷有一種敬意。
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教師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就是教學生怎么做人,特別是中小學教師,他們對孩子的成長起著關鍵的引導作用。我始終覺得人品不好的人肯定當不了好老師,人品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學問。我從教30余載,從中學到大學,教過的學生數以千計。對我而言,學生的事兒是天大的事兒,學生對我來說就是天。心里面有沒有學生,這是對一個教師合格與否的基本評判點。我在密云做中學老師的時候,還是“文革”期間,學校的教學無法正常進行,我跟學生說,現在的狀況是暫時的,你們千萬不要荒廢了時光,一定要多讀書。雖然我這樣做可能會讓自己惹上麻煩,但是為了學生,我還是要堅持指引他們正確的方向。很多學生聽了我的話,最后經過自己的努力都考上了大學,我也覺得問心無愧了。在北師大任教期間,對研究生的指導都是一對一的,經常有學生到我家里來請教問題,也有本科生,甚至是沒教過的學生登門拜訪,我都熱情接待,耐心指導。學生為了社團活動的事情找到我,我也是有求必應,盡我所能地幫助他們。不擺架子,跟學生說真心話,身體力行地指導、潛移默化地教育,多鼓勵、少批評,因材施教、注重學生的個性化培養,這些是我一直堅持的教學原則,也都是得益于先生們對我的教誨與影響,特別是我的恩師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有一套自己獨特的教學方式,他稱之為“熏”。他對學生的教育特別注重從日常生活的些微小事入手,一點兒一點兒地生發出去,在看似不經意間闡發做人和做學問的道理。即使不是在正兒八經地上課,只是私下和學生閑聊,啟功先生也能聊出學問來。這種啟發式的教育,讓學生感覺特別親切,接受起來也更容易。而且,這種交流是一對一的,又特別有針對性,因此對學生的影響十分深遠,甚至會影響一輩子。先生對我們的影響,正如杜甫詩句所描繪的那樣,“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是親切的、深入人心的。啟功先生在世的時候,家里每天都是訪客盈門,有的時候里面有人交談著,外面還有人在排隊等著。來拜訪的客人里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也不乏位高權重之人,但啟先生總是會優先接待學生,不管多忙,他都會耐心地對學生進行細致入微的具體指導。
我們是“文革”后北師大的第一屆古典文學研究生,當時師資嚴重不足。啟功先生除了系里安排的課外,還額外給我們加了一門課,講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他認為這是古典文學入門的重要工具,中文系的學生必須要了解,但學校教室排不開,啟先生也不計較,就專門跑到學生宿舍來給我們上課。那個年代學生宿舍條件相當艱苦,房間里擺了四張上下鋪的床,剩下的空間幾乎只夠放一張桌子。我們那屆有9個研究生,聽說啟先生要來宿舍講課,其他專業的學生還有年輕的教師都跑來“蹭課”,四張雙人床上擠了十幾個人,有坐著的,有趴著的,有躺著的。啟先生也不介意,跟學生并肩坐在下鋪,在一種非常輕松、愉快的氛圍里給我們講課。除了版本目錄學的知識,啟先生也會講一些清代學術思想。教學形式也比課堂上靈活得多,大家有問題可以隨時提問,講累了,啟先生還會講點笑話調節情緒。那時候聽啟先生講課真是一種極大的享受!我們后來整理了一本《啟功講學錄》,里面的很多內容都是啟先生在宿舍里給我們講的。
啟功先生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出于對學生的愛。這些課程不是中文系教學大綱要求的內容,可以不講,但啟先生覺得學生有必要學習這方面的知識,便主動創造條件為學生開課。這種對學生的仁愛之心、對教育的熱忱態度,是特別值得我們后輩學習的。
我1981年畢業后留校,在中文系任教,與啟功先生的交往自然又多了一些。那時候啟先生年紀大了,我經常到他家里去幫他送信件或者協助他處理一些事情,我自己也很珍惜每一次與先生接觸的機會。受啟功先生影響,我自己也搞點詩歌創作,啟先生每次看到我的習作都特別高興,當面就給我批改,也有的時候拿回去改了再還給我,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也算偏得了一些啟功先生的“獨門秘籍”吧。如果教古典文學的教師自己連古文都不會寫,那他就只能是很膚淺地照本宣科,因為他對創作沒有深切的體會,沒法跟學生說明為什么同樣一個題材,有的人寫出來流于俗氣,有的人寫出來卻格調高雅。別的人怕辛苦,不動筆,但是我一直堅持創作,如果說啟功先生對我有一些偏愛,大抵也有這方面的原因。
啟功先生有一些事情也會找我幫忙,最初是協助整理鐘敬文先生的詩稿。鐘先生不光是民俗學大家,還是一位詩人。他的詩歌都是隨性而發、信手寫在小紙條上的,長年累月積攢了一麻袋之多。鐘先生委托啟先生找一個學生幫忙整理,于是我承擔了這樣一個工作。之后,我為啟功先生的《論書絕句》作注,在作注的過程中收獲很大,后來便主動請纓為先生的詩集《啟功韻語集》作注。整理書稿的這段時間,我常常到先生家里去當面討教。很多時候都是在晚上,一燈如豆,萬籟俱靜,和先生促膝而坐,聆聽先生教誨,無拘無束,如沐春風,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在我的后半生能投到先生門下,追隨先生,是我今生最大的幸事!
1997年,北師大為迎接95周年校慶,廣泛征集校訓。啟功先生最初擬的是“師垂典則,范示群倫”,這幾個字雖含義雋永,但讀起來稍嫌艱深,經反復推敲,最后定為“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八個字不僅比原來的更平易通暢,也更深刻蘊藉,它不但緊扣“師范”二字,而且包含了學與行、理論與實踐、做學問與做人、做一般人與做教師之間的辯證關系。這八字校訓十分精練地詮釋了“師范”的意義,亦頗具大師的品格精神與氣度風范。校方敦請啟先生賜墨勒碑,先生欣然奉命,然而先生并沒有把校訓當成自己的專有創造,而只把自己當成學校的普通一員,因此,在校訓碑正面右首署“北京師范大學校訓”,落款逕書“啟功敬書”。一個“敬”字足以見先生之高風亮節,著實令人欽佩。
啟功先生生前曾多次提起自己的恩師、原北師大的老校長陳垣先生對他的提攜與栽培,《啟功叢稿》的第一篇文章《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寫的就是陳垣校長。陳校長特別關照、愛護啟先生,有些人反對啟先生,說他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陳校長卻三次將他請到輔仁去教書,所以啟先生特別感激陳垣校長。陳校長在具體的教學上對啟先生也有很多指導,啟先生曾說“如果說予小子對文化教育事業有一滴貢獻,那就是這位老園丁辛勤澆灌時的汗水”,啟先生的造詣和成就確實也得益于陳校長的教誨和影響。可以說,“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八字校訓,也是啟先生從陳垣校長等老一輩優秀教育工作者身上總結提煉出來的。啟功先生對后輩的教誨也是在傳承陳校長的精神,他想把陳校長身上的優秀品質作為精髓傳遞給后人。我們這一代也一直在盡力學習繼承,“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教師是一個崇高的職業,是國家的棟梁和希望,肩負著培養下一代的責任。要培養好下一代,我們不光要把最好的建筑留給學校,更需要把最好的人才留給學校,讓一流的人才源源不斷地補充到教師隊伍中去,應該在全社會更加提倡尊師重道,加大對教師的培養,給教師更多的發展和提升空間。現在年輕的教育工作者,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應該有更高的追求。如今時代不同了,大家都對物質有一定的追求,這無可厚非,但作為教師,不能把物質追求作為唯一的人生目標,即便沒有物質上的豐盛,也仍然要堅守教師的本分與職責。我們身邊有很多這樣的楷模,前輩中有,當代也有,年輕的教育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學習,傾畢生心血于學術,注滿腔熱忱于教育,薪火相傳,澤被后人。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江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