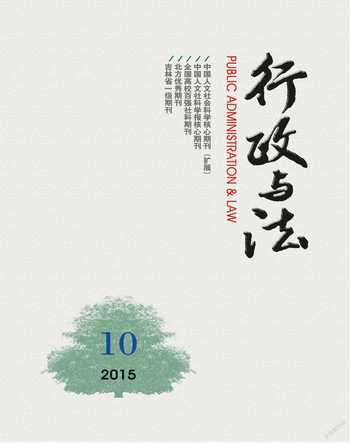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研究:文獻回顧與評價
摘 要:街頭官僚是政策執行的核心主體,研究街頭官僚對于改善并提高政策執行能力有重要作用。利普斯基的街頭官僚理論全面闡述了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中所扮演的角色、面臨的工作環境及其行為模式。而后續的研究在街頭官僚的裁量權、人格特征、組織結構、顧客特征以及街頭官僚的控制等方面對利普斯基的觀點進行了修正和拓展。本文認為,當前學界對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尚存在局限性。
關 鍵 詞: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利普斯基
中圖分類號:D63-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07(2015)10-0001-06
收稿日期:2015-06-25
作者簡介:李宜釗(1977—),男,福建永春人,海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公共政策分析、地方治理。
基金項目:本文系海南省教育廳高校科學研究資助項目,項目編號:Hjsk2012-13;海南大學青年基金項目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qnjj1103。
街頭官僚概念的提出源自利普斯基。1977年,利普斯基發表了題為《走向街頭官僚理論》的論文,首次提出了街頭官僚概念。在這篇文章的基礎上,利普斯基又于1980年發表了《街頭官僚:公共服務中個體的兩難困境》一書,全面闡述了街頭官僚理論。該書在政策研究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利普斯基也因此被視為自下而上的政策執行政府模式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根據利普斯基的觀點,街頭官僚是指在工作過程中與公民直接聯系,且在執行工作時擁有大量裁量權的那些公共服務工作者,[1]比如學校、警署、福利部門、低級法院、法律事務所等組織中的工作人員。[2]根據這一界定,街頭官僚表現出三個基本特征:第一,街頭官僚是公共服務的工作者,但并不一定就是政府官員,如教師。第二,街頭官僚是與公民直接產生聯系的人員。這與我們通常理解的基層官員有區別,如雷納在討論警察概念時,專門對“街面警察”與“管理警察”在功能上的區別作了說明。[3]前者指處理實際問題的警察,屬于街頭官僚范疇;而后者雖屬基層官員,但并非街頭官僚。第三,街頭官僚擁有大量的裁量權。裁量權是指“決定某種行為適當性以及將該行為付諸實施的一種能力與責任”。[4]街頭官僚的裁量權一方面源于法律與政策的特征,即“無論政策和規則如何詳細,現實的復雜性與多變性都將遠遠超出規則制定者的想象力”;[5]另一方面則源于信息的不對稱。因為“行政裁量在互動之間是不可避免的”,[6]當與上級官員和公民發生互動時,街頭官僚往往處于信息優勢一方,從而街頭官僚便有可能脫離組織權威的約束與控制,從組織權威中獲得自主性空間。可見,街頭官僚是政策執行中的核心主體,研究街頭官僚如何執行公共政策,對于改善并提高政策執行能力有著重要的作用。
一、街頭官僚的政策執行:
利普斯基的觀點
(一)街頭官僚:執行者與決策者的雙重角色
在利普斯基的街頭官僚理論中,街頭官僚雖然僅僅是公共服務部門中最低層級的人員,但事實上他們卻是公共服務的實際建構者。這種建構的累積,甚至可以直接成為或者等同于實際的公共政策本身。[7]因此,街頭官僚在公共政策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即他們在執行政策的同時也扮演著實際的政策制定者的角色。這使得公共政策的成敗可能掌控在街頭官僚的手中,而不是高層決策者與管理者的手中。
街頭官僚扮演的實際政策制定者角色,建立在其職位的相互聯系的兩個層面之上:相對較高程度的裁量權,以及來自組織權威的相對自主性。[8]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街頭官僚所擁有的這種裁量權與自主權能夠影響政策的產出。
裁量權是利普斯基街頭官僚理論的核心概念。利普斯基認為,裁量權是街頭官僚的基本特征,而較大幅度地減少這種裁量權往往比較困難。原因如下:一是街頭官僚的工作環境往往都很復雜,以至于街頭官僚無法根據固定的規則或政策來決定他們的行為;二是街頭官僚的工作環境往往需要其對情境中的人性層面作出回應;三是街頭官僚必須與公民進行互動,并在互動中獲取尊嚴與權威,從而促成國家的合法性。[9]相對自主性是街頭官僚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概念。多數學者認為,街頭官僚將會按照上級的要求執行公共政策。這種觀點是建立在街頭官僚在組織行為中將采取合作模式的假設基礎之上的。但事實表明,在命令與執行的產出之間總是存在差異。當街頭官僚與管理者之間目標不一致時,街頭官僚將產生集體的不合作策略,如玩忽職守、刻意的破壞行為以及在工作中表現出消極的態度。[10]其深層原因體現在街頭官僚與管理者之間關系的特征上。一方面,兩者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沖突。街頭官僚希望能夠快速地處理大量的事務,同時也希望能夠減少工作中的危險和不適,因此其角色的定位就將是盡量擴大自主權;而管理者所感興趣的則是能夠達成與組織目標相一致的結果,因此其角色定位就將是盡量減少街頭官僚的自主權。[11]另一方面,街頭官僚與其管理者之間也存在相互依賴的關系。街頭官僚需要管理者的支持,從而使得其工作更為輕松和令人向往;而管理者能力的展現和管理目標的達成,則需要依賴于街頭官僚的裁量權與實際決策者的角色,兩者是一種互惠的關系。[12]因此,利普斯基總結道,關于政策執行的一般假設,即認為權威會自動地自上而下流動,并使得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中將采取合作的模式,必須受到質疑。從而將分析的視角轉換到街頭官僚的工作情境中來。[13]
(二)工作環境: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困境的根源
街頭官僚在執行政策過程中重新建構了公共政策,從而扮演著執行者與決策者的雙重角色,這是由其在執行政策過程中面臨的困境所決定的,而這種困境則與街頭官僚的執行環境密切相關。街頭官僚的政策執行環境包括資源、目標以及與顧客的關系三個方面。
首先,街頭官僚通常是在資源十分有限的情境中執行政策的,如決定時間的緊迫、信息獲得的困難、人力資源的不足以及可用資金的限制。其原因在于街頭官僚組織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著互動關系:當管理者試圖通過增加供給以滿足公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時,需求會隨著供給的增加而增加。[14]這一命題可以為街頭官僚所提供的服務質量難以改善的情況作出解釋:一是如果街頭官僚的資源充足,其首選是增加服務的數量而非質量;二是街頭官僚通過更多的資源以改善服務的質量,這一說法是不可信的;三是即使可以通過減少工作的數量以提高質量,這種質量的提高也是不明顯的。[15]
其次,街頭官僚的工作目標在本質上是沖突和模糊的。具體表現為:一是以顧客為中心的目標與社會運作目標之間的沖突,二是以顧客為中心的目標與組織目標之間的沖突,三是街頭官僚本身的目標與公眾對街頭官僚的社會期待之間的沖突。[16]目標的沖突與模糊是造成對街頭官僚工作績效進行評價困難的最為重要的因素。因此,利普斯基認為,街頭官僚組織工作的績效難以量化評估,這使得街頭官僚組織無法進行自我矯正,而對績效的界定也呈現高度政治化的特點。[17]
第三,街頭官僚所面對的顧客往往是非自愿性的。非自愿性有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像警察部門這種具有強迫性質的公共機構,其顧客具有顯而易見的非自愿性;二是在表面上看,顧客是自愿接受街頭官僚的服務,但實際上除了接受公共服務之外,街頭官僚的顧客并沒有其它選擇,比如福利機構所面對的低收入人群。[18]這導致了街頭官僚與顧客之間的關系呈現“單邊權力”特征。[19]在這一權力關系中,街頭官僚通過利益分配與制裁、顧客與街頭官僚及其組織之間互動關系的建構、對顧客角色扮演的教導、對顧客心理層面的獎懲等方式,社會性地建構了顧客的概念,從而在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有效地控制顧客。[20]
(三)走出困境: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邏輯
工作環境的特征決定了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中往往要面臨大量的困境和不確定性。[21]從而,街頭官僚將發展出一系列有效的機制或模式,以回應其在工作上所面臨的困境與不確定性。[22]這些機制或模式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街頭官僚的政策執行。
對街頭官僚而言,應對不確定性的方式是通過發展某些行為慣例以限制顧客的需求,從而最大化地利用可得資源,并獲得顧客的服從。如通過提高服務成本的方法來限量供應免費的公共福利,從而控制顧客的數量,簡化自己的工作;或者通過分類的方法來區分顧客,并以此為依據提供有差別的公共服務,從而減少自己的工作量。街頭官僚發展出的行為慣例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為了簡化并控制街頭官僚復雜的工作情境,從而有助于街頭官僚限量供應公共服務;控制顧客并減少不確定性所造成的后果;節約工作資源等。[23]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街頭官僚所遵循的這些行為慣例幾乎等同于其所執行的政策,[24]這是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基本邏輯。有學者將該邏輯稱為生存的邏輯。[25]
當街頭官僚通過行為慣例來執行政策時,將與社會對公共服務的期望產生較大的差距。因此,街頭官僚將面臨一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并不得不進行心理調適,以使其能夠適應街頭工作。這種心理調適同時也是街頭官僚回應環境不確定性的行為策略:一方面,街頭官僚可能通過修改其工作的概念來調解其工作能力與組織目標之間的緊張關系。如在心理上抽離其所從事的工作,從而拒絕為組織的表現承擔個人的責任;降低工作目標;避免將工作看作一個整體;否認裁量權等。[26]另一方面,街頭官僚往往通過修改對于顧客的看法,尤其是通過區分顧客以重新建構顧客的概念,使其覺得如果沒有工作結構的限制他們也有能力服務好顧客。這不僅使街頭官僚的自尊心免受打擊,同時也可以在其內心里將造成工作困境的原因歸結到顧客身上,從而將工作的責任外推給顧客。[27]
二、后續研究:對利普斯基
觀點的修正與拓展
自利普斯基正式提出街頭官僚理論以來,眾多學科紛紛對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也對利普斯基的理論進行了修正和拓展。從整體上看,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
第一,街頭官僚的裁量權與規則的關系。裁量權與規則是相關聯的:規則詳細說明了街頭官僚的責任和義務,而裁量權則賦予他們行動的自由。Bull強調,街頭官僚的裁量權內嵌于規則結構之中,并造成了政策和法律的差異性。[28]組織社會學者根據街頭官僚工作的復雜程度和責任委托之間的關系來研究裁量權。Hupe與Hill認為,無論規則從何而來,規則總是無法自發執行的;規則可能是模糊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同時行動者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因此行動者就只能在一般規則與特定情境之間、規則與規則之間進行選擇。[29]Veen從規則的特征、執行組織的結構、民主控制的實踐方式以及街頭官僚的工作環境等四個方面探討了裁量權的來源。[30]DiMaggio等則強調,專業化可以提供街頭官僚的自主性及其合法性,因為他們可以借專業性的特點來界定其工作方法和工作條件。[31]其基本觀點是:街頭官僚的工作特點需要裁量權,而裁量權則賦予了街頭官僚政策執行中的自主性。不過,爭議仍然存在。例如:Ellis的研究認為,街頭官僚裁量權空間的大小與是否采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方法緊密相關,而與其它因素關系不大。[32]
第二,街頭官僚的人格特征與政策執行的關系。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曾冠球以臺北市十二個區公所的行政人員為調查對象,定量地探討了街頭官僚和人格特征對行政裁量權的影響。其結論是街頭官僚人格與行政裁量權直接相關。[33]Hill也認為,官僚人格與組織行為間的關系是一個可供觀察的切入視角。[34]官僚人格具有普遍化的特性,而街頭官僚作為官僚類型之一也包含了這些特點。Hummel則從精神分析學的角度闡述了組織結構對官僚人格的塑造,即官僚體系透過層級節制來壓抑個人良知,同時以分工來控制員工的自我控制權,自我因而逐漸地喪失對事物是非與對錯的判斷能力。[35]不過,斯科特的研究發現,街頭官僚的人格特征是一個影響最小的因素。[36]這與其他人的研究觀點并不一致。
第三,組織與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關系。Riccucci探討了組織績效評價體系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福利政策執行過程的影響。作者發現,當福利政策目標由現金資助向幫助貧困人員培養工作能力甚至找到工作轉變時,由于組織中對街頭官僚的績效評價體系沒有發生相應變化,街頭官僚們仍然按照其原來的工作方式(即貧困者的資格審查)來執行福利政策。[37]曾冠球分析了組織領導風格對行政裁量權的重要影響。[38]斯科特探討了組織控制程度對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影響。而科利則認為,組織文化中強調的價值影響著組織結構的特征,從而影響和制約著官僚的裁量權。[39]我國學者在分析中國農村基層政府行為時,提出了壓力型體制這一組織特征對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決定性影響。[40]歐博文和李連江則分析了“下管一級”制如何使街頭官僚與組織管理緊密相連,而離社會壓力越來越遠,從而推動了不受歡迎政策的執行。[41]
第四,顧客特征與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關系。利普斯基認為,街頭官僚的顧客是非自愿性的,因此,顧客對公共服務的需求通常是無法選擇的。在這種情況下,街頭官僚利用其裁量權發展出一套方法和技術,以規范顧客的行為。從這個角度上看,似乎是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建構了顧客的行為。[42]不過,更多的文獻卻表明,顧客的特征會影響街頭官僚的政策執行。皮索討論了顧客的合作程度對街頭官僚行為的影響。他對基層的兩個組織結構相當類似的福利機構中街頭官僚行為的研究發現,顧客的合作狀況而不是街頭官僚的態度本身決定了福利機構的政策執行結果。當顧客與街頭官僚積極合作減少了他們的負擔時,街頭官僚就會提供較好的服務;而當顧客不合作從而加大了街頭官僚的負擔時,他們就不會提供良好的服務。[43]馬拉登卡等則討論了顧客需求表達能力的影響情況。他們分別對圖書館的公共服務與黑人居住地的垃圾回收服務進行了研究,認為在街頭官僚提供公共服務時,不同的顧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的不同是影響公共服務質量的主要因素;那些表明自己有很高需求的當事人通常會獲得很高比率的福利。[44]換言之,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結果與顧客需求表達能力相關。
第五,對街頭官僚的控制。針對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中因裁量權而導致的一系列問題,學者們提出了有關控制的一些建議。現實中的控制措施主要是通過制定工作手冊、績效評價以及明確街頭官僚行動目標等方式,以減少街頭官僚的自由裁量權。但是,這些措施卻往往被證明是無效的。[45]管理者與街頭官僚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或許是主要原因。[46]為此,利普斯基最早曾提出增加人手能夠減少街頭官僚的對抗行為。[47]但這一觀點很快便被他自己推翻,因為人手的增加永遠趕不上顧客需求的增加。[48]Bovens與Zouridis探討了信息技術對街頭官僚裁量權的影響,指出在新技術條件下,街頭官僚將轉變為系統官僚,即街頭官僚原有的自主性將移交給系統設計員。通過技術發展,可以控制街頭官僚的裁量權。[49]法律在控制方面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合法性原則、發展公民權利、進行政策管制以及司法訴訟的途徑。[50]同時,倫理和責任的控制也被廣泛提及。[51]
三、簡要評價
在裁量權的衡量中執行公共政策,這是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研究的核心。街頭官僚擁有裁量權并通過裁量權重構其所執行的政策,是街頭官僚執行政策過程中的必然現象,是無法完全消除的。也因此,公共政策的執行效果在某種程度上便取決于街頭官僚基于裁量權的行動選擇。可以說,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研究者們試圖通過考察街頭官僚在特定情境下的主觀心理狀態,來解釋其執行過程中的行為邏輯。這是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研究的重要貢獻。街頭官僚理論也因此被看作是第二代政策執行理論的典型代表。
然而,與其他所有理論一樣,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也存在許多局限。其一,與其他自下而上的政策執行模式一樣,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忽略了決策者、管理者的影響,將政策執行看作是完全由街頭官僚理性選擇的結果。事實上,決策者與管理者對街頭官僚的政策執行雖然沒有決定性的影響,但將其忽略則無法反映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實際狀況。其二,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無法解釋街頭官僚的所有行為。穆蒂和雷蘭德的研究發現,那些認為街頭官僚運用裁量權使其工作變得舒適和安全的觀點只是描述了一部分而非全部的街頭官僚行為;某些街頭官僚是非常負責任的執行者,這些街頭官僚的決策常常使得其工作變得更加艱難,甚至對他們的職業安全構成了威脅。[52]正是在這個意義上,Moore認為將決策過程的其他維度排除在外,所看到的將只是街頭官僚政策執行的部分圖景。[53]其三,街頭官僚政策執行問題的研究從工作環境的角度來解釋街頭官僚的行動選擇,認為環境使街頭官僚面臨各種壓力,為緩解壓力,保證其行動的舒適和安全,街頭官僚在政策執行過程中重構了公共政策。其隱含的假設是將街頭官僚看作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個體。顯然,這種假設是有爭議的,它簡化了現實中人的復雜心理狀態和行為模式。事實上,現實中街頭官僚的行動不僅是對個體生存的理性反應,同時也是對許多其它環境的反應,如組織因素、社會互動因素等。
【參考文獻】
[1][2][7-24][26][27][45][48]LIPSKY M.Street-level Bureaucracy[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
[3]羅伯特·雷納.警察與政治[M].易繼蒼,朱俊瑞譯.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
[4]BOOTE D.N.Teachers’ Professional Discretion and the Curricul[J].Teachers and Teaching:Theory and Practice,2006(4):461-478.
[5][49]BOVENS M,ZOURIDIS S.From Street-level to System-level Bureaucricie[J].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2002(2):174-184.
[6]戴維·羅森布魯姆,羅伯特·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學:管理、政治與法律的途徑[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25]米切爾·黑堯.現代國家的政策過程[M].趙成根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4.
[28]BULL D.The Anti-discretion Movement in Britain:Fact or Phantom?[J].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 Law,1980(3):65-83.
[29][30][42]HUPE P,HILL M.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J].Public Administration,2007(2):279-299.
[31]DIMAGGIO P.J,POWEL 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 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3):147-160.
[32]ELLIS K,DAVIS A,Rununery K.Needs Assessment,Street-level Bureaucracy and theNew Community Care[J].Social Policy&Administration,1999(3):262-280.
[33][35][38]曾冠球.基層官僚人員裁量行為之初探:以臺北市區公所組織為例[J].行政暨政策學報,2004,(03):95-140.
[34]HILL M.The Policy Process in the Modern State (3rd)[M].N.Y.:Prentice Hall,1997.
[36][39][46][50[52]馬駿,葉娟麗.公共行政學理論前沿[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37]Riccucci N.M.How Management Matters: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Welfare Refor[M].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05.
[40]榮敬本等.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轉變[M].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41]O'BRIEN K.J.LIANJIANG L.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J].Comparative Politics,1999(2):167-186.
[43]詹姆斯·Q·威爾遜.官僚機構:政府機構的行為及其原因[M].孫艷譯.三聯書店,2006.
[44]查爾斯·T·葛德塞爾.為官僚制正名——一場公共行政的辯論[M].張怡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
[47]WEATHERLY R,LIPLKY M.Street-level Bureaucrat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Implementing Special-education reform[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1977(2):171-197.
[51]韓志明.街頭官僚的行動邏輯與責任控制[J].公共管理學報,2008,(01):41-48.
[53]SCOTT T.MOORE.The Theory of Street-Level Bureaucracy:A Positive Critique[J].Administration&Society.1987(1):74-94.
(責任編輯:劉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