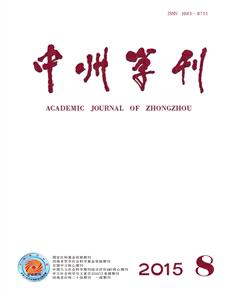西周早期周王室對“南國”的戰略部署初探*
樊 森
“南國”一語金文常見,如中方鼎“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①,禹鼎“噩侯馭方率南淮夷、東夷,廣伐南國、東國”②,晉侯蘇鐘“隹王卅又三年,王親遹省東國、南國”③等。朱鳳瀚先生考證“南國”應“東起今江蘇北部,經今安徽北部、河南南部之信陽地區南部,西抵今河南西南部之南陽地區南部,西南抵今湖北北部地區,大致即在今江蘇和安徽境內之淮水流域、今河南境內之淮水以南地區、南陽盆地南部與今湖北北部之漢淮間平原一帶”④。在這片廣大區域中居住著南淮夷、徐方等多個部族,作為西周王朝經濟和人力資源的重要來源,⑤對周王室具有重要意義。而漢淮平原,因為是周人掌控“南國”的中間地帶,則成為西周早期王室經略南方的重點區域,對周人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對這一區域的解讀對于掌握西周政治地理格局、了解周王室與南方民族關系意義顯著。朱鳳瀚先生指出周人在武王克商后不久就已確立了控制南國西部區域的“戰略部署”⑥,但限于材料,學界對于西周早期這種“戰略部署”的具體安排不甚清楚。近年來,隨著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墓、文峰塔東周墓等一批新出銅器銘文材料的公布,使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探索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本文認為西周早期主要是通過在漢淮平原交叉安置同姓兄弟之國和異姓舅甥之國的方式,來實現其南疆軍事屏障的建立。下以西周早期同處于隨棗走廊要沖之地,且比鄰而居的曾、噩兩國為例,⑦結合近年來的考古資料作簡要分析,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曾、噩兩國的族屬及其與西周王室的關系
1.曾國族屬及其與西周王室的關系
曾國的族屬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長期未有定論,2013年湖北隨州市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M111出土的方座青銅簋為該問題的解決找到了新的線索。該青銅簋為“曾侯犺”自作器,銘作:
犺乍剌考南公寶尊彝。⑧
從銘文的稱謂看,此簋應是曾侯犺為其父輩“南公”所作之器。其中的“南公”二字,恰可與2009年隨州市文峰塔東周墓出土曾侯□編鐘銘文相聯系。曾侯□鐘M1:1正面鉦部和左鼓的部分文字系連后為: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曰:伯適上/帝,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奠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⑨
曾侯□鐘M1:3正面鉦部和左鼓的部分文字系連后為:
惟王十月,吉/日庚午。曾侯/曰:余/稷之玄/孫⑩
M1:1“伯適上帝”中的“帝”字,李零先生認為應讀為“禘”,即祭祀祖宗之禮,“伯適上帝”意指南公適為曾侯始祖。[11]M1:3中“稷”,即周人先祖后稷。“玄孫”指自身以下的第五代,《爾雅·釋親》:“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12]也可泛指遠孫,《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有渝此盟,明神殛之,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13]
從M1:1曾侯□的追思中可知其先祖為“南公”,從M1:3中可見曾侯□稱自己為“稷之玄孫”,那么綜合曾侯□鐘銘和曾侯犺簋銘,可以推知西周早期的曾侯犺與東周時期的曾侯□同宗,也應為“稷之玄孫”。曾侯既為周人先祖后稷之遠孫,那么曾國的族姓自然為姬姓無疑。
確定了曾國的族屬后,我們再看其與西周王室的關系。M1:1“伯適上帝,左右文武。達殷之命,撫奠天下”說曾侯先祖南公適曾經輔佐文王、武王討伐殷紂,建功立業。“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中“汭土”為兩條水系匯合之處,此處應該是指隨州漂水、涢水的匯流位置[14],“庀”為治理[15],四句連起是說周王因為南公輔助有功,特將其封于曾地,令其肩負起治理淮夷,監視江夏的重任。據此可知,隨州之曾應是西周王室防范淮夷而分封的同姓諸侯國,這正是“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16]的真實反映。
2.噩國族屬及其與西周王室的關系
噩國由來已久,“噩”文獻作“鄂”,《戰國策·趙策》記魯仲連語“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17],《史記·殷本紀》亦記紂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18]。噩侯在商代已位列三公,可見噩國地位重要、影響巨大。噩國姞姓,噩侯簋銘記載:“噩侯乍王姞媵簋,王姞其萬年子子孫永寶。”[19]姞為黃帝之姓,《國語·晉語》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20]唐蘭先生將噩侯簋的時代定為穆王時期[21],噩侯嫁女與周王室,這反映出西周早期噩與周之間的姻親關系。婚姻在周人看來向有和“兩姓之好”的政治作用,《禮記·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故君子重之。”[22]而《左傳·宣公三年》中記石癸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23]更是反映了姬姓的周與姞姓的噩世有聯姻的歷史事實。周人通過聯姻拉攏勢力強大的噩國助其防守南方,正體現了陳鵬先生《中國婚姻史稿》中“武王克商,首封同姓為兄弟之國,以‘藩屏王室’。繼之以婚姻結異姓諸侯,使化為甥舅,以資弼輔”[24]的論斷。
綜上可見,無論是同姓分封還是異姓聯姻,周人確在西周早期使得曾噩兩國成為其南方屏障。
二、從相關銅器銘文看曾、噩兩國拱衛周疆的具體表現
1.西周南方的軍事重鎮
藏于日本出光美術館的靜方鼎部分銘作:
隹十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或(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室,令靜曰:“司女采,司/才(在)曾噩師。”[25]
銘文記載周王南巡前,先遣中和靜省南國的史實。同樣的記錄也見于“安州六器”的“中甗”,其部分銘作:
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設/居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中省自方、登、造□邦,在噩/師次。[26]
由中甗、靜方鼎銘文,可以得到兩點重要信息:
其一,曾噩兩國皆有“師”。《國語·魯語》記載:“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27]陳恩林指出《魯語》所說的“元侯”,又可稱為“方伯”。[28]而“方伯”之所以能夠組建軍隊,是為了代表周天子坐鎮一方,起到拱衛周室的藩屏作用。綜合曾噩兩國有“師”的事實與曾侯□鐘銘中“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的記載,我們就能清楚地了解曾、噩兩國作為西周南方軍事屏障的重要地位。
其二,中和靜受命于王,在省視南國“小大邦”的途中于曾“設居”,“在噩師次”。周王的先行官在巡行南方各國時,選擇在曾、噩兩國,特別是噩國軍營中停留駐扎,除了表明曾、噩兩國在西周早期均為周王倚重和信任的南方軍事重地外,還與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有關。朱鳳瀚先生指出西周初年王室為經營南國西部漢淮區域間的局勢,刻意在其南部邊域分封了一批重要封國,自西向東分別是“曾、噩(約在今湖北隨州),厲(隨州北)、呂(今河南南陽),申(今河南唐河以北),應(今河南平頂山西),滕、薛(均在山東滕州),蔡(今河南上蔡西南)”[29]。觀察這些封國的所在位置可知,曾、噩、厲三國所處的隨州區域已經深入到南國的西部區,而在三國以南、以東的廣大地界再無西周封國,如此則曾、噩等國的邊境軍事要塞地位就不言自明了。
2.周人南方“金道”的經濟護衛
張光直曾經指出“沒有青銅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沒有銅錫礦,三代的朝廷就沒有青銅器”[30]。西周時期的青銅器冶鑄原料主要來源于南方,稱“南金”,《詩經·魯頌·泮水》有“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31]的記載。“南金”輸入道路的暢通與否對于周王室來說意義重大。
曾伯漆簠中就記有曾國參與戰爭、護衛周人南方“金道”的重要史實,該器部分銘作:
……曾白漆慎圣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方……[32]
“元武孔黹”是指曾伯其人義氣和威武十分彰顯[33];“印”,應為“抑”之本字,可理解為“安”。“燮”為“和”,《爾雅·釋詁》曰:“燮,和也。”[34]《尚書·洪范》有“燮友柔克”[35],《尚書·周官》有“燮理陰陽”[36]。“繁湯”,地名,屈萬里先生認為“繁湯”當是“齊、魯、鄫、杞、滕、邾、宋、陳等國往淮南的孔道,也就是輸入南金的重地”[37]。“金道”“錫行”互文,均指銅錫運送的道路。“卑”通“俾”,“使”義。“方”,“常”義,《禮記·檀弓》有“左右就養無方”[38]語,鄭注曰“方,猶常也”[39],或解為“有之”義,《詩經·召南·鵲巢》“維鵲有巢,維鳩方之”[40],《傳》曰“方,有之也”[41]。“克狄淮夷,印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卑方”是說曾伯打敗淮夷、安順繁湯,使運送銅錫的道路得以通暢。吳其昌、劉節等先生將該器定為周宣王時期[42],認為“克狄淮夷”應指宣王討伐淮夷之事。由銘文可見周室征討淮夷,曾國不僅參與其中,而且為打通“金錫”之道立下了卓越功勛。
這一點也可以從葉家山出土發現中找到相關材料。葉家山M28曾侯墓出土了一圓一方兩塊青銅錠,這兩塊銅錠的材質與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遺址出土的銅錠相似,故其應為銅器原料[43]。兩塊銅錠出土時均位于墓室二層臺,與禮器同置。銅料入葬且與禮器共同放置,可以反映出曾人對銅料的重視程度。而從曾國自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均表現出的與南方銅源的密切關系上,我們可以猜測周人分封同姓曾國于隨地的另一個重要目的,即為其護衛南方銅錫之道。
三、西周王室對曾、噩兩國的監管手段
對于如此重要且又遠離王室的南疆侯國,除了宗法、姻親聯系外,周王室主要用控制軍權和監國制度對其進行有效監管。這在金文資料中即有體現。
1.控制軍權
周王對曾、噩兩國的軍權控制同樣體現在靜方鼎、中甗等器銘中。靜方鼎記載王令靜“司才(在)曾噩師”,中甗記載中“在噩師次”,王可以直接任命靜掌管侯國軍隊,而中及其南省隊伍可以放心的“次”于噩軍大營,這反映出西周王室對于地方侯國軍隊有直接的管轄權。這種現象我們仍用《國語·魯語》“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奸慝”[44]這條史料來解釋。陳恩林先生指出:“所謂‘作師’,即組建軍隊;所謂‘帥師’,即統帥軍隊。在西周時代,這兩項權力均由周天子掌握,諸侯是無權參與的。雖然,‘元侯’尚保留著組建軍隊之權,但在行使這種權力時,必須‘承天子’,即必須接受天子的命令。天子準許諸侯國所組建軍隊的數量,各依其爵秩的高低等次而定。”[45]由此可知,曾、噩兩國雖組建了軍隊,但其軍隊的指揮權卻牢牢掌控在周天子手中。
類似的情況也見于2009年山東高青陳莊西周遺址M35出土的引簋銘文,該器銘文中提到周王不僅可以直接任命“引”管理齊國軍隊、帶隊出征,而且“引”的祖輩也一直是周王親命的齊師統帥。這與靜方鼎反映的王命靜掌管曾、噩軍隊的情況相似。李學勤先生將引簋的時代定為西周中期后段[46],綜合引簋和西周早期的靜方鼎、中甗,我們可以推斷自西周早期至中期,周王始終都掌控著地方侯國的軍事大權,正如陳恩林先生所說:“這種以天子為核心的軍事體制,勿庸置疑,是一元化的領導體制。”[47]
2.監國制度
2013年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入藏了一件噩監簋,其上銘文對于理解周王對噩國的掌控手段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該簋銘作:
噩監乍父/辛寶彝。[48]
田率先生認為其大致時代應為西周早期前段成王時期[49]。“監”字,本有“君”義,但狹義的“監”僅表監管。噩監簋銘中的“噩監”應是西周監國制度的反映。這種“某監”字樣的銘文亦見于他器,如1958年發現于江西余干黃金埠初級中學的西周早期器“應監甗”,郭沫若先生就曾經指出“應監”可能是“中央派往應國的監國者。周代有監國之制,故仲幾父簋銘文中有‘諸侯諸監’之語”[50]。后1964年山東黃縣蘆頭鎮韓欒村出土一件西周早期的“句監鼎”,1981年陜西扶風溝亦出土一件帶有“艾監”字樣的西周銅飾件。李學勤先生指出“艾監”與“應監”意義類同[51],朱鳳瀚先生也指出“句監”如“艾監”“應監”,“其身份與周初之三監同,是周王朝派到下屬侯國或其他地區代表朝廷進行監管的官吏”[52]。西周監國制度不僅反映在出土文獻中,在傳世文獻中亦多有記載。《史記·五帝本紀》就記載黃帝時期已“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53],《禮記·王制》也有“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54]。
以上材料表明監國制度在先秦,特別是西周時期較為盛行。正如前文分析,噩國為商代延續下來的姞姓大國,其實力雄厚、影響廣泛。那么周人以聯姻方式拉攏噩人的同時,于其國中設置監官是合情合理的事。只是就目前的考古發現,尚未見到有“曾監”類的銅器出土,但是根據仲幾父簋銘中“諸侯諸監”的記載,可以推測周王室在曾國很可能也設置有類似的官員。
綜上所述,我們對周初王室經營“南國”的戰略部署大致可以得到如下認識:西周早期,王室在南疆設置同姓兄弟之國和異姓舅甥之國作為其“南國”屏障,倚重侯國防衛能力的同時又嚴控其軍政大權;而以曾、噩為代表的各諸侯封國比鄰而居、互成犄角、犬牙相錯,既聯合拱衛又彼此監視,為安定淮夷、拱衛周疆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種戰略思路中,分封諸侯、以藩屏周與設置監官、“一元”軍制形成了一種交互而又統一的機制。正是這種機制的有效促發,中央王室與地方諸侯有機互動,成功實現了西周早期社會政權的穩定繁榮。
注釋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二)編號02751、02752,中華書局,2007年,第1419-1420頁。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二)編號02833、02834,中華書局,2007年,第1508-1511頁。③馬承源:《晉侯蘇編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七期,上海書畫出版社,1996年,第1-17頁。④⑤⑥[29]朱鳳瀚:《論西周時期的“南國”》,《歷史研究》2013年第4期。⑦關于西周早期曾、噩兩國地望和政治中心所在,學界論述較多,非本文討論重點,此處不再贅敘,可參見李學勤等《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墓地筆談》《文物》2011年第11期,張昌平《噩國與噩國銅器》《華夏考古》1995年第1期,張昌平《論隨州羊子山新出噩國青銅器》《文物》2011年第11期等文。⑧為避免造字,本文所引銘文中部分為破讀后用字,下同。黃鳳春、胡剛:《說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論隨州葉家山西周曾國墓地的族屬》,《江漢考古》2014年第2期。⑨⑩[11][15]李零:《文峰塔M1出土鐘銘補釋》,《江漢考古》2015年第1期。[12][34]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17、27頁。[13][16][2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466-467、1475、675頁。[14]陳偉:《曾侯□編鐘“汭土”試說》,《江漢考古》2015年第1期。[17]劉向:《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07頁。[18][53]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年,第106、6頁。[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三)編號03928、03929、03930,中華書局,2007年,第2121-2123頁。[20][27][44]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組:《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56、188、188頁。[21]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中華書局,1986年,第404頁。[22][38][39][54]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18、169、169、351頁。[24]陳鵬:《中國婚姻史稿》,中華書局,1990年,第30頁。[25]李學勤:《靜方鼎補銘》,朱鳳瀚、張榮明:《西周諸王年代研究》,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6-357頁。[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一)編號00949,中華書局,2007年,第754頁。[28][47][45]陳恩林:《試論西周軍事領導體制的一元化》,《人文雜志》1986年第2期。[30]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三聯書店,1990年,第30頁。[31][40][41]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405、64、64頁。[32][33][37]屈萬里:《曾伯漆簠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33本,臺灣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331-349頁。[35][36]孔安國傳、孔穎達正義、黃懷信整理:《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65、703頁。[42]吳其昌:《金文歷朔疏證》卷五,國立武漢大學叢書影印本,1934年,第26頁,轉引自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三十八冊,線裝書局,2005年,第127頁;劉節:《壽縣所出楚器考釋》,《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8-140頁。[4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州葉家山M28發掘報告》,《江漢考古》2013年第4期。[46]李學勤:《高青陳莊引簋及其歷史背景》,《文史哲》2011年第3期。[48][49]田率:《新見鄂監簋與西周監國制度》,《江漢考古》2015年第1期。[50]郭沫若:《釋應監甗》,《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51]李學勤:《應監甗新說》,《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1期。[52]朱鳳瀚:《中國青銅器綜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