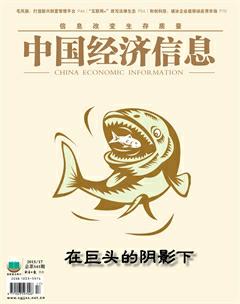許小年:需要反思凱恩斯主義
陳芬
政府的調控從根本上也難以逃脫“動物精神”的魔咒,如果調控不能最為精準,一旦出現偏差就會造成更不良的后果。
近日,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于清華科技園發表題為“凱恩斯經濟學及其批判”的演講,現場聽眾滿座,互動積極。許小年從凱恩斯主義的涵義、實質、后人對凱恩斯主義的誤解等方面進行解讀,并結合現實問題與聽眾進行了良好的互動問答。根據講座內容,本文對許小年的觀點加以整理,報道來自經濟學界的不同聲音。
許小年認為,被我們一直奉行為不二法則的凱恩斯主義,其內在邏輯實際上具有不一致性。其只求目的不問緣由的調控療法,以及盲目相信政府脫離了投資沖動的理論基礎,是凱恩斯主義的兩大缺陷。
凱恩斯主義者的誤區
在應對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時,凱恩斯認為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需求不足”,需求不足也就無法帶動生產,促進就業。許小年認為,經濟運行中并不存在人們所說的“需求不足”的問題,談論“需求不足”沒有任何意義,實際上存在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后人對凱恩斯的誤解之一是用“需求”代替了“有效需求”。而所謂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收入不足。央行印發過量的鈔票、股市發行股票,并不能產生財富,也就不能真正的帶動有效需求。在投資不足的時候,傳統的做法是刺激消費,許小年對此提出了質疑:消費是能鼓勵的么?“不是需求不足,而是口袋不足”,許小年說。
凱恩斯并未觸及經濟增長的問題,只是在力促縮小潛在GDP增長與之前的差距,但是現在的很多經濟學家卻把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當成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后人對凱恩斯的另一誤解就在于用宏觀政策來控制經濟的增長。潛在GDP與實際的GDP并不同。實際GDP的增長呈現在坐標軸上,并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條曲折的波浪線。
許小年認為,人們不問原因地在這條波浪線上“削峰填谷”,以求平穩:經濟蕭條了就“蒸桑拿”;經濟過熱了就“冷水浴”。這種“目的療法”雖能短時見效,卻忽視了對經濟波動根本原因的研究與把控。許小年認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并不可取。政府能不能消除頭疼?答案是消除不了。政府的政策在很多場合下非但沒有使經濟平穩發展,反而加大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
原因是,就算存在這么一個震蕩波,政府想把這個震蕩波的波峰削掉,想把這個波谷填平,前提是政府要對這個波有很準確的預測,能夠在正確的時點上使用正確的力度,推出正確的政策來調整,才能把它削平。如果時間、力度選擇不對,工具選擇不對,有可能放大這個波的幅度。宏觀經濟的偽科學就在于政府能不能在實踐中這么精確地,這么有預見性地操作宏觀政策,從而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否則經濟大起的背后跟著的就是大落。
宏觀經濟學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是什么?經濟周期的波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以后,我們才能看清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許小年在近日列舉美國五大湖區工業集群的例子來闡述過于奉行這種療法而帶來的弊端。美國政府在五大湖區鐵路投資高峰期間覺得經濟勢頭過熱,于是遵行凱恩斯主義對其進行了抑制,結果使得投資在下一個技術革新到來之前失去了方向。許小年還提到,中國目前產能過剩,根源也是由于太過信奉凱恩斯主義。
凱恩斯主義不僅提倡政府干預經濟,而且特別澄清政府干預是可以實現“自我支付”的,并不會造成過于負擔的財政赤字。堅信政府可以通過發債彌補部分財政赤字是凱恩斯主義一大缺陷,同時也是連凱恩斯本人都未察覺到的邏輯矛盾之處。許小年認為,這樣通過發債、擴大稅基并以此彌補赤字的做法實際上是在向后代借錢。
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除了會發生代際轉移,在倫理層面更是會涉及社會公平等命題。在這場現代與下一代的對話中,充滿著不對等性:下一代沒有聲音、沒有代表,甚至可能還沒有出生。
“動物精神”與“人類精神”
當代凱恩斯主義者沿襲了“動物精神”的傳統,指責新自由主義是上次金融風暴的始作俑者。在“動物精神”的驅使下,華爾街貪婪逐利,金融創新過度,而政府又疏于監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類精神”約束華爾街的沖動,聽任資產泡沫發展,終于釀成大禍。不僅如此,他們還宣稱,泡沫破滅之后,具有“人類精神”的美聯儲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超常規的市場干預挽狂瀾于既倒,避免了金融體系的崩潰,從而避免了大蕭條的重演。遺憾的是,事實并非如此。
許小年指出,凱恩斯經濟學的關鍵假設是“動物精神”,而由于“動物精神”無邏輯可言,幾乎無法對它進行有意義的分析,人們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這個現實,并以此為前提,探討應對之策。
眾所周知,標準的凱恩斯主義對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財政開支以彌補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減少“動物精神”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但是,許小年認為,政府調控機構的組成者、決策者也是人,而人自身就是有“動物精神”的,政府的調控從根本上也難以逃脫“動物精神”的魔咒,所以,如果調控不能最為精準,一旦出現偏差就會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所謂宏觀調控并不科學。
“浪費了一次危機”
許小年直言,“我們浪費了一次危機”。2008年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中國的經濟有個斷崖式的下跌,雖然是外部沖擊引起的,但也反映了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如果我們能利用2008年那個時機,在經濟下跌的過程中,忍受痛苦,進行結構調整,就不會有今天的困境。但是我們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于是浪費了一次衰退,浪費了一次極好的調整機會。
如果沒有當初的“4萬億”,可能沒有現在這么困難,許小年說,2009年“4萬億”執行的結果,使本來已嚴重的結構失衡更加地惡化,這表現在很多的傳統制造業部門那時產能已經過剩,產品技術落后,在市場上找不到銷路,急需更新換代。然而政府的巨量投資,又使這些落后的產能、落后的技術和產品得以茍延殘喘,甚至繼續擴張一直到今天。原來經濟中的內在的增長動力減弱了,這個時候需要增強它的體質,我們非但沒有消除導致虛弱的內部結構性弊病,反而是給它注射“強心針”,讓落后產能繼續膨脹。
最近許小年同樣提到了落后產能的問題,他說,民營鋼鐵廠很多,產能落后,現在全國鋼鐵生產能力大概在11億-12億噸,而全國的消費只有6億-7億噸,也就是說鋼鐵產能過剩30%-40%。這些過剩產能沒有消除之前,鋼價不會反彈,各家都在產能的壓力下,低價在市場上銷售鋼鐵。低價銷售的結果是誰都沒有利潤,一些鋼鐵公司是靠著政府的救濟在活著,其實早就應該倒掉了。它們不倒,那些效益高的鋼鐵公司也沒有辦法正常經營,因為價格被壓的太低了。鋼鐵行業是傳統制造業的一個代表,我們用新的產能泡沫去掩蓋舊的產能泡沫,結果致使泡沫越來越大。
許小年說,經濟形勢不好反而能夠倒逼改革,希望大家更多關注微觀層面上政策的變化、監管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市場機會。最近政府也出臺了一些較好的改革政策。
“我喜歡熊市,不喜歡牛市,為什么?因為在牛市中,資產的價格都被高估,只有在熊市中,資產的公允價值才能夠在市場上出現,就像巴菲特喜歡熊市一樣。所以不要害怕經濟的下行和經濟的調整,在調整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的商業機會。”許小年在近期如此表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