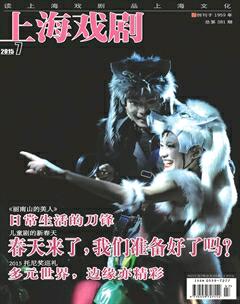“戲劇與文學關系的反思”學術研討
楊揚:戲劇跟文學是一種比較強勢的關系,這兩年,話劇對于小說的改編是從未有過的密切,但主要體現在量的跟進上,比較受關注的小說幾乎在舞臺都有呈現。但是對于選擇什么作品來進行改編,現在好像不大看得出話劇自己的自主性特征,創作主體意識弱化,這與以往強調經典性是有差距的,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消費文化中的一個頑疾。
郜元寶:戲劇與文學的關系,既可以是對經典的追求,也可以是一種對抗的關系,這就需要戲劇家跟文學展開競爭。如果能達到這一境界,那就是在一個很廣闊的文學性空間進行創作,戲劇的空間就更大了。文學存在于文本中,但本身是一個活的結構,是需要被召喚出來,如果沒有召喚,它永遠是一個死的文章,這需要戲劇家要有充分的戲劇與文學準備。
趙耀民:我們本身就是搞文學,只不過寫的是劇本不是小說。劇作是一度創作,但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一度創作成為依附了,而且也不叫做創作,就是策劃、制作過程,只起一個文本的作用,也許從工業化產業化生產流程來說是科學的,但是編劇作為創作個體,肯定受到擠壓甚至最后可能消失。
熊源偉:現在確實有一些偏執于“工作坊”即興創作模式的人提出:“當代戲劇超越了文學,成為視聽/時空/觀演合一的劇場藝術”,這種論調直接威脅到戲劇的文學性,但這只是一個自以為是、似是而非的命題。我們承認,當下的戲劇藝術由Drama發展到Theater,但這只是戲劇創作完成方式的側重點不同,“劇場藝術”與戲劇的文學性不是二元對立的矛盾體,優秀的戲劇作品,都不會排斥文學性,或者說,都應該具備文學性。
話劇《死神與少女》
@郭晨子:編劇的技巧和深度使《死神與少女》榮獲了殊榮,使觀眾和劇中人一起經歷了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靈絕境。當薩拉·凱恩、馬丁·麥克多納等人的劇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英國為評論者稱為“直面戲劇”,智利劇作家阿·多爾夫曼的《死神與少女》似也在“直面”,而“直面”,本不就是戲劇的品質之一嗎?
兒童劇《牧神午后》
@張敞:我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合家歡的兒童劇,結果我從頭到尾飽含著熱淚看完。這是生命的締造和毀滅,這是上帝、人類、自然的哀歌。純凈的愛開始,卻以殘酷的破壞結尾。人性和天地的不可捉摸,喜怒無定,讓我沉浮哀慟。
話劇《黑鳥》
@安倪化為雨滴彩虹:激情與墮落、愛情與虐待,少女對愛情的幻想與期待,終究敵不過丑惡變態的人性,女主悲催的命運!一份痛苦難忘的愛,在那天以后“你把我扔在愛里”,一層層脫去偽裝,露出真實丑陋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