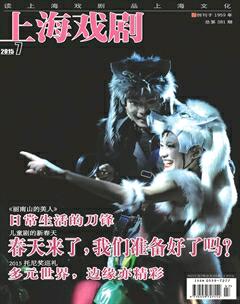你的“升級”我真的不懂
冷自如
借著上海越劇院院慶六十年的東風,上海大劇院與上越強勢推出“殿堂版”《紅樓夢》。尤為值得一提的是,“殿堂版”不僅將從2016年開始定期于農歷春節在上海大劇院駐場演出,中生代藝術家演出的“名家版”更是今后“獨家供應”殿堂版,不再在其他劇院演出。
暫且不論這是否是一場藝術盛宴,不如先說它是一次營銷事件。眾所周知,上海越劇院最有影響力的“紅樓團”正是以經典版《紅樓夢》這部作品命名的,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說它是紅樓團甚至上海越劇院的品牌形象也不為過。也因此,“殿堂版”的高調亮相、長期駐場、以及名家版的“獨家供應”意義深遠,可視為上海越劇院對《紅樓夢》的品牌升級。
“經典”、“名家”、“大制作”無疑是其升級品牌的主打要素。一方面,通過“那一年,我看過的《紅樓夢》”展覽征集活動與后續的“海上紅樓花”主題展,借勢“經典版”積累的口碑效應與品牌影響,成功為“殿堂版”加冕上“中國戲曲頂尖代表作”的光環,不知不覺間讓老觀眾把幾十年來對“經典版”的深厚感情與“舞臺綜合藝術集大成之作”的聯想原封不動地轉移到“殿堂版”上面去。另一方面,各類宣傳報道又開啟了“暌違16年”、“數遍了指頭把佳期待”等話題熱點,不僅鏈接上曾經的奇跡見證者對于“中生代名家的共同記憶”,更是喚起了未能躬逢其盛者對于以“因華麗宏大、制作精良的服裝舞美、云集多個流派名家的演員陣容等特色冠絕一時”的大劇院版神話的強烈憧憬。
只是,這一場“大制作”、“名家版”的“經典劇目”真的等同于更好的制作、更好的表演、更好的藝術么?還是只是營銷上的“瞞天過海,暗度陳倉”呢?
這次的演出和1999年大劇院版《紅樓夢》一樣,以“元妃省親”開篇,以“太虛幻境”結尾,刪掉“黛玉進府”、“識金鎖”全場,對其他多個場次也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壓縮,同時犧牲了周寶奎的“可憐你年幼失親娘”、金采風的“昨日樓頭喜鵲噪”、徐天紅的“自古道世事洞明皆學問”,尤其是王文娟的“繞綠堤,拂柳絲,穿過花徑”等經典唱段,取而代之的是“我愛那瀟湘館中千竿竹,與我一樣瘦伶仃”、“你住瀟湘館,優雅又清靜,我住怡紅院,兩處靠的近,常來常往共談心, 你我兩個靠得近”……精致的唱腔被拋棄,優美的唱詞被世俗化,敘事流暢遭到破壞,情感打動人心的力量被嚴重削弱。試問,這樣的“紅樓夢”還能與“經典版”等而視之為“戲曲藝術的頂尖代表”嗎?這樣的改編難道又是“大制作”必須的嗎?
在劇情與唱腔作出巨大犧牲后,斥資數百萬的“大制作”僅僅被等同于更大的布景,更多的龍套,而不是更精良的制作與更適合戲劇表演的舞臺空間無疑是令人遺憾的。“游園”里粗壯的亭柱遮住了演員的臉孔,“葬花”里繽紛的花雨淹沒了黛玉的表演,“金玉良緣”里偏居一隅的雄偉婚床使得新人的耳鬢廝磨都成了隔空喊話……這樣為排場而排場,喧賓奪主的“大制作”真的能等同于更好的制作嗎?
而“名家”們狀態的整體滑坡亦未能成就“更好的表演”。臺步隨意、身段潦草、氣息不足、念白慌亂,破音、跑調比比皆是,更遑論人物。更大的舞臺,更大的調度,又對名家們的體力造成極大挑戰,也使得整臺演出的效果更打折扣。
如果說經典版以其精美的唱詞,精妙的表演,精致的唱腔,精良的服裝布景,使人切實體會到一個一流院團在編劇、演員、舞美等各方面的頂尖藝術實力,那么“殿堂版”所著力打造的華麗、宏大、人海的品牌聯想,最多讓我們感知到的也僅是制作這場演出的經濟力量而已。
建院六十年后,上海越劇院在傳承與創新、藝術與市場上必然是要有的新的方向,但我以為,從經典版到殿堂版,《紅樓夢》的品牌內涵已悄然轉換,從并列“越劇四大經典之一”到與《甄嬛》花開并蒂,折射出的是彷徨與迷失。
作為“中國越劇的搖籃”,上海越劇院的核心資產正是宗師一輩積累下來的大量經久不衰的經典劇目,它是包括了劇本、音樂、服裝、舞美、唱腔、身段、表導演在內的“活的數據庫”。上海越劇院得天獨厚之處正是藝術上的原汁原味,師承上的直系嫡傳。不同于“浙百”的時尚與創新,不同于“紹百”的文武并重,我認為上海越劇院的風格與定位在于“古典”——這是任何其他院團都不具備的競爭優勢。
“古典”首先意味著它是越劇的正統與典范。當代越劇的基本特征都由宗師一輩奠定,包括以導演為中心的排練制度、以尺調與弦下腔為主的基本曲調、公認的十三種流派唱腔、昆劇與話劇結合的表演手段、來源于古裝仕女圖的造型、虛實結合的舞美等。其中屬上越者何止半數?徐進、吳琛、顧振遐、蘇石風、劉如曾等都是編劇、導演、表演、音樂、舞美等各領域開疆拓土之士,而表演上更在公認的十三位流派宗師中占據九席。不僅越劇的民間老戲,如《梁山伯與祝英臺》、《碧玉簪》、《九斤姑娘》都以上海越劇院修改、打磨后的版本定為范本流傳于世,其第一代“夢之隊”所創造的大量新編經典劇目如《紅樓夢》、《西廂記》等更是在任何方面都具有教科書般的價值與意義,成為后世難以超越的經典之作。可是,雖然自稱是“活的數據庫”,但真正活態的劇目還剩多少呢?縱然是“復排”,也要“重修”,當“升級”、“駐場”、“名家獨家供應”已經危害到鎮團劇目的傳承之時,不能不格外加以警惕。我們都知道,戲曲是角兒的藝術,而戲曲人才的培養最重要的是劇目的學習與累積,可想而知,當經典劇目逐漸失傳或者變質之后,越劇的未來將走向何方?
其次,以《紅樓夢》、《西廂記》為代表的上海越劇院所創造的第一代經典劇目等充分展現了中國古典文學藝術之美。與源自民間故事、充滿鄉土氣息的越劇老戲不同,上個世紀上海越劇院的新編劇目或改編自中國古典文學,或出自著名文人之手,諸如黛玉焚稿時所唱“我一生,與詩書作了閨中伴,與筆墨結成骨肉情”,再如《西廂記》結尾鶯鶯目送張生遠去,紅娘問“小姐,他往哪里去了”,鶯鶯答“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里”——無不充滿著濃郁的詩意,蘊藉的意境。它擴充了越劇的題材,更提升了劇種的文化品格。在舞美與服裝設計方面,當年的上海越劇院也奠定與發揚了優美抒情的風格。比如源自古代仕女畫的典雅婉約的造型,比如融入古典藝術如山水畫、工筆畫、園林建筑、皮影剪紙等的舞美設計。再加上宗師們內求體驗,外法昆劇的表演程式,才使得越劇長于刻畫具有書卷氣的翩翩公子與知書達理的古典佳人,能其他劇種之不能。而“殿堂版”一味追求場面上奢華與闊氣,不僅與和諧統一、婉約雅致的古典美學背道而馳,而不惜犧牲劇目文學與藝術的品格。怎不讓人扼腕嘆息。
我相信院團并非不明白自身的優勢與特色,但他們擔憂的是“古典”越劇已經過時過氣,不符合現代審美等等,說到底是對觀眾的盲目揣測與迎合。然而試問,“殿堂版”《紅樓夢》的火爆有多少來源于戲本身的品質?如果大劇院的平臺與強勢營銷都可以將“殿堂版”打造成神話,為什么我們有了更好的渠道與運作,卻不用以宣傳與推廣真正的藝術經典呢?又有什么理由認為在同樣的條件下,原有的經典版《紅樓夢》不能吸引更多的觀眾、不能做到更好?
以這樣的“殿堂版”來說“留住老觀眾,吸引新觀眾”、展示院團“傳統根基與創新能力”恐怕事與愿違。走了六十年,是時候停下來想一想,藝術/經典與財力/排場,對老觀眾來說,“上海越劇院”、《紅樓夢》的品牌意味著什么?院團又希望它們對于新的觀眾來說,意味著什么?立足古典特色與競爭優勢,珍惜“規范正統”的品牌形象,傳遞“藝術經典”的品牌價值。前一陣方亞芬、吳鳳花版“敬禮大師、修舊如舊”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叫好又叫座是不是說明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