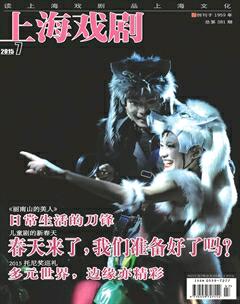一幅活態(tài)昆曲史
蔡正仁
當(dāng)我翻看這本《昆曲摭憶》的時(shí)候,即有一種先睹為快的愉悅, 30位與上海昆曲密不可分、休戚相關(guān)的昆曲人頓時(shí)躍然紙上。一人一文,有長有短,30篇文章就像30出折子戲,連綴起來就是連臺(tái)本戲。不管是寫人說戲,敘事記史還是談藝論技,角度多樣、文筆清新,它們所講述的內(nèi)容構(gòu)成了當(dāng)代上海昆曲的立體呈現(xiàn),是一幅活態(tài)的昆曲演出史、教育史和發(fā)展史圖錄。
1953年冬,華東戲曲研究院昆曲演員訓(xùn)練班開始招生。1954年3月1日,60名(男34,女26)學(xué)制為8年的第一屆昆曲演員訓(xùn)練班的學(xué)員(即“昆大班”)正式走進(jìn)校園學(xué)習(xí)昆曲。1955年,華東戲曲研究院易名為上海市戲曲學(xué)校。1959年又招收了71名第二屆昆曲演員訓(xùn)練班學(xué)員(即“昆小班”或“昆二班”),其間還陸續(xù)招收了與之配套的音樂、舞美、武功師資班等。這些學(xué)員畢業(yè)后成為上海昆曲界的活躍分子,或在演出第一線,或在教學(xué)第一線,無論是在臺(tái)上臺(tái)下還是臺(tái)前幕后,可以說,他們與昆劇的命運(yùn)緊密相連。他們把青春與熱情獻(xiàn)給了昆曲,他們嘔心瀝血、傾盡畢生之力將昆曲的藝術(shù)魅力傳播到全國甚至世界,為昆曲在當(dāng)下的繁榮作出了自己的貢獻(xiàn)。他們的藝術(shù)實(shí)踐實(shí)乃當(dāng)代昆劇無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
1959年“昆小班”進(jìn)校后,“昆大班”還沒畢業(yè),“昆大班”和“昆小班”還在一起學(xué)習(xí)。有趣的是,1961年“昆大班”的同學(xué)畢業(yè)后,有一部分人留在學(xué)校做了傳字輩老師們的助教,所以他們和“昆小班”的同學(xué)成了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很特別。
據(jù)我所知,錦華小友2004年到上海戲劇學(xué)院讀書不久,就癡迷上昆曲,成了一名“昆曲義工”,義務(wù)宣傳昆曲。她為《魂?duì)坷デ迨辍贰ⅰ稛o悔追夢》等與上昆有關(guān)書籍的出版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對(duì)我們上昆、昆曲在上海的發(fā)展,乃至整個(gè)昆曲發(fā)展史都比較了解。博士研究生畢業(yè)以后,她又到了上昆工作,把她的專業(yè)學(xué)習(xí)和興趣愛好結(jié)合起來,更加如魚得水。這些年,她在專業(yè)上肯鉆苦學(xué),無論是理論學(xué)習(xí)還是工作實(shí)踐,進(jìn)步很大。值得欣慰的是,她有一種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虛夸、不浮華、謙虛低調(diào)、實(shí)事求是,甚至?xí)榱艘痪涑弧⒁痪淠畎椎挠蓙矸磸?fù)求證。她也樂于把自己融入到上昆這個(gè)大家庭中,我們都很喜歡她。
這本書里所采訪的30位昆曲人,只是眾多昆曲從業(yè)者中的一小部分,屬于冰山一角。我希望錦華小友能克服各種困難,繼續(xù)把老藝術(shù)家口述實(shí)錄的工作做下去,這是一項(xiàng)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常說“紅花也要綠葉配”,紅花鮮艷綠葉多,正是由于綠葉的襯托紅花才分外突出,如果沒有綠葉,紅花也會(huì)黯然失色,紅花與綠葉并不對(duì)立,而是一種相輔相成、相依相傍的關(guān)系。昆劇是一門綜合藝術(shù),除了臺(tái)上光鮮地站在舞臺(tái)中間的演員外,也有很多一串跟頭翻過來,可能觀眾還沒看清他們的臉就又跑下臺(tái)的龍?zhí)祝斜姸嗟哪缓蠊ぷ魅藛T包括主創(chuàng)、舞美、樂隊(duì)、行政人員、后勤服務(wù)人員等等,還有很多昆曲普及推廣人員。主演和他們之間就像“紅花”與“綠葉”的關(guān)系。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這些“龍?zhí)住被蛘哒f是“綠葉”的數(shù)量遠(yuǎn)遠(yuǎn)占優(yōu),把他們的故事呈現(xiàn)出來,讓更多讀者了解他們平凡卻又不平凡的歷史,也是一種尊重。
我還想說,因?yàn)槟撤N機(jī)緣,我們的一生和昆劇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是一種緣分,亦是前世修來的福氣。雖然我們?yōu)槔デ瞰I(xiàn)了一生,但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人生卻因?yàn)槔デ兊酶恿钊瞬毮浚屿n麗,更加絢爛。我們應(yīng)該感謝昆曲,我們也應(yīng)該恪盡昆劇人的職責(zé), 守護(hù)好這份老祖宗傳下來的家當(dāng)!
目下,這些以“昆大班”“昆二班”為主體的昆劇人大部分已經(jīng)退出或者淡出舞臺(tái),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偶爾也會(huì)參與一些示范性的演出活動(dòng)。據(jù)我所知,這批人中的很大一部分還在教學(xué)第一線忙碌著,培養(yǎng)著下一代。歲月不饒人,當(dāng)年“昆大班”的同學(xué)都已七十出頭,“昆二班”的同學(xué)也已是“奔七”的人了。回顧我們的藝術(shù)人生、發(fā)明創(chuàng)造,或是總結(jié)我們曾經(jīng)創(chuàng)作演繹的舞臺(tái)形象,或是我們的教學(xué)經(jīng)驗(yàn),哪怕是一些失敗的教訓(xùn),對(duì)于我們的晚輩后學(xué)來說,既是一份藝術(shù)品格的傳承,也是一份專業(yè)藝術(shù)的傳承,更是一份精神財(cái)富的傳承。為他們照亮今后的藝術(shù)人生之路,這也是我們這群老頭老太義不容辭的責(zé)任。
我深切地期待能涌現(xiàn)出更多熱愛昆曲的仁人志士,支持昆曲,呵護(hù)昆曲。昆曲不僅是屬于我們的,更是屬于你們的,是屬于我們大家的!
(本文為《昆曲摭憶》一書序言,標(biāo)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