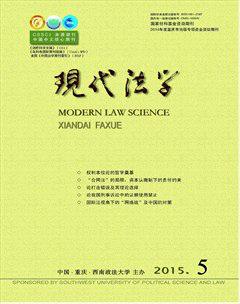雜家尸佼與戰國法思想研究
摘要:戰國中期的尸佼以“去私”為核心理念,循政治實用原則,折衷各家,“取合諸侯”而開創雜家學派。尸佼之學,提挈道家天地道論以立綱維,歸旨于“事少功多”的理想治世;兼采儒、墨道德仁義之說,致力于道德倫理與功利效益的取舍整合;匯合名、法名實之論,呈現出治人層面之“用賢”與治法層面之“案法”的統合性闡釋。尸佼之實用觀念與折衷主義,乃商鞅變法前后各家學說沿道法轉關、儒法融合的思想史譜系演變之先聲,其治道法術合攏之旨趣,堪稱先秦諸子思想融匯之范本,亦為漢代百家話語歸一之先兆。
關鍵詞:尸佼;雜家;商鞅;去私;道;仁義;正名
中圖分類號:DF092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5.02
尸佼(約前390-330年),國籍不詳。 尸佼生卒年錢穆有所考證。尸佼國籍爭議頗多,《史記》記載為楚國人,劉向《別錄》認為是晉人,《漢書·藝文志》認為是魯國人,錢穆則推測尸佼是魏國人。(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16,695.)關于《尸子》,秦漢之際“世多有其書”,《漢書·藝文志》雜家類著錄為二十卷,據《隋書·經籍志》,魏晉時己非全本。清人汪繼培《尸子》輯本,綜合古人各輯本之優長,詳細注明佚文之出處,今人研究多本之。 文獻學研究認為《尸子》汪輯本最優。(參見:王彥霞.《尸子》汪輯本初探[J].圖書館雜志,2005(1).)
《后漢書》、《宋史》將尸佼歸入儒家 在《后漢書·宦者列傳》中,李賢注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宋史·藝文志》子部儒家類:《尸子》一卷。,但劉向言尸子“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雖非確當之論,亦可見其疏隔于儒門道統。按說尸佼與商鞅謀劃計事,立法理民,似可并歸法家行列。不過,史書大多收錄《尸子》于子部雜家類,如《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等。近人金德建曾將尸佼譽為“雜家”創始人,曰:“尸佼年代較早,開創雜家學派。《廣澤篇》的說明宗旨,樹義如此明確;足為后來的雜家視為準則。”金德建還論證尸佼學說與《荀子·解蔽》、《呂氏春秋·不二》的共通性,以強化尸佼為雜家宗師之觀點。(參見:金德建.先秦諸子雜考[M].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164.)蓋為確論。
先秦雜家法思想的研究歷來不足,武樹臣先生的研究有開山之功,惜乎內容只及《呂覽》。 武樹臣的《中國法律思想史》撰專“雜家(呂)的法律思想”。(參見:武樹臣.中國法律思想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3.)觀《尸子》之殘篇,固難媲美《呂覽》,但時代較早,成于一人,更可顯現早在戰國中期即有一種融合會通諸子學說的理論嘗試。或因循古書辨偽之風氣,或囿于儒法冰炭不容之成見,或罔于尸佼國籍界說之紛亂,或畏于其學之雜錯漫羨,曾有論者推斷《尸子》為偽書,或認為存在兩位“尸子”。 “古史辨派”多以尸子為《偽書》,徐文武則認為存在兩位“尸子”。(參見:張西堂.《尸子》考證[G]//羅根澤.古史辨(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646-653;孫次舟.論尸子的真偽[G]//羅根澤.古史辨(第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01-104;徐文武.《尸子》辨[J].孔子研究,2005(4).)其實,尸佼學派屬性之聚訟,抑或《尸子》真偽的爭辯,反而映襯出尸佼學說之博通。閱者的姿態左右了對其學說的釋讀,“儒家看到的是仁義,道家看到的是道德,法家看到的是法術。”[1]
尸佼以為,儒、道、名、墨各創學說,為鴟張門戶而交相攻訐,皆“弇于私”。有見其時出奴入主之風氣,尸佼主張“去私”,摒棄一端之見,歸于“一實”。故而,其學大有沖決學派藩籬,總攝各家大旨之氣象,既吸納各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又不拘囿于一家一子之學術立場。由此,發軔于商鞅變法前后的雜學,在先秦思想領域嶄露頭角,昭示著諸子之學朝向道法轉關、儒法融合之趨勢。核心理念之包容,學說范疇之圓實,知識方法之融通,治術手段之兼及,此四端蓋為雜家學說之特征,亦可為今人詮釋之框架,析論如下。
現代法學馬騰:雜家尸佼與戰國法思想研究一、去私:《尸子》的核心理念《尸子·廣澤》云: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故智載于私則所知少,載于公則所知多矣。……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后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于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
在該篇中,尸佼集中闡明雜學宗旨,宣揚“去私”理念。所謂“去私”,既是一個道德論說、是非判斷的客觀性基礎,消除成見、綜合學說的共通前提,也意在實質性地從“公私之辯”的角度凝合儒、道、墨之核心精神。
一方面,尸佼“去私”的第一要義在于對智識障礙與認識前見的審視。當代正義論大師羅爾斯提出“無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的理論模型,精妙地構設一個人們在“原始平等地位”前提下訂立“社會契約”的程序,經由對正義觀之前見的深刻反思,啟示人們沖決現實拘囿之思維定勢。(參見: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9-10.)中國先哲確已有見于自身情境與個人私欲對正義標準的扭曲與消解。尸佼譬喻道:“夫私心,井中也;公心,丘上也。”私心拘囿了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視閾,公心則鋪設起人們認知事物的最優平臺。因此,“無私,百智之宗也。”(《尸子·治天下》)廣博智識的獲致與高尚道德的體悟,都根植于去個體化,超越自我前見的平恕之心。表達任何訴求、辨明一切是非,都必須以公心為支撐才能做出客觀公正的判斷,“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后可知也”。進而,“去私”的理念,清晰表達了將林立的學術派別與“相非”的學術觀點加以提煉統合的抱負。尸佼舉例闡釋了語義表述的多樣化與概念實質內涵的相通性,同理,“若使兼、公、虛、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充類至盡,儒、道、名、墨各家的某些主張,乃至根本精神名異實同,均可在道的統攝下獲得統一。 道論與雜家姿態關聯密切。(參見:郭齊勇.《尸子·廣澤》、《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與《呂氏春秋·不二》中的真理史觀之異同[J].中國文化復興月刊,1990(12).)endprint
另一方面,與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一樣,“去私”警惕一種因私而致使正義法則支離破碎的傾向,竭力倡導以天下公利為本。孔子言“仁”,墨子貴“兼”,尸佼則認為“去私”這一語詞更能直截明了表達同一義涵。“去私”蘊涵著人性論點:“私”雖為人之本性,但人皆應努力培養“公心”。雜家去私之精神,使得尸佼拒斥楊朱式的絕對個人主義,更偏向于墨翟式“無我”的集體主義。 當然,尸佼也是在承認“私”的前提下言“去私”,畢竟“公”與“私”是相對存在的,絕對的“去私”是不可能的。(參見:徐文武.《尸子》的社會政治思想及其學派屬性[J].長江大學學報,2007(10):22.)
尸子既沿襲道家“天道無親”的思想,又吸納墨家“天志兼愛”一義,故曰“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從推天地以明人事,推己而及人的原理出發,自然得出人君“去私”之結論。尸佼亦祖述圣王,認為“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不私其親而私萬國”,都是以“大私”為“無私”的典范。《尸子·綽子》說:“圣人于大私之中也為無私”,“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無不滲透著道家“辯證趨反”思維之妙用。所謂“大私”,是“私萬方”、“私萬國”,將所私之畛域擴充到天下萬國,以天下為“私”,亦返為“公”也,故“大私”即“公”。于是,這種邏輯自然演繹出天子之“私利”即天下之“公利”的結論。這又隱約可見儒者進諫君王的情境,天子欲維護自己的“私利”,必以實現天下之“公利”為路徑。有感于私見私利對公共生活的妨礙,尸佼以現實主義的眼光關注社會政治中的公私問題,實為對“家天下”之國家秩序與政治形態的寫照與詮釋,亦為君王制樹立一個崇高的政治原則。概言之,尸佼的“去私”論,是彰明一種矯正偏見、倡導包容的學說姿態與倫理情懷,凝合儒、墨諸家之核心精神,并以辯證思維檢視歷史與現實的公與私的矛盾統一。“去私”論雖有消磨儒、墨諸學精神差異之嫌,但在當時不失為對國家社會與個體生活之間關系的深刻洞見,也構成其“制分正名”之法制言說的倫理基礎。
二、道·仁·義:《尸子》的基本范疇近人張琦翔曰:“雜家者,雜取眾說而能自立宗旨,雜而能成家也,此所謂雜即調和意義。調和并非湊合,亦非混合中和,兼揉眾長,舍去其短,免去矛盾,融合為一,此之謂調和,雜家之意以大矣。”[2]《尸子》融會貫通諸家學說之抱負,自當訴諸一個綱舉目張的統合架構,為百家學說的融通提煉出理論基點。尸佼建構了天地、四時、德性與政治合一的宏大框架,將天道、治道、人道聯系起來編織其思想體系的大網,“是先秦雜家在內容與形式上構筑大體系的最早嘗試。”[3]
(一)“天地之道”:“事少功立”的治世境界
與道家如出一轍,尸佼闡發了“道生萬物”的創生論,描述了“天地之道”對萬物的玄妙支配,詮釋了“道法自然”與“天道無私”的自然平等觀念。而且,尸佼也推崇道家“無為之治”,憧憬“事少功多”之治世境界。尸佼本“從道必吉”(《尸子·佚文》)之見,以無事為宗旨,奉行不爭原則,不以強行力爭天下,拒斥陰謀智巧權術,均不失為對道家道論的繼承。茲列下表對照《老子》與《尸子》中的道論言說:《尸子》與《老子》道論對觀表《老子》《尸子》創生論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天地生萬物。(《尸子·分》)實存論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老子》第十四章)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尸子·貴言》)無私論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第五章)天無私于物,地無私于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尸子·治天下》)無事論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老子》第三十七章)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尸子·分》)反智論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偽棄詐,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老子》第十九章)執一之道,去智與巧。(《尸子·分》)柔道論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第八章)水有四德……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尸子存疑》)在《老子》中,存在著“道-德”的脈絡或從天道到人道的思維,經由“德”的外化作用,形而上的“道”本體便落實為具體而普遍的社會規則。 陳鼓應釋曰:“落向經驗界的‘道,就是‘德。”(參見:陳鼓應.老子今譯今注[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4.)尸佼云:“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遍,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尸子·勸學》)在“勸學”以進于“德義”的倡言中,尸佼賦予了“德義”如同天地之道的本體論色彩與普遍性特征。于是,在天地之道落于人間之德的映射軌跡中,尸佼沿用了道家“道-德”的脈絡,同時也在天地之道的本體論框架注入儒家的重要德目與實質精神。 另外,《尸子》一書也糅合了陰陽、四時學說。見《尸子·君治》、《尸子·仁意》、《尸子·佚文》。
《尸子·處道》云:“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德、義、禮之訓詁,均不離“天地”二字,尸佼旨在構建一個綜合性詮釋:“德”即是“得”,是天道在人間的折射,是自然之“道”的社會鏡像,故曰“天地萬物得也”;“義”釋為“宜”,同《禮記》之說,實為將“義”詮釋為中庸適度性;“禮”稱為“體”,闡明了“禮”作為規則整體的形式化義涵。三者之間,義(宜)是德的精神內容,禮是德的體系框架,三者涵義的整合便進于尸佼所謂“大仁”。從《尸子》對道論的沿襲,確可窺見“在道家強大形上系絡的統攝之下,戰國中晚期的思想特色已然有了一個共識——朝向統治術的整合。”[4]而在這一整合中,尸佼雖借用道家“無為”的話語,但只保留其博大精深的天道本體論,在“治道”層面更多注入的是儒家之“仁德”、墨家之“義利”。呂思勉說:“雜家兼容而并苞之。可謂能攬治法之全。所以異于道家者,驅策眾家,亦自成為一種學術,道家專明此義,雜家則合眾說以為說耳……后世所謂學者之先驅也。”(參見: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5:158.)胡適說:“雜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雜家的新名。漢以前的道家可叫做雜家,秦以后的雜家應叫做道家。”(參見: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C]//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294.)由此看來,“攬治法之全”的《尸子》,縱跨形上道家與儒、道、法統治術之間,一方面,將道家“道生萬物”、“執一”的“道—德”形式架構,接續上儒家內圣之仁德與外王之德治的實質內容,以及墨家“兼愛交利”的功用觀點與經驗主義;另一方面,尸佼的名論凸現了道、儒、法之間的理論接榫,以道家“事少功多”為意旨,綜合各種“法”思想,制分且正名,因智而因賢,案法并賞刑,皆在通向“無事”之政治理想的路徑中獲致其存在價值與現實意義。雜家的集大成著作《呂氏春秋》思想體系之特點,如高誘所說“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尸子》相類。(參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M].北京:中華書局,2009:3.)endprint
(二)“四儀之德”:儒家“正己治人”的德治理路
尸佼認為,不只萬物為天地所化生,倫理道德也是天地之道的人間投射,進而嘗試將儒道之義理融于“道-德”系絡中。尸佼言“事少功多”,雖有不恃強力、不行間諜等觀點,但仍與道家無為之真貌大殊。在德治的范疇中,尸佼轉向了儒家的修齊治平,即從圣王自我修德到天下大治的德治理路。《尸子·神明》云:
圣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圣人之身小,其所燭遠,圣人正己而四方治矣。上綱茍直,百目皆開。德行茍直,群物皆正。政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
考察《尸子》可以發現,彰顯于前儒家時代,光大于孔孟學說的傳統德目,亦在尸佼之學中層見疊出。陳來的研究揭橥前諸子時代“德行”觀念與話語的意義。(參見:陳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上海:三聯書店,2009:311-368.)《尸子·君治》言“仁則人親之,義者人尊之”,將仁義奉為君王安身立命、安邦定國的重要原則。《尸子·四儀》曰:“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四儀”之“仁”、“義”、“忠”、“信”無非儒家最基本的道德范疇,尤其《恕》篇推崇“仁恕”,重視內心修養,均符合儒家之精神。此外,《尸子·佚文》引孔子“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之語,流露出對儒家“法先王”,重詩書的尊重傳統姿態的認同。尸佼還講“守道固窮,則輕王公”,亦不失保有子思恪守道義、傲視權貴的儒者風骨。
既深通儒學精義,諳曉儒家后學,尸佼自然對儒家君民關系論亦推崇備至。他闡明“夫知眾類,知我則知人矣”的道理(《尸子·佚文》),著實體現了無異于孔孟推己及人之仁學、仁政思路。而且,《尸子》熟諳儒家式的貴民修辭,如《尸子·處道》引孔子言:“君者盂也,民者水也。孟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尸子·君治》援引子夏將君民關系比作魚水關系的言說,《尸子·佚文》將民眾看作天子、諸侯興衰滅亡的根本所在。也須承認,尸佼亦流露出將民眾視為客體、工具的傾向,竟謂“民者,譬之馬也”。(《尸子·佚文》)這已顯露出富國強兵變法中驅策民眾的功利色彩。故論者指出,尸佼學于儒家,《尸子》是“子思子之學傳入秦晉的重要線索”、“儒學通向法家的棧橋”。(參見:魏啟鵬.子思之學[G]//武漢大學中國文化研究院.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636-641.)
在諸德目之中,尸佼意識到“義”的多向度特征可以統合諸德。他用一番形象比喻加以闡明:“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佚文中還堅持富、貴、生皆不能易“義”,堪稱儒家式舍生取義的崇高命題。可見,尸佼的“義”論,仍保有思孟學派的心性學色彩,強調個人的道德之自律與內省[5]。
《尸子·貴言》曰:
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則行,禁焉則止。……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
尸佼認識到“一天下”之關鍵在于令行禁止的法令實效性。然在對社會秩序的審思中,尸佼將“令行禁止”的法律理想治理模式內轉到個人內心層面,經由個體自身對“義”的認識與反躬自省,方能獲致一種真正的法令實效,最終是為了闡明“心者,身之君也”的結論。所以,在尸佼的法思想中滲透著儒家式的“德治-人治”思路,也與墨家所言“義者,正 《天志上》篇作“政”。孫詒讓案:“意林引下篇‘正皆作‘政,二字互通。‘義者,正也,言義者所以正治人也。”(參見:孫詒讓.墨子間詁[M].北京:中華書局,2001:193.)也”(《墨子·天志下》)相類。
(三)“義必利”:墨家“兼愛交利”的實用觀念
誠然,尸佼言不離圣王、仁義,卻掩蓋不住學說的實用特征與功利色彩,反映了戰國初期政治道德論的顯著發展。尸佼的“義”,雖在“心者,身之君也”的映照下呈現出“內圣”的心性學取向,但也在“治己則人治”的合釋中具有“外王”的政治化向度。 尸佼之“義”具有歸宿實利的傾向,往往能融入到實踐活動中,外化為社會準則,凸顯出社會效應。(參見:朱海雷.尸子及其雜家思想[G]//汪繼培輯,朱海雷撰.尸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其實,《尸子》中的德性言說,已更多顯現出群體秩序的面向。所謂“人待義而后成”,凸顯的是人的社會性而非自然性,“義”透露出群體性意味,獲得豐足的秩序性義涵。在外轉為社會實踐,歸宿于社會效應的言說中,這一道德尺度又經由個體的自省,參驗于主體間而凝合成共識的通用準則,并構筑法律秩序的倫理基石。《尸子·恕》云:“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事中義”為“法”,意即“義”在實踐運用中發揮其社會效應,外化為法律規范。逆言之,能夠稱其為“法”的,必須中“義”,這就為“法”的檢驗樹立了一個道德尺度。“事中義”的思路,也就與墨家的“法儀”之說異曲同工。
更重要的是,尸子的道德論,尤其是“義”論,與“利”已不再呈現為緊張對立的關系;相反,尸佼以“義”為核心的“德”染上了濃重的功利色彩,故云“兼愛百姓,務利天下”,且拾墨翟之說以節葬、非樂為中“義”之道。(《尸子·佚文》)有論者指出:“在道德與利益的關系上,(雜家)既堅持以義為最高準則,又能注重現實,以利為歸宿。”[6]《墨子》有《貴義》篇申“萬事莫貴于義”之旨,而《經上》又曰:“義者,利也。”商君亦言:“吾所謂利者,義之本也。”(《商君書·開塞》)同樣,《尸子·發蒙》云:“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義”的道德準則與其實際效果常合而言之,“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分天下以生為神”。(《尸子·貴言》)其實,不管是商鞅的“利者義之本”,還是尸佼的“愛民且利之”,無不表明以利釋義的思路,無不閃現墨家“兼愛交利”之精義。故有論者認為,“尸子把墨子的兼愛塞進孔子‘仁的概念中了。”[7]endprint
蒙文通認為《尸子》“其書十九者通乎儒墨之義,是周秦之間,合儒、墨于一轍者,固未有先于尸子者也。”[8]因而,尸佼在義利觀層面確展露一種游移于儒墨之間的思想形態:既倡導儒家仁學,卻不重申義利之辨,而是標揭“義必利”的客觀效果。胡適指出,從墨子“愛利一體”、“自苦為極”的功利主義,到雜家尸子、《呂氏春秋》構建在使人民得遂其欲的功利主義,逐步遞嬗衍化出傳統文化中秩序進路的樂利主義政治哲學[9]。在這一思想譜系中,法制原則與正義標準的道德倫理色彩漸漸褪去,呈現出著眼于人民利害與社會實效的利益特征。
三、制分正名:《尸子》的承轉媒介先秦名論異彩紛呈 先秦名學有多種范式。(參見:翟錦程.先秦名學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7-14.),與政法關聯者約有三脈:其一,孔子的正名主義,逐漸衍化出刑(形)名學或稱名實之論,成為后來一以貫之的“法理學基礎。”[9]237、252-253其二,作為法家先驅,鄧析精通刑名之學而作竹刑,從形式到實質均與后來法家的思想緊密相關。梁啟超說:“名與法蓋不可離,故李悝法經,蕭何漢律,皆著名篇。而后世言法者亦號‘刑名。”[10]刑名之書正是憲令不一、刑律繁雜的時代所催生[11],如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后相繆”(《韓非子·定法》),則有申子刑名之書“三符”。其三,黃老之學皆重名論,史家常目之為法家刑名學之源泉。 《經法·道法》云:“刑(形)名已立,聲號已建,則無所逃跡匿正矣。”人們認識事物,也經歷從“審其形名”、“循名窮理”到“名實相應”的認知過程。(參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239.)《管子·白心》 郭沫若認為《白心》出于尹文,仍屬稷下黃老的思想。(參見:郭沫若.青銅時代·宋钘尹文遺著考[C]//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47-572.)中關于名實之論核心命題——“名正法備,則圣人無事”與申韓刑名論頗為接近,蓋為道法名論之接榫。
名實之論,往往是論政之架構,諸學之媒介,故自然成為雜家之焦點。在先秦名論的發展衍變中,經歷了一種雜糅儒、法的過渡形態,呈現于尸佼的思想中。錢穆說:“正名以治,為法家師,如吳起之流矣……則尸子之學,固當與李悝吳起商鞅為一脈耳。”(參見:錢穆.先秦諸子系年[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16.)尸佼之名論少有邏輯名辯的色彩,承襲儒家政治化的正名主義,以經驗主義與實用觀點審視名實關系,反映了政治化、實用化趨向的名論由儒入法的趨勢。李澤厚說:“儒道法均講‘無為而治,均講名,此名非語言、邏輯,乃實用政治。”(參見:李澤厚.論語今讀[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178-179.)
(一)“裁物以制分”:尸佼名論的基本內涵
《尸子·分》曰:
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用賢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
所謂“裁物以制分”,制分之“分”,有“名分”、“份額”之義,是所分配之名分,也蘊涵分量適宜之慮。孔子以前,即有關于德目之適度性的闡述,而儒家以中庸哲學將這一思想系統化[12]。愛、施、慮、動、言,本身只是一個關于舉動或行為的中性描述,而是否“得分”則包含著價值判斷,由此決定了能否升格為褒義色彩的德目范疇——仁、義、智、適、信。值得注意的是,尸佼將適度性考量的中庸觀,順洽地接上正名主義并歸旨于“事少功立”的政治理想,是對儒學義理的創造性發揮,也揭示了中庸之道的制度原則面向,即朝向關于法制創立之正名范疇的過渡或聯結。《尸子·分》云:“君人者,茍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賞罰隨名,民莫不敬。”
在注重制度的尸佼看來,既然存在符合中庸主義的適度性標準,那么,在治國治民的問題上,就應當以制度設計與秩序建構將這一狀態穩固下來,所謂“得其分曰治”,制分、立官之說意即在此。在這種以“制分”為核心詞匯的正名論當中,尸佼之學反而消隱孔子對“禮崩樂壞”的批判視界,而富有強烈的現實主義色彩:期待現實社會中推進政治階層分化與新“分成”秩序的,以立法者的主觀能動性積極“制分”,將劇烈變法形成的新等差秩序合理化并以法律秩序的形式確定下來,所謂“天下之可治,分成也”。
在用賢與治吏的意義上,“制分”邏輯上意味著權力與責任的合一。《尸子·分》言:“諸治官臨眾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所謂“君明則臣少罪”,“制分”要求合理而清晰地劃定臣屬之職責,自然能夠促使臣下對自身職責有明晰的認識,對違反職責之制裁有足夠的警戒。對法律制度客觀性的秉持與強調,顯示出道德判斷觀點向法律制度思索的轉變,這是先秦名學譜系從宏大的權力之“名”縮聚于專門的法令之“名”的轉折點。
(二)“名實合為一”:尸佼名論的轉捩關鍵
在《尸子·分》“裁物以制分”的敘述中,“正名”凸顯出鮮明的政治價值,可達致“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治世。《尸子·發蒙》曰:
若夫名分,圣之所審也……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群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此名分之所審也。
尸佼講“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尸子·發蒙》),佚文中亦論及君臣上下森嚴之禮制,承儒家正名主義余緒,申調整君臣上下權利義務之義,并無二致。不過,尸佼以“用賢”、“明分”、“賞罰”諸論,將正名主義廣泛付諸具體的政治統治實踐中,其言“審名分,則群臣之不審者有罪”(《尸子·發蒙》),契合法家“循名責實”之考績術。“審名分”從正面講是突出“名”以界定官吏的權利義務之內容,反映了建立一種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新秩序之愿望;從反面講則是突出“分”而為官吏的職責劃定邊界,包含一種治道層面分權委任的“明分”思想。endprint
一方面,尸佼憧憬一個圣王來做實質性的審慎建構與設計,為君權秩序提供一套富有哲理根基的制度保障,在“名”為“人君之所獨斷”、“圣之所審”之表述中,法家“術”論的韻味已經開始彌散。“審名分”是為了讓臣民產生“戒慎戒俱”的心理,使臣下“莫敢不盡力竭智矣”,“情盡而不偽,質素而無巧”,君主能更好駕馭利用臣屬以掌控最高統治權。
另一方面,諸子“貴名之正”,大多無意于申說法律之“名”對社會之“實”的反映,而在于強調法律之“名”對社會之“實”的統制地位與決定性質。《尸子·發蒙》云:“名實判為兩,合為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所謂“判為兩”,名實本是可分離的理念與現實,尸佼則強調“合為一”,真正發揮其辨別是非、施以賞罰的實效。結合尸佼“去私論”中“一實”之說,“名實合為一”反映了墨辯“取實予名”、“志功合一”對名論的改良 《墨子·貴義》曰:“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墨辯名論之研究,參見:侯外廬,趙紀彬,杜國庠.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26-232.,顯示了從儒家偏重“虛名”到名實相當的遞嬗軌跡。《尸子·分》中“正名去偽”畢竟并舉了“以實核名”與“正名覆實”兩個層面,與申、韓“刑名參驗”之名論近在咫尺。 胡適認為,名與法其實只是同樣的物事,兩者都是全稱,都有駕馭個體事物的效能。孔子的正名主義的弊病在于太注重“名”的方面,就忘了名是為“實”而設的,故成了一種偏重“虛名”的主張……后來的名學受了墨家的影響,趨重“以名舉實”……如尸子的“以實覆名……正名覆實”,如《韓非子》的“形名參同”,都是墨家以后改良的正名主義了。(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C]//胡適學術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253.)概言之,作為諸學之媒介、言法之根基,尸佼名論偏向實用法術,蘊含著道法轉關、儒法融合之征兆。
四、“用賢”與“案法”:《尸子》的綜合治術
《尸子》有治天下“四術”,即忠愛、無私、用賢、度量。尸佼認為,“因智”而“因賢”可以“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尸子·治天下》),貌似與“去智與巧”的反智論相齟齬,卻意在以有為而致無事,“用賢使能,不勞而治” 尸佼曾引孔子與子貢對話,闡明先王“尚賢”之功:“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見《尸子·佚文》。;另一方面,“案其法則民敬事”,以“貴因任法”闡弘南面之術。然“用賢”與“案法”,儒、法常各執一端使其互相排抑,而在尸佼之學中,兩者卻共融以名學,歸旨于道論,而輻輳并進。
(一)“以賢舉賢”與“以才為儀”:選賢的主客觀標準
在選賢的主觀標準方面,尸佼強調人才的發掘選拔必賴專才,“比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相玉,而借猗頓也”。(《尸子·治天下》)身為賢才,方能慧眼識人,舉薦賢才,此為“以賢舉賢”的“眾賢之術”。他進而主張“便進賢者有賞,進不屑者罪,無敢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尸子·發蒙》)由此,尸佼為“以賢舉賢”之術設計了一個法律保障措施,即將舉賢作為考察官吏的政績,以所舉之人的能力來論功行賞或論罪處罰,終能以制度保障舉賢而靡有孑遺,堪稱后代選官舉措之思想源泉。在尸佼看來,這種頗具連帶責任色彩的機制,不僅是一種“選賢之策”,還是一種“考績之術”,舉賢與賞刑皆歸旨于“事少功多”的效益原則。當然,這種吏治思想與配套制度不免理想化,高估治人的能動性而苛求之,連帶機制亦缺乏正當性基礎。后來秦法正是采用了這一吏治原理,《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載:“秦之法,其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在選賢的客觀標準方面,尸子游移于諸家理念之間。一方面,尸子反對注重出身、宗法世襲的“爵列”,而以實際“德行”為主要標準。首先,名為“勸學”,實則承儒家余緒,力倡德行之修;所謂“賢者之治,去害義也”(《尸子·恕》),仍向往德教意味的賢人政治。其次,與亞圣一樣,尸佼津津樂道于先賢事跡,堅信人才德行常可沖破爵列出身之宿命。再次,尸佼認為,同具普遍化效用的爵列與德行,仍存在效力范圍之差異。《尸子·勸學》曰:“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最后,“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對于人的社會地位與美德懿行,尸佼以形式與實質的關系論之,誠為金玉良言而垂范后世。
另一方面,他將選擇事物的形式標準稱為“儀”,并“以才為儀”。尸佼說:“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故何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為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為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為儀,則管仲、伊尹不為臣矣。”(《尸子·佚文》)以馬、玉等物譬喻,尸佼凸顯的是“用賢之利”。
孔子提倡“舉賢才”,設想于世卿世祿之外另辟蹊徑;孟子宣稱“惟仁者宜在高位”,卻眛于“仕者世祿”之舊識。而墨子憧憬“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墨子·尚賢上》),旨在徹底打破氏族血緣界限,顛覆世卿世祿的世襲舊制,與儒家“親親尊尊”原則下的“舉賢才”貌合神離。這昭示了戰國時期的賢能觀從理論到實踐已發生了一些微妙轉變:為真正實現“賢能面前人人平等”楊俊光認為,墨子提出了“在賢能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參見:楊俊光.墨子新論[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2:83.),“尚賢”從一種與“親親尊尊”相配套的改良方案,轉變成一種旨在顛覆世卿世祿制的批判觀點,與之相應,“賢”也從相對疏闊空洞的倫理德性標準,漸次具備一些契合政法實踐之要素。
尸佼的“尚賢”游移于“德”“才”之間,既有意延續孔孟道德觀念,又援用墨者與前期法家的新尚賢論,體現了對儒、墨、法的兼收并蓄。如果說“德行,公貴也”意在宣揚“去私”觀念,那么“以才為儀”則更直截地表明其賢能觀點。在尸佼看來,德行與才能,在政治實用情境本應綜合考量。有論者說:“對于這個議題,《尸子》采取的觀念可能與墨子較為接近,試觀《尸子》的賢能政治主張也是才能的意義大于道德的意義。”[4]40,44所謂“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尸子·佚文》),“以才為儀”的政治實用轉向仍不言而喻。戰國時期的思想界,在表面一致的“尚賢”話語中,“賢能”的標準,悄然透射出從“貴”到“德”與“才”的轉變軌跡。而在尸佼學說中,道德理想與事功實踐的張力,傳統美德與現實才干的權衡確昭然可見,也反映當時政治社會階層的流動、變遷乃至重置現象背后的法制轉型——以才能、功勛為實質內容的新爵祿制。endprint
(二)“比度觀賢”與“有所委制”:用賢的制度性原則
在孔子時代,雖有正名觀念以界定君臣權利義務,但對于臣下之品行與才能卻未見一套可供實踐的考核理論。“循名責實”的考績之術,借用刑名論之框架得以推衍闡發,以申子之學為前驅,為戰國法家之通論。大概同時,《尸子·分》言:“諸治官臨眾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與法家一樣,尸佼從尚賢進于吏治,并秉持法律制度客觀性而闡發吏治之術。他指出吏治對治國的重要性,“必有所委制,然后治矣”(《尸子·佚文》),“委制”也以“制分”前提,是“制分”在用賢層面的觀照。
賢能政治觀點在《尸子》殘篇中舉足輕重。尸佼言:“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尸子·發蒙》)確也,“進賢”依賴“以才為儀”,“知賢”訴諸“比度觀賢”,“用之”則當“有所委制”,而“儀”、“度”、“制”三者都直接指向“尚賢”所不可或缺的舉賢與考績制度。概言之,尸佼在舉賢方面順應潮流,承祧儒宗,吸納墨學,展現了從“爵”到“德”到“才”的轉向,在用賢方面契合現實,運用名學,開啟了法家考績之術。有論者評曰:“尸佼的忠愛、用賢、無私和量度治世四術中,以用賢即人才為根本,并置于‘從道之中,看成是不可動搖的規律性這是卓知灼見。當時的思想家都看重人才這個問題。尸佼由于其親身的豐富經歷,則看得更為深遠。”[13]
(三)“案其法”與“刑以輔教”:治法的特性與功能
據《漢書·藝文志》,尸佼為商君之師;據《史記·孟荀列傳》劉向《別錄》載,尸佼為商君之客。不管是“師”是“客”或兼而有之,商鞅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對那場叱咤風云的商鞅變法,尸佼自然廁身其間,全程參與。攜《法經》入秦,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不管從理論上重法學說的闡釋,還是從實踐上變法改革的施行視之,皆堪稱先秦法家巨擘。然而,商鞅見秦孝公,竟能先后說之以帝道、王道、霸道,對諸家學說亦可謂運掉自如,甚至有人認為商鞅之重法農戰只是“一時之利”,之后必然走向禮治[14]。商鞅深通儒家之學,也諳曉博通諸家學說的經世價值,或許正是他與尸佼一道“謀事劃計、立法理民”的因緣吧!水渭松就斷言:“尸子在學術思想上曾給商鞅以一定的影響……他們是一脈相承的。”[15]這也反映出融匯各種統治術的尸佼雜學,有將多種治國理念加以法制化的傾向。
就廣義之治法而言,韓非“抱法處勢”的法勢結合論已在尸佼學說中初見端倪。正如法家之慎到、申子、韓非、儒家之荀況都以蓍龜、書契、度量、繩墨、規矩、尺度、鏡、權衡、椎鍛、榜檠等器物類比法,以器物之標準精確的基本屬性比照法之公正特性,尸佼闡釋了法的普遍性、客觀性:“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傚焉。”(《尸子·佚文》)而《尸子·貴言》言:“臣天下,一天下也,一天下者,令于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前文已述,尸佼緊扣令行禁止的法律秩序實效性問題,將其終極價值指向君王“一天下”的功效。尸佼曰:“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日之能燭遠,勢高也。”(《尸子·明堂》 《大戴禮記·盛德》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所以御民之嗜欲好惡,以慎天法以成德法也。刑法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劉師培說:“然吾觀上古之時,政治、學術、宗教,合于一途,其法咸備于明堂。……而有周一代之學說,即由此而生。”由此可見,《尸子》以“明堂”為篇名,寓意學旨歸一,統合禮度德法。(參見:劉師培.左盦外集·古學出于官守論[C]//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483.))唯有處在權力金字塔的上層乃至頂端,以“高顯尊貴”的階層或勢位,方能向下位之階層、蕓蕓之眾生頤指氣使。“若夫名分,圣之所審”,所有關乎權利義務內容的名分皆不可超出君王的掌控。對于治理政事的官吏,尸佼強調居官守法,《尸子·發蒙》謂:“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 《黃帝四經·稱》亦言:“案法而治則不亂。”意即“用法度來治理就不會混亂”。(參見:陳鼓應.黃帝四經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348.)“案其法”的規則之治,才能真正讓百姓遵守秩序,服從治理。
就狹義而言,尸佼的“治法”專指刑罰,有統合儒家德教與法家刑治之旨趣。如后來韓非把賞刑奉為“二柄”,尸子將“賞罰”視為治道應有之義:“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尸子·發蒙》)與法家一樣,尸佼聚焦于刑罰的威懾力與制裁特征,“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尸子·佚文》),刑罰是一種制裁工具,其存在意義乃是在通向治世的漫漫路途上充當一種如同鞭策般的驅動工具或保障手段。然而,尸佼也以儒家的口吻說:“為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尸子·佚文》)刑罰仍被置于德教之下,作為一種違反道德教化的法律制裁。“《尸子》一方面將孔子的‘仁學視為統治上的重要憑著,一方面卻也不忘強調刑的重要性,這里宣示出《尸子》的統治術是德與刑合一的。”[4]45-46
《尸子·佚文》載:
秦穆公明于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于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于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
借秦穆公“明于聽獄”之典故,尸佼闡釋其刑法觀:其一,由于可歸咎于統治者的原因,儒家式的德教有可能“不至”,這是刑罰的合理性基礎;其二,基于對刑罰的謙抑認識,統治者應意識到“使民困于刑”是戾政信號。所以,其刑罰觀雖有法家式“刑期無刑”之邏輯,但“刑以輔教”的認識又使其并未完全認同一味重刑的霸道。
余論呂思勉曾說,《尸子》“確為先秦古籍,殊為可寶”。呂思勉還指出,《尸子》“實足以通儒、道、名、法四家之郵”。(參見:呂思勉.經子解題·尸子[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194-196.)另外,有學位論文全面研究《尸子》之文獻價值。(參見:李文鋒.《尸子》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06:9-31.)然而,觀《尸子》之斷簡殘篇,卻不及道家之博大、儒家之深邃、墨家之雄渾、法家之犀利。上卷之篇目頗為旁通曲鬯,偶有微言大義,惜乎語焉不詳,未免“術通文鈍”(《文心雕龍·諸子》) 劉勰謂尸佼在思想上“兼總于雜術”,而在文學上“術通而文鈍”。(參見:劉勰.文心雕龍[M].王志彬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2:201-206.);下卷所輯錄后人鉤沉寥寥數語,多為上古掌故,義理貧瘠,豈非“雜錯漫羨”?endprint
然而,諸子時代,官學失守,道術為天下裂,百家蜂出并作,紛立新說,“彷佛各有一把開啟各自房門的鑰匙卻沒有通用于各個房門的萬能鑰匙,不足以應付日新月異的歷史變化與瞬息萬變的社會需要。”[16]尸佼雜學之價值正在于“通眾家之意”,顯露出以“王治”為原則,整合“取合諸侯”的諸家法思想之學術抱負,且能以政治實用為原則,不固持成見而能平等汲取[3]105。古人常謂雜家“無所指歸” 《隋書·經籍志》曰:“雜者,兼儒、墨之道,通眾家之意,以見王者之化,無所不冠者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無所指歸。”《劉子·九流》曰:“雜者,孔甲、尉繚、尸佼、淮夷之類也。明陰陽,本道德,兼儒墨,合名法,苞縱橫,納農植。取與不拘一緒。然而薄者則蕪穢蔓衍,無所系心也。”,近人或曰“家而曰‘雜,實為不詞。”[17]然就實際政治而言,學術的雜糅是思想進程之需求,折衷主義是實用價值之顯現,是學問術化、經世致用之必然,亦是政治智慧發展的標志之一[18]。
從王官之學到諸子百家,從諸子百家到漢代儒術,恰是一個隨政治態勢亦步亦趨的文化思想分裂復統一的歷程。鑿王官學之竅而突破創發的各家子學,兼采它家別說力圖話語覆蓋范圍的圓融完滿,并朝向治道法術領地拓充合流,是中國思想發展史的本質特征。博通宏旨之標揭(“去私”)、思想范疇之圓融(“道仁義”)、知識方法之整合(“制分正名”)、治術路向之合攏(“用賢”與“案法”),乃是圓實意識形態主旨、填復官學總貌的必由之路,雜家尸佼之學,蓋能一一發其端緒。此種融合諸家的思想綜合取向,尸佼創議于前,荀卿、賈誼、董仲舒踵武于后。唐君毅說:“諸家分流以后,左右采獲,以求反于一本之思想潮流,秦漢之際之一轉捩思想也。……唯漢興以后,乃實現先秦諸子所向往之文化凝合之理想。”[19]漢代百家學術終趨向治道法術攏合,觀諸董仲舒為代表的漢儒思想、漢家“霸王道雜之”的意識形態(《漢書·元帝紀》),“其統一的旗幟是儒家,統一的精神是雜家。”[20]回觀先秦雜家尸佼之學,揚“去私”精神,陳雜家旨趣,既博采眾家優長之說,又能提挈精義以立綱維;既融洽凝合千端萬緒,又能獨出機杼而發治道王曉波更強調尸佼之學的創新成分:“(尸子)把老子要求對待人民的‘去智與巧,改造成要求統治者的‘執一之道。他把孔子要‘克己復禮的‘正名,改造成客觀的‘令名自正,令事自定。他把儒家義務論的‘仁義,改造成效益論的‘益天下以財為仁,勞天下以力為義。他肯定了法家的‘自為,更要求統治者能以‘大私為‘公”。(參見:王曉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學思想及其論辯[J].臺灣國立大學哲學論評,2008,36:71.),實于戰國中期開啟治道學術合流之先河。甚者,其學深合儒法遞嬗之態勢,盡現治術融通之時風,或許預示著秦漢“道術為天子合”該語引自雷戈書名。(參見:雷戈.道術為天子合——后戰國思想史論[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8:31,90-120.)的思想史趨勢。ML
參考文獻:
[1]李守奎,李軼.尸子譯注[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
[2]張琦翔.秦漢雜家學術[M].北平:金華印書局,1948:1.
[3]潘俊杰.先秦雜家研究[D].西安:西北大學,2005:108-109.
[4]林俊宏.《尸子》政治思想[J].政治科學論叢,2000(12):52.
[5]陳復.由內圣而外王:尸子心學的意蘊與啟思[G]//林文華.第四屆先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高雄師范大學國文學系,2001:221-247.
[6]許青春.先秦雜家義利觀探微[J].濟南大學學報,2006(5):75.
[7]王曉波.兼儒墨、合名法——《尸子》的哲學思想及其論辯[J].臺灣大學哲學論評,2008,36:56.
[8]蒙文通.論墨學源流與儒墨匯合[M]//蒙文通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222.
[9]胡適.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C]//姜義華主編胡適學術文集·中國哲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1:302-305.
[10]梁啟超.先秦政治思想史[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162.
[11]胡適.諸子不出于王官論[C].胡適學術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1: 594.
[12]馬騰.儒家“中庸”之傳統法文化觀照[J].北方法學,2011(2):139.
[13]魏宗禹.尸佼思想簡論[J].山西大學學報,1990(2):12.
[14]鐘泰.中國哲學史[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39.
[15]水渭松.新譯尸子讀本[M].臺北:三民書局,1997:2-3.
[16]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210.
[17]蔣伯潛.諸子通考[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8.
[18]劉澤華.中國政治思想史(先秦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511.
[19]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49.
[20]孟天運.雜家新論[J].哲學研究,2001(11):66.
Abstract: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Shi Jiao set up Zajia School (the Eclectics), which advocated Qusi (denouncing selfishness) as its core idea, and incorporated other schools theories suited for various states based on political pragmatism. His theory centered on the Taoist philosophy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and aimed at an ideal world with “few undertakings but full achievements”.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included the idea of Ren Yi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morality of Confucianism and Mohism, hence featuring a fusion of morality and utilitarianism. Moreover, he incorporated the discussion of name and nature of Mingjia (the Name School) and Fajia (Chinese Legal School) and came up with an integrated interpretation of “employing talents” and “conforming to the laws”. His pragmatism and eclecticism were a reflection of the thinking of Warring States before and after Shang Yangs reform, which followed the trends of Fajias development from Taoism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Fajia. He also suggested a tendency of formulating pragmatic political and governing philosophies, hence a model of incorporation of various schools in the preQin period, also forecast the convergence of all schools in Han Dynasty.
Key Words: Shi Jiao; Zajia(the Eclectics); Shang Yang; Qusi(denouncing selfishness); Tao; righteousness and morality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