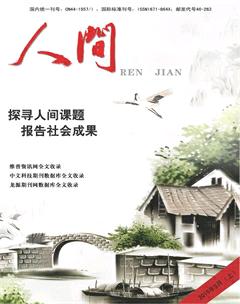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主觀罪過探析
?
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主觀罪過探析
查洪
(貴州師范大學(xué),貴州 貴陽 550001)
摘要:主觀罪過是判定行為人構(gòu)成犯罪不可缺少的要件之一,它是指行為人對其危害行為所致的危害結(jié)果所持的心理態(tài)度。我國刑法將罪過分為故意和過失兩種,主觀罪過直接影響行為人刑事責(zé)任大小的認(rèn)定和承擔(dān)。《刑法修正案(八)》規(guī)定了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但是對該罪的主觀罪過形式卻沒有明確規(guī)定,因此,學(xué)界關(guān)于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主觀罪過問題的爭論一直存在,直接影響著司法實踐中對本案的定罪量刑。本文擬對目前學(xué)界關(guān)于該罪主觀罪過理論觀點進(jìn)行理清,進(jìn)而認(rèn)定該罪的主觀罪過,以期能更好的為司法實踐中對該罪的認(rèn)定與量刑服務(wù)。
關(guān)鍵詞: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故意;過失
從刑法第408條第2款:“負(fù)有食品安全監(jiān)督管理職責(zé)的國家工作人員,濫用職權(quán)或者玩忽職守,導(dǎo)致發(fā)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yán)重后果的....”的規(guī)定來看。食品監(jiān)管瀆職的包括濫用職權(quán)和玩忽職守兩個方面,目前學(xué)界對于以玩忽職守行為方式實施的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主觀方面來說,刑法學(xué)界已經(jīng)基本達(dá)成共識為過失。但是,與在此之前刑法學(xué)界對濫用職權(quán)罪的主觀方面的討論存在的爭議一樣,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罪的主觀方面的討論也一直存在爭議。總結(jié)起來,刑法學(xué)界對“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罪”的主觀方面的討論主要形成了以下幾種觀點:
一、單一罪過說
該說認(rèn)為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罪過形式是單一的罪過形式,即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和過失中的一種。因此,該說的內(nèi)部又分為“故意說”和“過失說”兩種觀點。
支持“故意說”的人主張負(fù)有食品安全監(jiān)管職責(zé)的工作人員的濫用職權(quán)行為必須是在故意的主觀心理支配下實施,即行為人明知自己實施的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行為會發(fā)發(fā)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yán)重后果,仍然希望或者放任這種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主觀上只能是故意,[1]支持“過失說”的人主張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罪的犯罪主觀方面只能是過失。[2]原因在于,首先犯罪主觀方面判定依據(jù)是行為人對自己行為可能引起的危害后果的態(tài)度,而非對濫用職權(quán)行為的態(tài)度;其次作為犯罪成立條件的客觀事實都是犯罪主觀方面的必要對象,不能將濫用職權(quán)行為造成的重大損失排除在濫用職權(quán)罪主觀方面的內(nèi)容之外;最后法律要求以危害結(jié)果的實際發(fā)生為犯罪成立條件的犯罪,原則上應(yīng)該是過失犯罪。而且大部分學(xué)者在主張過失說時考慮濫用職權(quán)罪和玩忽職守罪規(guī)定在同一法條中且適用相同的法定刑。
二、故意過失并存說
支持“復(fù)合罪過說”的人認(rèn)為,濫用職權(quán)罪的主觀方面是由過失和間接故意共同構(gòu)成的,本罪的主觀罪過是間接故意與過于自信過失結(jié)合的復(fù)合罪過。[3]復(fù)合罪過是相對于單一罪過來說的,是指對于同一罪名,既可以由犯罪的故意構(gòu)成有可以有犯罪過失構(gòu)成,然而為便于司法實踐的操作,理論界提出了由犯罪故意以及犯罪過失結(jié)合的符合罪過,這樣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guān)的證明責(zé)任相對較小,但是此種觀點難以解釋的是,在我國刑法中,明確規(guī)定了故意與過失兩種罪過形式,那么故意與過失作為刑法中兩種不同的責(zé)任形式,其區(qū)別在立法與實踐中便有其相應(yīng)的區(qū)分標(biāo)準(zhǔn),例如,對于故意與過失的區(qū)分,學(xué)界就是從行為人認(rèn)識因素以及意志因素進(jìn)行區(qū)分的,主觀持故意的行為人對行為的危害結(jié)果是積極追求或放任的態(tài)度,而過失犯罪的行為人對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是不希望的,持的是反對的態(tài)度,因此,犯罪的故意以及過失并不是不可區(qū)分的,再有,即使刑法關(guān)與故意與過失的規(guī)定難以區(qū)分,那么也只能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進(jìn)行完善,對司法實踐進(jìn)行指導(dǎo),而不是通過理論界的解釋來指導(dǎo)司法實踐,或者說為便于司法實踐操作就維持現(xiàn)狀,而不對之進(jìn)行完善。
三、故意過失選擇說
該說認(rèn)為無論是故意還是過失都可以獨立作為“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罪”的罪過形式。[4]對于主觀方面是故意的食品監(jiān)管濫用職權(quán)罪來說,其罪過形式一般情況下是直接故意,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形下也可以是間接故意;對于主觀方面是過失的食品監(jiān)管玩忽職守罪來說,其罪過形式一般只能是過于自信的過失。與復(fù)合罪過說不同的是,依混合罪過說認(rèn)定的罪過形式并非是在傳統(tǒng)的罪過形式之外的一種新的罪過形式,也就是說在認(rèn)定某一具體的犯罪的罪過形式時,最終認(rèn)定的結(jié)果只能是故意和過失這兩者中的一個。相反,復(fù)合罪過說所認(rèn)定的罪過形式與當(dāng)前通行的罪過形式完全不同,也就是所依復(fù)合罪過說所認(rèn)定某一具體犯罪的罪過形式是同時具有故意和過失這兩種罪過的新的第三種罪過形式。然而支持混合罪過說的人只是舉例說明了每種罪過形式的適用場合,而沒有充分闡述其支持的理由。
四、模糊罪過說
持該說的人認(rèn)為,由于濫用職權(quán)型瀆職罪的主觀方面的認(rèn)定比較困難,在司法實踐中不太好把握行為人在實施濫用職權(quán)犯罪行為時的主觀心理,致使司法機關(guān)在對具體案件中的濫用職權(quán)犯罪行為定罪量刑時常常出現(xiàn)法律適用困難,因此,司法機關(guān)在認(rèn)定濫用職權(quán)型瀆職犯罪的罪過形式時應(yīng)當(dāng)適用嚴(yán)格責(zé)任。[5]具體來講,司法機關(guān)只要能夠認(rèn)定行為人的濫用職權(quán)行為符合濫用職權(quán)罪的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其他方面,就可以據(jù)此認(rèn)定行為人的行為構(gòu)成該罪,而無需有證據(jù)證明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時的主觀心態(tài)。
五、本罪主觀罪過分析
筆者認(rèn)為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主觀罪過形式應(yīng)確定為“過失”,具體包括疏忽大意的過失犯罪與過于自信的過失犯罪兩種,即單一罪過說中的過失說較為合理,原因在于:
首先,在司法實踐中,根據(jù)刑法罪過之間的位階關(guān)系,認(rèn)定濫用職權(quán)罪和玩忽職守罪行為人罪過的時候,行為人主觀罪過故意和過失之間并不是對立的,他們是位階關(guān)系,可以將行為人故意評價為過失,但不能將過失評價為故意。只有這樣才能準(zhǔn)確地打擊犯罪,做到無漏罪情況發(fā)生,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中濫用職權(quán)罪和玩忽
其次,根據(jù)罪行相適應(yīng)原則,行為人的所受的刑罰應(yīng)與行為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一致,主觀罪過決定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以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而故意和過失作為兩種不同的罪過形式也決定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的不同,通常,刑法對于故意犯罪的懲罰要重于過失犯罪,原因在于,在故意犯罪中,行為人明知自己行的行為會產(chǎn)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仍然持放任或追求的態(tài)度,其主觀惡性要大于犯罪過失,《刑法修正案(八)》將玩忽職守型的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和濫用職權(quán)型的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規(guī)定在同一條款中,并且配置了相同法定刑,可以判定這兩種行為的主觀罪過是一致的,其主觀罪過都應(yīng)當(dāng)是過失,這符合立法的原意。
最后,從刑法總則關(guān)于故意與過失的規(guī)定來看,犯罪的故意以及過失都是針對行為人對其行為造成的危害結(jié)果而不是危害行為本身來說的。濫用職權(quán)型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中的危害結(jié)果是發(fā)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yán)重后果。而司法實踐中致使公共財產(chǎn)、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這一構(gòu)成要素對于濫用職權(quán)罪來說,并非是犯罪結(jié)果而是獨立的罪量要素。沒有出現(xiàn)這一構(gòu)成要素,仍然屬于濫用職權(quán)行為,只是刑法不予以處罰而已。只有當(dāng)具備了這一構(gòu)成要素,刑法才加以處罰。因此,這一構(gòu)成要素是表明濫用職權(quán)行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數(shù)量因素。對于確定行為的故意或者過失沒有關(guān)系,在刑法對犯罪故意和犯罪過失有相關(guān)規(guī)定的情形下,應(yīng)堅持總則指導(dǎo)分則的原則,根據(jù)行為人對其危害行為所致危害結(jié)果所持的主觀心理態(tài)度來判斷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式。因此,濫用職權(quán)型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行為人的主觀罪過形式是過失。
參考文獻(xiàn):
[1]趙秉志主編:《刑法修正案(八)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頁。
[2]賈宇:《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認(rèn)定及適用》,載《河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xué)學(xué)報》2012年第2期。
[3]王洪用:《食品監(jiān)管瀆職罪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2014年第9期。
[4]馬榮春:《危害食品安全罪犯罪構(gòu)成新探》,載《法治研究》2014年第2期。
[5]張軍、姜偉等:《刑法縱橫談:理論.立法.司法(總則部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
文章編號:1671-864X(2015)05-0037-02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中圖分類號:DF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