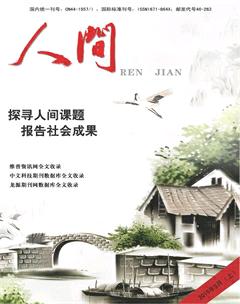淺析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況
?
淺析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況
王鑫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重慶 沙坪壩 400031)
摘要:2012年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新刑事訴訟法全面總結了我國刑事司法在尊重和保障人權領域的豐富經驗,把司法實踐中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提升為法律規則,其中最大的兩點是非法證據的排除。本文將簡要闡述新刑訴法頒布之后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況、構成要件以及如何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關鍵詞: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構成要件;完善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概況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定義。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具有偵查權的執法人員因取證手段違反憲法或者法律的規定,侵犯到了公民的憲法權利或者法定權利,導致取得的證據沒有證據能力,即不具有可采性,而被法院予以排除的規則。
2.非法證據:按照最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非法證據是指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只是前者證據是直接排除,而后者是先進行補正,不能補正的才可以作為非法證據排除。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意義。
1.對基本人權予以保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實質和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保障人權,這一規則本身就體現出了對人的尊重,特別是對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隱私權的尊重。在保障人權的同時也準確打擊犯罪,維護司法權威與司法公正。《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的出臺就將會極大程度上避免虛假、非法的證據被法庭采納,從而有利于案件經過審判而得出公正、正確的結果,有利于司法機關及時地査明犯罪分子,準確地打擊犯罪行為,避免傷害無辜的公民。
2.對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加以平衡。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的運行過程中,收集審查證據無疑是前提性、基礎性的要件之一,而對于搜査扣押證據的審查更是對于刑事訴訟活動的結果有著尤為重要的影響力,因此需要嚴格的證據規則來確保刑事訴訟程序沿著合法方向進行發展,這也是實現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
3.順應國際司法改革和發展的潮流。1984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公約》第十五條規定:“每一個締約國應保證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使用任何己經確定是由酷刑而獲得的口供作為證據。”我國早在1988年就經批準加入了這一公約。所以,在我國正式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不但有利于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律符合國際公約和普遍規則的要求,還有利于我國司法改革與國際的接軌。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發展現狀。
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0 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司法解釋中也有類似的簡單規定。在實踐中,2010年之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基本只限于文本規定,很難在實踐中發揮效用。但此次刑事訴訟法修改,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內容,這是中國第一次在全國人大的立法層面采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標志著我國正式確立了該規則。除這一條外,新《刑事訴訟法》中還有5個法條共同構成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具體來說有新《刑事訴訟法》第50、55、56、57、58條,至于其具體內容在下文將會相應地提到。2012年12月24號公布的《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進一步明確“刑訊逼供”的定義,根據《解釋》“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愿供述的”就應當認定為“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目前相關的法律和司法解釋就只有這么多。
二、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構成要件
(一)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
指哪些證據需要排除,按照新《刑事訴訟法》54、56條之規定,主要有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指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即指言辭證據。第二部分是指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物證、書證。
對于這個問題有的學者認為,對于偵查機關、檢察機關自行發現的非法證據,應當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僅僅對該證據直接予以排除。因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有權知道哪些證據系非法所得,是不是予以排除,以及不予排除的理由,即便該證據予以排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也應當知曉,因為該證據系非法所得還可能關系到其它證據的合法性,以及整個偵查程序的適當性,因此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參與下進行。筆者認為這樣的考慮是妥當的,因為在賦予被告權利的同時也對偵檢機關的調查取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樣更有利于保證文明司法、以及保證被告人在訴訟中的合法權益。
(二)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程序。
1.啟動主體:按照新《刑事訴訟法》第54、55、56條之規定,該程序的啟動主體主要分為兩個部分:(1)司法機關(偵查機關、檢察院、法院)主動啟動;(2)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向法院申請啟動。
2.啟動階段:新《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階段都可以提起。就我看來,應該將非法證據排除在訴前審查之前完成,在進入審判階段之前盡早將非法證據排除到訴訟程序之外,對不必要進入下一階段訴訟程序的案件及早進行分流,一方面使無辜涉訴者早日擺脫訴累,另一方面也可以節省司法資源和提高司法效率。所以這也應該是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方向。
3.審查主體:就法條來看,目前主要局限在法院審查。但有的學者認為“在審查逮捕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因為有檢察機關的介入,有條件適用三角形的刑事訴訟構造,由檢察機關居中裁判,公安機關和犯罪嫌疑人一方就非法證據進行辯論,并由檢察機關做出決定。”即把檢察院作為一個審查主體來看待,但筆者認為,在目前的司法環境下想把此模式運用于現實的條件并不成熟。
(三)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分配。
按照新《刑事訴訟法》第57條之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以及第58條之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說明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是由檢察機關承擔的,檢察機關有義務提供各種證據證明其證據來源的合法性,否則將承擔由此帶來的不利法律后果。
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
(一)明確界定“非法證據”的范圍。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相關規定不但要界定非法言詞證據應當排除這一原則,更要詳細明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細致闡述應當被排除的非法言詞證據的特征,通過界定何為非法手段來判斷何為非法證據,從而能準確地指導司法實踐。這不但需要立法者有著先進的法治理念,更需要將司法實踐與立法技術相結合。
(二)增加濫用非法證據排除程序權利的違法成本。
即要求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主體在不能明確提供相應的初步證據而故意使訴訟程序中止的時候,給與相應的懲罰,對偵查機關的失職及濫用職權等行為加大處罰,提高違法人員的犯罪成本,這樣應該能對比如意圖刑訊逼供的人員起到一定警示和威懾作用,讓其三思而后行,衡量利害結果。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被告人或者相應的司法機關濫用訴訟權利,也更能有效的達到非法證據的排除的制度目的。
(三)降低啟動該程序主體的初步證明責任。
新刑事訴訟法中將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權利賦予被告人,要求被告人在主張其言詞證據為非法取得時,應提供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線索,且提出的這些線索應達到足以令法官懷疑取證合法性的程度。但是這種提供線索的行為是不是屬于證明責任呢?如果讓被告人承擔主張非法證據證明責任,理論依據何在。因此我認為這無疑加大了被告的舉證責任,因為對于這些證據被告是很難甚至不可能出據的,因為被告自被羈押之后就已處于公權機關的控制之下,在這種情況下,實行舉證責任倒置是必要的。
總而言之,本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雖然不算盡善盡美,但本次刑訴法修改中正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無疑是中國法治的一大進步,代表了中國未來由輕程序重實體的立法思想向程序實體并重的法治理念的轉變,同時也體現了中國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保障的重視。
參考文獻:
[1]佘景妮.審查逮捕階段排除非法證據問題探析——以《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及其指導意見為視角[J].法制與社會.2011(19).
[2]姚海東,董斌.司法實踐中排除非法證據的途徑 [J].中國檢察官.2011(21).
[3]宋英輝.中國大陸地區非法證據排除的適用范圍 [J].中國法律.2010 (04).
[4]任琰,譚恩惠. 刑事訴訟中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研究 [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03).
[5]馬書奎.淺議民事法律援助工作 [J].華章.2011(28).
職守罪行為方式,同樣可以用位階關系將二者的罪過形式認定為過失,也就是說食品監管瀆職罪的主觀方面應為過失。
文章編號:1671-864X(2015)05-0038-02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D9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