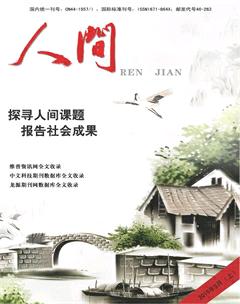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看外交口譯員的必備素質
?
從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看外交口譯員的必備素質
宮穎
(福建師范大學,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長期以來,翻譯理論研究一直是翻譯研究領域里最受重視的,翻譯史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關注,尤其是口譯史。上世紀后50年,我國出版了約500本翻譯方面的書籍, 其中翻譯理論研究占有約20%,翻譯史僅占1%,而口譯史只有1本——黎難秋的《中國口譯史》。本文從翻譯史研究的角度,通過對馬格爾尼使團訪華口譯員的分析, 希望在強調口譯員必備素質的同時,引起人們對口譯史的重視。
關鍵詞:馬戛爾尼使團;外交;翻譯史;口譯
一、引言
1792 年9月26日,為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增進貿易交流,喬治· 馬戛爾尼勛爵 ( Lord George Macartney) 受英王指派,以賀乾隆八十大壽為名,率領規模龐大的使團來華。這是西歐政府同中國的第一次正式外交,在中英關系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這次英國使團訪華的使命最終以失敗而告終,但后人對這次事件的研究興趣卻經久不衰。
譯者是翻譯活動中的主體,口譯者在外交活動中的作用至關重要。因此,中英雙方都在譯者的選定問題上下了一番功夫。通過分析中英雙方選擇的譯者能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整個歷史事件,讓我們對口譯員的必備素質有更深入的認知。
二、英方的譯員分析
馬戛爾尼使團在最初籌備時就發現物色譯員的不易。最后副使喬治·斯當東(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找到了兩名愿意回國的中國神甫——李雅格和周保羅。他們兩位都會意大利語和拉丁語,但是都不會英語。另外,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斯當東( George Thomas Staunton)作為見習兒童隨使團一同前往中國。小斯當東聰明伶俐,有著超強的語言學習能力,沿途隨著中國翻譯學習中文,很快便掌握了中文并且會寫漢字,正式了成為馬戛爾尼使團中的一名“譯員”。當時,中國人不能擅自離開國門,也不能受雇于外國人。英使團坐船抵達澳門后,因害怕被降罪,周保羅便執意上岸,不愿為使團翻譯。這樣,李雅各和小斯當東便要承擔起馬戛爾尼使團的翻譯重任。
馬戛爾尼使團第一次和清王朝派來的眾多大臣會面時,小斯當東便和李雅各一道完成翻譯任務,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他作為使團中唯一一個學會了說中國話的成員,還參與到禮品清單的翻譯中。馬戛爾尼使團為了表現其對清王朝的重視和對此次訪華的誠意和用心,要求在禮品單里對每項禮物作出詳細說明以凸顯出其禮物的貴重,翻譯難度可見一斑。另外,小斯當東還承擔起謄抄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禮儀照會譯文的工作。禮儀照會的英文原件是先譯為拉丁文,經由李雅各粗略譯出中文意思后,由法國傳教士羅廣祥(Nicholas Joesph Raux)請來的一位中國基督徒進行加工潤色使之符合清朝官文格式后完成。但是他擔心被清王朝認出字跡因參與國事被降罪,因此謄抄照會譯文的任務就落到了小斯當東身上。可見,小斯當東的中文水平頗高,既能說也能寫。
與小斯當東相比,李雅各的中文水平則不盡如人意。他雖然是中國人,但他13歲便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在國外待了20年,長期使用拉丁語和意大利語,中文對他來說早已陌生。另外, 他對中國官場用語和宮廷禮儀習俗完全不熟悉,也沒有任何中國官場經驗。例如,他不理解委婉語和話語中的弦外之音。大臣和珅的話“要不是皇上估計你們還有自己的事要辦,他倒挺愿意讓你么留下”,他翻譯時只是翻譯了字面意思,完全沒有理解這其實是“逐客令”,沒有把真正的意思傳達給中國人。這樣的翻譯失誤完全是不諳熟中國的語音和文化導致的。
由此可見,掌握雙語言文化對譯者來說是多么重要,翻譯不只是一種語際轉化,在深層意義上它更是一種跨文化轉換。從文化的角度看,翻譯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傳播和文化闡釋。[6]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不能僅僅局限于字面上的翻譯,還要諳熟兩種語言下的文化,才能游刃有余地完成翻譯任務。
三、中方的譯員分析
雖然李雅各的翻譯水平得不到認可,但是他對馬戛爾尼使團卻是不容置疑的。他始終站在英使團的立場,竭盡全力維護英使團的利益。他敢于承擔任務,面對困難,堅守崗位,沒有像周保羅那樣臨陣脫逃,竭盡所能完成任務;堅持英國遞交給乾隆皇帝的是“禮品單”而非“貢品單”,拒絕練習并向英使團示范覲見乾隆皇帝時清朝要求做的三跪九叩覲見大禮;拒絕接受臣屬關系,堅決要求中英兩國外交活動中的平等地位,維護英國的政治立場,利益和尊嚴。李神父對英方利益的敏感度甚至超過了馬戛爾尼,對于“進貢”一詞馬戛爾尼都置若罔聞,他卻極力爭辯。因此,季壓西稱李雅各為“忠實的仆人,不稱職的翻譯”。[4]
同樣,清王朝在翻譯人才的選擇上也頗為重視,也遇到了相同的困難。當時的中國長期閉關鎖國,不具備精通中英雙語的翻譯人才,并且清王朝一直都靠為朝廷服務的歐洲傳教士處理外交事宜,所以請7名歐洲傳教士為翻譯,成立了以葡萄牙傳教士索德超(Joseph-Bernard d’Almeida)為首的翻譯團隊。這些歐洲傳教士不懂英文,且因為來自歐洲各個國家,各個國家就宗教利益和在華利益的掠奪上是有矛盾的,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錯綜復雜,所以他們當中有的像索德超一樣憎惡英國人,對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要求千般阻撓,有的像法國傳教士賀清泰(Louis de Poirot)和羅廣祥支持英使團來華。
索德超是馬戛爾尼使團未抵京前就被清王朝確定下的譯員。當馬戛爾尼使團在熱河時,他被清廷委派擔任主要翻譯。[7]
而馬戛爾尼使團事先就了解到索德超對英國的敵意,因而堅持不讓其當翻譯。“彼那鐸此人……然妒念極重,凡西人東來者,除其本國人外,閣不加以仇視。對于英國人懷恨尤切。吾至澳門之時,即有人囑余抵北京后善防此人。今日一與此人相見,觀其沉毅陰險之貌,始知此人非處處防范,必為所陷。”[5]雖然只想讓李雅各作為唯一一名正式譯員,可由于李雅各的翻譯能力不盡如人意,特別是不諳熟官場用語,英使團無奈之下才啟用葡籍傳教士索德超。
當時,索德超在中國已有十余年,擔任欽天監副監,與李雅各相比,他諳熟中國文化習俗和官場用語,所以馬戈爾……尼使團上呈給乾隆皇帝的文書全都要經他一一過目。在進行翻譯任務時,他以葡萄牙在華利益為重,千方百計破壞英使團訪華的計劃。他在翻譯中可能刻意添加了一條原本在英使團六條要求備忘錄中沒有的第七條:傳播英國國教。也正是這一條,引起了乾隆皇帝的反感和震怒。出于維護葡萄牙在華利益和對英國的嫉妒,在馬戛爾尼使團離開中國后,他繼續散步對其不利的謠言,意在進一步破壞中英兩國的外交關系,以鞏固葡萄牙的在華優勢。索德超之所以從中作梗,是因為葡萄牙多次意圖與清廷建立外貿關系均未獲得批準,因此他也不希望馬戛爾尼使團取得成功。[2]
那法國傳教士賀清泰和羅廣祥為什么會支持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呢?這些不同國籍的傳教士在北京不僅僅是承擔翻譯任務這么簡單,他們絕對不是一心一意為清王朝服務的譯員,而是“充當著各自的國家在中國的代理人,遇有涉及本國利益的事項,他們總要進行些活動”。[1]法國傳教士認為,如果歐洲等國與中國的關系進一步改善的話,有利于他們在中國傳教進程的發展,而英國在傳教問題上根本不是法國的對手。正因為基于這點考慮,在翻譯英國國王第二道勅諭時,他們刻意添加了對英王表示敬意的詞語以緩和原稿的語氣,并告訴馬格尼爾“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敕諭中塞進一些對英王陛下致敬的詞語”。[3]馬戛爾尼使團對羅廣祥教士的印象極佳,還請他參與了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的禮儀照會的翻譯工作。
作為中方選擇的譯者,各國傳教士們屬于不同的宗教派別和國家,出于對他們個人的宗教利益和國家利益的考慮,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有的幫助馬戛爾尼使團,有的則破壞馬戛爾尼使團活動,給中英外交造成了巨大影響。根據上述分析,我們不難得出,譯員的政治意識和政治傾向在外交翻譯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我們在外交翻譯過程中,必須要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將自己的立場擺在公正的位置上,確保原文的信息準確無誤地翻譯出來。
四、結論
在歷史長河中,口譯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口譯在外交翻譯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關系著外交活動的成功與否。在口譯員在進行外交翻譯時,不僅要具備有過硬的雙文化能力,駕輕就熟地實現兩種語言的轉化,傳遞出原文的真實意思,而且要有敏銳的政治意識,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將自己的立場擺在公正的位置上,切勿強加自己的意志和觀念。只有這樣,才能讓外交活動順利進行,促進兩國關系的和諧發展。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口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對口譯發展史的進一步研究對我國的對外關系是非常重要的。
參考文獻:
[1]Staunton,George. 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M]. London: Pall-Mall,1797.
[2]陳順意. 論譯者的立場———以近代來華傳教士口譯活動為例[J] 長春工程學院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4 (15).
[3]戴廷杰. 兼聽則明———馬戛爾尼使華再探[A]. 載于一史館編. 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匯編[C]. 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P137.
[4]季壓西,陳偉民. 中國近代通事[M]. 北京: 學苑出版社,2007.
[5]濮蘭德· 白克好司.乾隆英使覷見記 [M]. 廣東:珠海出版社,1995,P30.
[6]王寧. 翻譯研究中的文化轉向 [M]. 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P14.
[7]袁墨香. 馬嘎爾尼使華與天主教傳教士 [M]. 山東大學,2005,P23.
作者簡介:宮穎,女(1991-8)。民族:漢。籍貫:山東省煙臺市。研究方向:英語口譯。
文章編號:1671-864X(2015)05-0083-02
文獻標識碼:A
中圖分類號:H3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