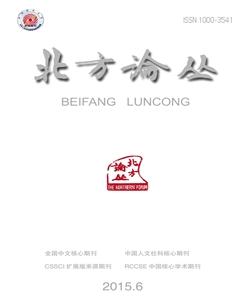詩歌中的“面具”美學
殷曉燕 萬平
[摘 要]詩歌主要是表達詩人思想、抱負、志趣的文體,側重于表述內在心聲。但文學中呈現出的“聲音”卻是非常復雜的,未必是作者本人的真實聲音,有時是寄托的聲音,美國漢學家孫康宜把這種仿若戴著“面具”不以真實面貌示人的文學現象稱為“面具”美學。晚唐詩人李商隱受黨派之爭牽連,政治上徘徊彷徨表現,在詩歌中欲言又止、隱喻深婉,內在心聲隱藏在“面具”之下,反而成就了詩歌含蓄蘊藉之旨、神秘朦朧之韻。
[關鍵詞]詩歌;面具;美學;李商隱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5)06-0033-06
“Mask” Aesthetics of Poetry
——A Interp.retation about Late Tang Poet Li Shangyin of Step.hen Owen
YIN Xiao-yan,WAN Ping
(Chengd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engdu 610106,China)
Abstract: Poetry mainly exp.resses the poets thought, aspiration, inclination, focusing on the representation inner voice. But literature showing a “voice”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may not be the true voice of the author, and sometimes it is the sound of sustenance. American sinologist Kang-I Sun Chang put this are like wearing a “mask” not to show his true face literary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mask” aesthetics. The Late Tang p.oet Li Shangyin was implicated by partisanship., political hovering hesitantly anxious exp.ression in poetry, metap.horical and eup.hemistic. The inner voice is hidden under the “mask”, but the achievement of poetry p.urp.ose of imp.licit and mysterious rhyme haze.
Key words:Poetry; Mask; Aesthetics; LI Shang-yin
《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載:“詩以言志。”《莊子·天下篇》云:“詩以道志。”《荀子·儒效篇》則曰:“詩言是其志也。”由此可見,詩歌這種文體主要表達的是詩人自己的思想、抱負、志趣等,側重于表述內在心聲。且由于詩歌文體的特殊性,人們傾向于認為詩歌乃詩人的真情流露,與“小說”此類文體敘事中第三人稱敘述或隱含作者是不一樣的。但從屈原開始,即有“男女君臣”之說,以香草喻君子,以蕭艾喻小人。男性詩人身處不同的環境中,政治上的復雜性使他們難以真正在詩歌中直抒胸臆,傾向于以“隱喻”的方式包裹內在心聲,而這種處理方式正體現了文學中的不同 “聲音”。美國耶魯大學漢學家孫康宜(Kang-I Sun Chang)說:“文學里的‘聲音是非常難以捕捉的——有時近在眼前,有時遠在天邊;有時是作者本人的真實的聲音,有時是寄托的聲音。解構主義告訴我們,作者本人想要發出的聲音很難具體化,而且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十分錯綜復雜,不能一一解讀,因而其意義是永遠無法固定的。”[1](p.2)這在“含蓄蘊藉”的中國古代詩歌中更是被文人發揮得淋漓盡致,而這種仿若戴著“面具”不以真實面目示人的文學現象也被孫康宜稱為“面具”美學。為探討此類美學下的文本意蘊,本文以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歌為例,體會其詩歌中的“面具”美學,發現覆蓋在“面具”之下的詩歌朦朧美。
一
弗洛伊德曾說:“面具是外在自我的隱喻”;從表面來看,“面具”是一個殼,一種可以遮擋人臉的罩子;而從象征意義來看,它也是一種人格的偽裝,是一種虛飾。而人之一生,無論虛構出來的東西有多么迷離奇特,但終究脫離不了現實的基礎。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面具”的妙用,在于為內在心聲蒙上了一層紗,既可使表達意圖若隱若現,又可避免直白若揭,還可激起他人掀開“面具”之欲。那如何掩蓋文本中的真實意圖呢?文人慣用“隱喻”的手法來表達,而這種手法也被詩人用在了“言志”的詩歌中。
李商隱作為晚唐著名詩人,在政治上成就些微,在文學上卻光彩倍出。他與杜牧并稱“李杜”,為了區別于李白、杜甫,又稱“小李杜”;“他和溫庭筠并稱‘溫李;再加上另一個作家段成式,又被當時人譽為‘三十六體——他們三人作文風格都傾向于繁縟華麗,恰巧在本家族中,各人又都排行十六”[2](p.1)。李商隱一生陷于“牛李黨爭”之中,他受牛派令狐楚提攜,后又娶李黨王茂元之女,雖并無明確證據表明王茂元即為李黨李德裕之人,但卻因此受到令狐楚之子令狐绹攻訐他“背恩”“無行”,《新唐書·李商隱傳》據此推衍他“忘家恩,放利偷合”,歷來遭到很深的誤解。正是由于受到黨派之爭連累導致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為緩解困境,他在許多場合都急于向令狐绹剖析自己的內心,但又難以直抒胸臆,所以,他的詩歌,如無題詩、愛情詩等,歷來不會被當作單純描寫男女情愛之詩來解讀,而是被歷代學者闡釋為具有一定的政治指向性,使之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內含無限的朦朧意蘊。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說:“李商隱詩歌的一部分是‘偷偷摸摸的,暗示某種用十分引人注目的明顯方式掩飾起來的處境。中國批評家從這些明顯作隱秘狀的詩歌得到提示,開始在更大范圍的李商隱詩歌中尋找隱含的艷情或政治所指。”[3](p.398)李商隱詩歌種類繁多,含有詠懷詩、無題詩、愛情詩、詠物抒情詩、政治詩等,其中尤以無題詩、愛情詩聞名。男女情愛本是人類正常感情的表達,但在傳統中國社會,特別是以儒家思想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將男歡女愛以直白露骨的方式描寫出來,只會降低詩歌的格調,故此種方式向來為道學家所不恥。即使《詩經》中有“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等愛情詩,也往往寫得隱晦唯美。《詩經》中之所以慣用賦、比、興之法,也與中國詩學道統有關。此兩首詩皆采用“興”的手法,朱熹《詩經集傳·關雎》注:“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通過對他物的敘述與類比,已收到了迂回的功效,在愛情詩的描寫中,可以起到委婉含蓄之美。
古代婚姻講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戀愛之事非為尋常。李商隱年輕的時候曾經有學道的經歷,他與女道士的關系以及詩歌中所用的語言,在宇文所安看來對于他詩歌的隱喻晦澀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對于自己年輕時醉心于道教的經歷,李商隱在詩歌中都有所涉及。“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韻》)“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安平公詩》)等都可以看出學道的痕跡。唐代是道教昌盛時期,李唐王朝的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將李聃奉為自己的祖先,故道教在唐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力壓齊梁時期貴盛無比的佛教。“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統治者的提倡對于整個社會倡道風氣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加上煉丹服藥、入道成仙的說法,更是令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都對道教產生了極大的熱情。唐時期李白、顧況、顧非熊等都有入道、習道的經歷。故李商隱有過習道的經歷也并非奇事,而這段經歷也在他的詩歌中留下了烙印。李商隱有詩《和韓錄事送宮人入道》:“星使追還不自由,雙童捧上綠瓊輈。九枝燈下朝金殿,三素云中侍玉樓。鳳女顛狂成久別,月娥孀獨好同游。當時若愛韓公子,埋骨成灰恨未休。”韓錄事,指的是韓琮,也為詩人,與義山并稱。馮浩認為:“中、晚唐頗多此題。”[4](p.120)可見,送宮女出宮入道的現象不在少數,韋應物也曾寫過《送宮人入道詩》、于鵠亦有《送宮人入道》等。
因李商隱有過這段入道的經歷,對他詩歌形成的意境、素材、語言等均有影響。楊柳認為:“在這階段中,李商隱結識了不少女冠,和她們有過較密切的過從關系,甚至對其中個別年輕貌美的女冠有過戀愛生活。”[5](p.82)中國的評論家們在闡釋詩歌時,習慣“知其人,論其世”將詩人的真實生活經歷與詩歌內涵相結合,何況義山詩中的確有以女冠為標題的,《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還有《藥轉》《銀河吹笙》《圣女祠》等,均為此段生活情景的寫照。因此,李商隱愛情詩的詮釋就有了道教生活與女道士為之披上的面紗。而在中國人的認知里,作為宗教,道教與成仙、長生不老、帝王等聯系在一起,與世俗的隔絕、神秘的氣息、朦朧的意境、隱喻化的語言都為其增添神秘的面紗,形成霧里看花的效果。
作為西方漢學家,與中國學者不同的是,宇文所安在西學背景下,傾向于以文本為中心,讓文本自己說話,從詩歌語言入手,認為李商隱詩歌語言體現的隱喻性特征和他的入道經歷有關。
道教高度隱喻性的語言是限制性比喻話語的特殊情況,傳達出特定精英群體的秘密知識。李商隱年輕時的學道經歷在他的一些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經常將道士的言論與艷情的暗示混淆在一起。評論家們幾乎從來沒有把他的詩僅僅作為是道士的語言來闡釋,除了一些在特殊場合提及道教的詩,例如一些與道觀主持酬唱的詩。[6](p.342)
如同前文所舉《有感二首》,整篇之中布滿了道家語言的蹤跡,“三靈”“云物”“鬼箓”“洪爐”等,顯得晦澀難懂。若非對道教語言有著一定的了解,并知此詩寫作的背景,實在很難弄明白此詩的含義。這既可看出道教語言的隱喻性對李商隱詩的影響,同時也可看出他對道教語言與典故的熟練掌握。而作于入道之時的《藥轉》一詩,堪稱其最隱晦難解的詩篇之一:
郁金堂北畫樓東,換骨神方上藥通。露氣暗連青桂苑,風聲偏獵紫蘭叢。長籌未必輸孫皓,香棗何勞問石崇。憶事懷人兼得句,翠衾歸臥繡簾中。
此詩曾被朱彝尊稱之為“題與詩俱不解”。紀昀也說:“題與詩俱不可解,不必強為之。”頸聯“長籌”指的是廁所用紙,加上“吳國孫皓把佛像置于廁中尿之頭上褻瀆佛像得到報應的典故”,“石崇因富可敵國而將廁所布置得奢華富麗,以致大將軍王敦入廁受辱”的故事都為此詩罩上了隱喻的意味,因此,人們難以相信這純是一首“入廁”之詩。正如宇文所安所說:“這首詩在唐代不是一個標準話題,而且沒有任何共同的詩學關聯。因此,評論家們假設這里肯定包括了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各種油然而生的解釋都在試圖說明廁所:從潛伏在廁所的女性刺客、到程夢星絕望的渴望,再到作為墮胎場所的廁所。”[6](p.344)采取“墮胎”之說的是馮浩,他認為:“頗似詠閨人之私產者,次句特用換骨,謂飲藥墮之,三四謂棄之后苑,五六借以對襯,結則指其人歸臥養療也。”[4](p.562)楊柳也認為:“這是一首諷刺入道貴主餌藥墮胎的詩。”[5](p.83)而葉蔥齊則認為:“這是用通便藥通便后,感到暢適,戲作的詩……通篇詞旨顯明,本沒有什么僻澀難解之處。”[7](p.113)幾方都各執一詞,爭論不休,詩歌的魅力由此產生。與白居易詩歌的直白淺切相比,詩歌帶有一定的“秘密”反而會成為詩歌的魅力所在,它吸引了眾多的評論家趨之若鶩,提供了各種版本的詮釋,深入詩歌背景,挖掘詩人心理,以此提高了詩人的價值與詩學的魅力。宇文所安認為:“這些詩的詩意不在于尋找開啟秘密的‘鑰匙,而在于建構秘密本身。”[3](p.399)
那么,作為一個美國漢學家,站在與中國文化迥異的外在立場來看,這首詩隱藏的“秘密”又是什么呢?他認為,此詩最重要的詩句應該是第七句,它包含了李商隱在此類詩歌中隱喻性指向的最清晰含義,這首詩是為一個女人(或者男人)所作,這個人掌握了一定的信息,為詩句提供了必要的語境。她也可能是非常博學的,已經超出了浪漫詩歌意象的標準范圍。對于律詩來說,尾聯承擔的是“合”的任務,應該是詩歌意義的歸結點。但此詩第七句的意義的功能被宇文所安認為是“散漫的”,因為:
如果這首詩是一個真正的私人交流,第七句是無意義的,因為“接受者”可能就是這個“人”,她知道如此朦朧表現的事件的本質。第七句似乎在假設讀者的身份,對讀者來說這一行是有意義的信息:它斷定了他們可能猜測的內容。當這句假定讀者可能不知道前面詩句指向的人物和事件,它也假設了讀者們可能不會知道人物和事件到底指的是誰。總之,這句詩指出了保持隱藏性的信息的存在。[6](p.345)
因此,宇文所安斷定它是“一種秘密的詩學”。可以說,這樣的評述抓住了此詩隱含的接受者,繼而去猜測她的身份與詩歌所寫的情境,并預設了讀者的身份與可能的想法,從讀者的角度而非作者的角度推導出《藥轉》一詩包括隱喻的復雜信息。雖然李商隱詩歌中的隱喻意義是評論家們賦予的,但是中國學者們通常是從李商隱的角度,以及他的時代背景、他所處的環境等來解剖詩歌的內涵,有所不同的是,漢學家卻是從讀者的角度,從文本入手,為我們展示了他的分析之路,對中國學者有所吸收與借鑒,呈現出異曲同工之妙。
二
李商隱詩歌以隱喻性增強其詩歌特色,除了前面提到的道家語言出現在詩中,深奧隱晦的道教語言為其詩的隱喻性增加了神秘的特色,仿佛戴上了神秘的面具。在他的詩作中,具體的隱喻性特征還表現在詩歌的題目與結尾。
(一)題目
題目是一首詩或一篇文章的靈魂,也是主旨,表達了作者的中心意圖,同時題目也是創作的語境,從題目中可以獲知一定的信息,對于解讀文本有著重要的意義。詩題同樣也不例外。故對于題目的意義,宇文所安如是認為:“一個題目就是一個語境,當我們有題目時,我們知道如何去解讀詩歌的部分內容或全部,如果沒有此語境化的題目,詩歌就會保持令人無望的晦澀性。”[6](p.350)李商隱的詩歌保存至今大約600首,其中最晦澀難懂、解說紛紜的那部分恰恰是“無題詩”。
所謂“無題詩”,共包括三種情況:一是直接以“無題”為詩題,即《無題》;二是截取詩歌開頭二字或三四字為標題,如《錦瑟》《碧城》等;三是選取詩篇中間或結尾幾字為題,如《中元作》《明日》等。此三者皆屬“無題詩”的范圍,其詩集中此類作品有八十多首,前兩類“無題詩”作品更為常見一些。
那么,以“無題”命名和以首句前幾個字節命名是否存在不同呢?如他的《無題》:“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如果將二者命題方式互換,分別為《昨夜》和《無題》,相信也沒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方式,而二者傳達出來晦澀不明的隱喻信息,同樣都令評論家們對它們充滿了好奇與探索。對于這二類不同的命題方式,宇文所安說:“它們的形式驚人地相似,強烈地暗示出‘無題詩和那些題目是前兩個字符的詩僅僅區別在命題的慣例上。”“評論家們的分歧在于這僅是一首艷情詩還是在艷情的偽裝下隱喻詩人與公主或提攜人的關系。”[6](p.400)李商隱的“無題”詩,向來是他最迂回隱蔽的詩歌部分,馮浩說:“自來解《無題》諸詩者,或謂其皆屬寓言,或謂其盡賦本事,各有偏見,互持莫決。余細讀全集,乃知實有寄托者多,直作艷情者少,夾雜不分,令人迷亂耳。”[4](p.135)雖然如此,馮浩卻認為,《無題》二首(昨夜星辰),“此二篇定屬艷情,因窺見后房姬妾而作”[4](p.136)。而葉蔥齊卻認為,此詩是“商隱由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時所作……商隱初釋褐入秘省時,實在是充滿了無限希望,而歷時未久,忽然外調補尉,懊喪的心情可以想見。詩人因為不愿明言,所以用無題托于艷詞來抒寫胸中的恨慨”[7](p.137)。可見大家對“無題詩”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均有自見。
李商隱詩歌中為什么存在如此多的“無題詩”呢?除了可能在詩集的流傳中,因為編選者面對的是不同版本的手稿,有的時候可能本身即沒有題目,所以,只好以“無題”擬之,剩下的情況則可能是李商隱描述的是晦澀不明的事情,他不愿讓他人窺探到詩歌中的秘密,故以“無題”題之,就是為了使意義不明。有時他隨便從詩歌中選取兩個字節作為題目,顯示出他無意為詩歌標明主旨,久而久之,特別是隨著此類詩作的增多,反而造就了貌似有題而實無題的局面,更加突出了詩歌的朦朧性,也顯得愈加神秘,形成了李商隱詩歌的獨特標志了。
宇文所安把“無題詩”譯成“Left Untitled”,對此,他給出了這樣的認識:“因為中國詩歌通常給出題目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來理解詩歌,我把‘無題翻譯成‘Left Untitled,暗示出拒絕提供一個題目是有意義的舉動。如此一個題目已經指向隱藏的信息并建構了神秘性,并成為李商隱詩歌重要的模式。”[6](p.380)
雖然宇文所安承認了李商隱詩集中“無題詩”的隱喻性,但對于他何以如此做,卻無法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因為他覺得今人無法確定這是李商隱故意為之還是在詩歌匯編時為了傳播的方便而為,“因為寫在便箋上沒有題目的一首單純的詩更易于傳播與保存”[6](p.380)。單純一首詩的傳播,這樣可能比較方便些,但在編輯詩集時,如存在大量的“無題”詩的話,對于后人的閱讀與傳播并非易事。因此,目錄中有些無題詩的后面都要跟隨第一句詩的說明,如同詞牌名后還要跟第一句詞一樣。
其實李商隱“無題詩”的創作并非首創,從《詩經》開始即有此傳統。先秦時期詩歌的形式多為民歌民謠,便于吟唱諷詠,故有題無題不甚重要,直到文人將其錄入典籍并進行編選時,才根據詩意加入題目,有時就從詩中選取幾字作為詩題,如《氓》《采薇》《蒹葭》《關雎》等等。漢代的《古詩十九首》也屬類似情況,在編入蕭統主編的《文選》時,統稱為“古詩”,后人以首句為題,可見知其本為無題詩,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等均是此類詩作。兩漢樂府中同樣存在此種情況,如《戰城南》《有所思》《雞鳴》《平陵東》等皆是如此。可見,以民歌性質出現、在詩題還不是非常發達的時期,易于出現“無題”的情況。
隨著詩歌的發展,它的形式、格律、詩法等越來越規范的時候,對于題目的要求也是從隱性趨于顯性,標志就是詩題越來越長,對于詩歌的語境描述得也越來越通俗化與直白化。有時,題目之后還要作序,更是將背景等交代得清清楚楚,如陶淵明的詩即有此現象,在詩題中已經將時間、地點、寫詩背景等表露出來,如他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作》。到了唐代,詩題的發展更稍嫌夸張,白居易曾經寫有《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望月有感聊抒所懷寄上浮梁大兄于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此詩為七律,共56字,而詩題則占了49字,給人一種不太對稱的感覺。詩題的詳細通俗優點在于曉暢易懂,缺點則是流于淺露,乏少含蓄之美。故袁枚曾說:“詩到無題是化工。”[8](p.624)王國維也指出:“詩有題而詩亡,詞有題而詞亡。”[9](p.218)宇文所安在分析了李商隱的《飲席戲贈同舍》后說:“當給出這種特殊場合的語境時,這首詩變得相當平凡。最好的‘無題詩要比它好很多,然而我們必須承認它們部分的優美來自環境化結構的缺失,這使得詩歌更加神秘與不確定。”[6](p.402)正是缺少了代表語境的詩題,才使得“無題”詩有了一種缺憾與神秘的美。
“無題”之作成為李商隱詩歌的獨特風格,代表著含蓄、內斂、神秘、唯美的藝術境界,無論是讀者,還是評論家,皆沉醉于他所創造的隱晦境界中,去尋找其中的婉曲深旨。梁啟超就曾說過:
義山集中近體的《錦瑟》《碧城》《圣女祠》等篇,古體的《燕臺》《河內》等篇,我敢說他能和中國文字同其運命。這些詩,他講的什么事,我理會不著;拆開一句一句的叫我解釋,我連文義也解不出來。但我覺得他美,讀起來令我精神上得一種新鮮的愉快。須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10](p.3944)
(二)結尾
李商隱詩歌善用興寄,長于隱喻,其“無題”詩除了在題目中有所暗示,結尾的對句即絕句的第四句、律詩的尾聯也是其詩歌意義的落點。宋人蔡正孫《詩林廣記》說:“一篇之妙,在乎落句。”[11](p.42)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一:“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尾句,如截犇馬。”[12](pp.11-12)清王士禎《漁洋詩話》卷上:“一篇全在結句。”[13](p.845)可見,結尾的妙句猶如“點睛”之筆,乃作者用意的落點,全詩主旨所在,可以起到顯示或加深作者旨意,彰顯作者藝術魅力的功效。
結尾是律詩中“合”的部分,李商隱作為詩歌寫作的高手,其結尾同樣是傳達意圖、表現信息的地方,故宇文所安是這樣評論的:“李商隱隱秘性律詩最大的魅力在于內在對句密度與難度的強烈對比和結尾,結尾通常被言說的迫切與情感的虛無所標志。”[6](p.389)以律詩為例,當前面六句更多地以具體意象傳達云山霧海的信息時,往往會使人感覺是景物的堆砌,只有在尾聯中,把詩人意欲說明的感情或旨意展示出來,由“物”落到“情”。如他的無題詩《一片》:
一片非煙隔九枝,蓬巒仙仗儼云旗。天泉水暖龍吟細,露畹春多鳳舞遲。榆夾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后期。
前面六句描寫得優美神秘,因知道李商隱詩往往多隱喻,故在閱讀時,讀者不會僅僅把他的詩看作景物的描寫,而會在“蓬巒”“云旗”“桂花”“月”等意象背后尋找隱藏的喻意。如果一味這樣寫下去,可能有令人摸不著頭腦的意味,但尾聯兩句才是作者真正想要說明的。使讀者更陷入猜測境地的是,因不知他所言說的對象意指何人:究竟是作者的感嘆還是針對詩歌的接受者所說的呢?故宇文所安指出:“李商隱詩的結尾通常向某人言說或者好像同讀者分享個人的信息,創造出一種隱秘性來,這種隱秘性在很多方面是同隱晦的內部詩句所表現的秘密事實極為相似。有的時候他的詩不是很難懂,但結尾使它有相同的隱私性。”[6](p.391)
李商隱無題詩中最有名并在文學史上一直爭論不休的應該是他的《錦瑟》: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最早從宋人劉頒《中山詩話》開始即說:“李商隱有錦瑟詩,人莫曉其意,或謂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14](p.287)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錦瑟”到底所指為誰,結果卻是眾說紛紜、難有定論,從“青衣”到“婢女”,再到“王氏”“宮嬪”“年齡”“瑟”等均有人說。該詩也一直在愛情詩、悼亡詩、政治詩、詠物詩與自傷身世詩等中徘徊。但毫無疑問的是,這首堪稱李商隱隱喻詩中最有水準之作。連宇文所安本人也覺得,“雖然它不能代表詩人作品的所有范圍,它卻成為李商隱詩的試金石,并成為人們對他的詩產生興趣的催化劑”[6](p.392)。
《錦瑟》一詩的難解不僅在于其指向的晦澀上,整首詩中充滿了典故,“莊生曉夢”“望帝杜鵑”“滄海月明”“藍田日暖”等,顯示了詩人對典故的熟練掌握,并為詩的整體構成增色許多。在詩人把典故代表的意象描述完之后,話鋒一轉,結尾又歸到詩人抒發心中感慨的不明暗示上。故宇文所安認為:“像‘錦瑟這樣的詩是形式的天賦。中間的詩句,屬于被強烈批評審查的客體,如果在五十韻的排律中將會顯得不易察覺,是詩的結構使它們活躍起來。雖然這首詩及大量諸如此類的名詩中,首聯與尾聯的作用一樣突出,尾聯卻是詩中進行反思的最好位置。”[6](p.394)
錢鐘書先生同樣也認為,《錦瑟》尾聯是好句:
七八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乃與首二句呼應作結,言前塵回首,悵觸萬端,顧當年行樂之時,即已覺世事無常,博沙轉燭,黯然于好夢易醒,盛筵必散。登場而預有下場之感,熱鬧中早含蕭索矣。朱行中《漁家傲》云:“拼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而今”早知“他年”,即“當時已惘然”也。[15](p.344)
李商隱的“無題”詩,沒有詩題的點明主旨,只能在詩歌本身中尋找隱含的意義,結尾無疑是詩人表達意圖的最佳位置,但卻因為其所指不明,或者說詩人與詩歌接受者心知肚明,留給讀者的卻是布滿迷霧的玄機,讓讀者在欣賞之中思索,在思索之中猜測,比起平鋪直敘、淺顯通俗的詩歌更多了一分興味,成為宇文所安與中國評論家抓住的焦點,突顯了李商隱“無題”詩的隱喻性魅力。
從李商隱的詩歌與宇文所安對他詩的具體分析中,我們看到詩人為避免平白直敘而對詩歌進行的藝術化處理,對自我完成“面具”的鑄造。在面具的覆蓋下,他的詩歌充滿了晦澀不明的氣息,詩中的意象、意境、氛圍、人物都使后人對李商隱充滿了神秘的探索之欲,既為詩歌蒙上面紗之美,也使其本人成為神秘的代表。正如孫康宜所說:“詩歌是一種表演,詩人的表述是通過詩中的一個人物,作為自我掩飾和自我表現的一種手段。”[1](p.255)雖然未必首首都有另外的人物,但以詩為媒介通過掩飾的方式來表現自己,成為中國古代文人含蓄內斂的象征。
[參 考 文 獻]
[1]孫康宜.文學的聲音[M].臺北:三民書局,2001.
[2]董乃斌.李商隱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宇文所安.劍橋中國文學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4]馮浩.玉谿生詩集箋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楊柳.李商隱評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6]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7]葉蔥齊.李商隱詩集疏注[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
[8]袁枚.隨園詩話[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9]王國維.人間詞話[M].徐調孚,周振甫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10]梁啟超.中國韻文里頭所表現的情感[C]//梁啟超全集:第7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1]蔡正孫.詩林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2]魏慶之.詩人玉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
[13]王士禎.漁洋詩話[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4]劉頒.中山詩話[C]//何文煥輯.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1.
[15]錢鐘書.談藝錄[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殷曉燕:成都大學副教授,文學博士;萬平:成都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 洪 軍]